按:不分析托马斯·曼是不是同性恋,不用女性主义解读弗吉尼亚·伍尔夫、托妮·莫里森,不把柯勒律治放在生态主义视域下考量,还能在耶鲁教一辈子文学,还能写《影响的焦虑》《西方正典》这样的著作。在89岁高龄逝世的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是这样,反对着“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在现代浪潮的洪流中担起了西方文明经典标准的大旗。
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读者之一,哈罗德·布鲁姆在晚年写作了《如何读,为什么读》。比起用五百页写26位作家的《西方正典》、用七八百页写一位作家的《莎士比亚:人的发明》等相对高深博学的著作,《如何读,为什么读》是一本面向大众的作品。在这本书的序言当中,他说自己已年近七旬,不想读坏东西如同不想过坏日子,所以,他写出的这本书,像是给年轻读者一份体验报告,什么该读,什么不该读,到底该怎么读。
其实,大多数人不怎么读书。哈罗德·布鲁姆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大部分时间用来看电视的童年,会催生面对一部电脑的青春期,阅读于是分崩离析,可是他也看到,今天仍然存在着孤独的读者,“如果批评在当前还有一个功能,那就必须是针对这个孤独的读者。”为这个读者,他直接指明阅读的核心:孤独和自我。阅读是消减孤独和增强自我,阅读是自我完善,而不是完善邻居街坊。“阅读的乐趣是自私的,而不是社会的。你不能通过读得更广泛或深入而直接改善任何别人的生活。社会上有一种传统的希望,希望个人想象力的增长也许能刺激人们关心别人,但我对此持怀疑态度,我同样对孤独的阅读乐趣带来的任何扩张能否增进公共利益持谨慎态度。”不过,他也看到,只要我们通过阅读增强自我、完善自我,最终我们也会成为别人的启迪。译者黄灿然认为,这种启迪别人,是自我完善的一种“溢出”,而非“灌输”。
在布鲁姆离世之际,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经出版社授权从《如何读,为什么读》选摘了部分内容。布鲁姆在其中不仅指出了阅读是为了增强自我、了解自我的真正利益,还提出了在今天我们恢复读书方式的原则。他邀请读者寻找真正贴近自己的东西、可以被用来掂量和思考的东西。“不是为了相信,不是为了接受,不是为了反驳而深读,而是为了学会分享同一种天性写、同一种天性读。”
《序曲:为什么读?》
文 | [美] 哈罗德·布鲁姆 译 | 黄灿然

如果人们要保留任何形成自己的判断和意见的能力,那么他们继续为自己而阅读就变得很重要。他们如何读,懂不懂得读,以及他们读什么,都不能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但他们为什么读则一定是为自己的利益和符合自己的利益。你可以只为消磨时间而读,或带着明显的迫切性而读,但最终你会争分夺秒地读。《圣经》读者,也即那些为自己而研读《圣经》的人,也许要比莎士比亚读者更能说明那种迫切性,然而两者的追求是一样的。读书的其中一个用途,是为我们自己做好改变的准备,而那最后的改变啊,是适合任何人的。
我转向阅读,是作为一种孤独的习惯,而不是作为一项教育事业。我们此刻独处时阅读的方式是与过去保持一定延续性的,不管学院里阅读风气如何。我理想的读者(和终生的英雄)是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他知道并表达了不间断阅读的力量与局限。像任何其他心智活动,它必须满足约翰逊最关心的事情,那就是“什么是贴近我们自己的,什么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弗兰西斯·培根爵士,他有些想法也被约翰逊加以利用。培根曾有一个很有名的建议:“读书不是为了发难或反驳,也不是为了相信和视为理所当然,也不是为了找话说和交谈,而是为了掂量和考虑。”在培根和约翰逊之后,我要加上第三位善于读书的哲人爱默生,他是历史和一切历史主义的猛烈敌人,他曾说最好的书“以这样一种信念感动我们,也即同一种天性写,同一种天性读”。让我们把培根、约翰逊和爱默生融合在一起,配制一个如何读的处方:找到什么才是贴近你又可被你用来掂量和考虑,且击中你心坎的东西,仿佛你分享同一种天性,摆脱时间的独裁。实际地讲,意思就是先找来莎士比亚,然后让他来找你。如果《李尔王》能够充分地找到你,那就掂量和考虑它与你共有的天性;它与你贴近的程度。我不是要把这当做理想主义,而是当做实用主义。把这出悲剧当做是一种对父权制的控诉来利用,那等于是抛弃你自己最主要的利益,尤其是作为一位年轻女子的利益,这听起来反讽味很浓,但实际上不。在两代人间的冲突方面,莎士比亚是无可逃遁的权威,尤甚于索福克勒斯;而在男女差别方面,他的权威是无人能及的。请敞开胸怀,充分阅读《李尔王》,你就更能明白被你认定是父权制的东西的起源。
最终,我们读书——如同培根、约翰逊和爱默生都同意的——是为了增强自我,了解自我的真正利益。我们把这类扩张当成乐趣来体验,而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美学价值一向被上至柏拉图下至当前我们校园里的清教徒这类社会道德主义者贬低。确实,阅读的乐趣是自私的,而不是社会的。你不能通过读得更广泛或深入而直接改善任何别人的生活。社会上有一种传统的希望,希望个人想象力的增长也许能刺激人们关心别人,但我对此持怀疑态度,我同样对孤独的阅读乐趣带来的任何扩张能否增进公共利益持谨慎态度。
专业读书的可悲之处在于,你难以再尝到你青少年时代所体验的那种阅读乐趣,那种哈兹利特式的滋味。我们现在如何读,部分地取决于我们能否远离大学,不管是内心方面的远离还是外部方面的远离,因为在大学里阅读几乎不被当成一种乐趣来教——任何具有较深刻美学意义的乐趣。开放你自己,去直接面对莎士比亚最强有力的作品,例如《李尔王》,绝不是一种轻易的乐趣,不管是在你青少年时代还是垂暮之年;然而,不去充分地(充分的意思是不怀着意识形态的期待)阅读《李尔王》,则无异于在认知上和美学上受蒙骗。大部分时间用来看电视的童年,会催生面对一部电脑的青春期,然后是大学录取一个学生,他不大可能欢迎“我们必须忍受死亡,甚至把它当成出生来忍受;成熟最重要”这样的建议。阅读分崩离析,那个自我也差不多溃散殆尽。现在哀叹这一切已经太晚了,且任何誓言或计划都补救不了。唯一可以做的,是通过某个精英版来实行,但精英版如今已不可接受,其背后理由有好也有坏。仍然存在着孤独的读者,老的少的,哪里都有,甚至在大学里。如果批评在当前还有一个功能,那就必须是针对这个孤独的读者,她为自己而读,而不是为那种被假定为超越自我的利益而读。

价值,在文学中如同在生活中,是与怪癖有很大关系的,因为意义正是从这种过度开始的。并非偶然的是,历史决定论者——那些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是由社会历史诸多因素所决定的批评家——把文学人物视为白纸上的符号,仅此而已。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则哈姆雷特甚至谈不上是一个“病历”。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要恢复我们的读书方式,我就要提出第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我从约翰逊博士那里借来的:清除你头脑里的虚伪套话。你的词典会告诉你,在这个意义上的虚伪套话是指洋溢着道貌岸然的陈腔滥调的讲话,是教派或秘密小团体的特殊词汇。鉴于大学把权力授予诸如“性别与性征”和“多元文化主义”之类的秘密小团体,约翰逊的告诫也就成了“清除你头脑里的学院虚伪套话”。现时的大学文化,已经用欣赏维多利亚时代女人内裤取代欣赏查尔斯·狄更斯和罗伯特·勃朗宁,这种文化乍看好像是一个新冒出的纳撒尼尔·韦斯特的敢作敢为,但实际上只是常规。这类“文化诗学”的一个副产品是现在再也不可能有纳撒尼尔·韦斯特了,因为这样一种学院文化怎能消受得起戏仿呢?适合我们阅读的诗歌,已被我们文化的紧身内衣取代。我们的新“唯物主义者”们告诉我们,他们已为历史主义寻回肉体,并断言他们是以“现实原则”之名行事。心灵的生命必须屈服于肉体的死亡,然而这根本就不需要一个学院教派来做啦啦队。
清除你头脑里的虚伪套话引向恢复读书的第二个原则:不要试图通过你读什么或你如何读来改善你的邻居或你的街坊。自我改善本身对你的心灵和精神来说已是一个够大的计划:不存在阅读的伦理学。心灵应留在家中,直到它的主要无知被清洗干净;太早涉足行动主义自有其魅力,但那样会太消耗时间,而要读书,时间永远不够用。不管是把过去或现在历史化,都是一种偶像崇拜,是对时间中的事物的过分膜拜。因此,应当用约翰·弥尔顿颂扬的,以及爱默生视为阅读原则的那盏内心之光来阅读,而它可以作为我们的第三个原则:一个学者是一根蜡烛,所有人的爱和愿望会点燃它。华莱士·史蒂文斯,也许是忘记了出处,曾一再根据这个隐喻写了很多奇妙的变奏,但爱默生这句原话的措辞,有助于更清楚地表达阅读的第三个原则。你作为读者的发展的自由,是自私的,不过这点你大可不必害怕,因为如果你变成一个真正的读者,那么你的努力所引起的反应,将证实你会成为别人的启迪。我回想我过去这七八年来收到的陌生人的来信,总的来说它们使我感动得难以回答。在我看来,它们的感染力在于,它们一而再地证明一种渴望,渴望研究正典文学,而这正是大学鄙视因而不愿意去做的。爱默生说,社会不能缺少有教养的男女,并有先见之明地补充说:“民间,而非学院,才是作家的家。”他指的是强势作家,是有代表性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代表自己,而不是选区,因为爱默生的政治是精神的政治。
现在大学教育的功能,已基本上被忘记了,但它永远铭刻在爱默生的演说《美国学者》中。他在谈到学者的职责时说:“这些职责可概括为自我信任。”我的第四个阅读原则,也是来自爱默生:要善于读书,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发明者。爱默生意义上的“创造性阅读”,曾一度被我形容为“误读”,这个词曾使反对者相信我患上了词汇诵读困难症。当他们望着一首诗时,他们所见到的一无所有或空白全都是在他们自己眼睛里。自我信任不是一种天赋,而是心灵的第二次诞生,而这第二次诞生没有经过多年深读是不可能的。美学没有绝对的标准。如果你要坚持认为莎士比亚的升起是殖民主义的产物,那么谁会在乎去驳斥你呢?经过四百年之后,莎士比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无所不在;他们将在外太空演出他,以及在其他世界,如果人类可以抵达其他世界的话。他不是西方文化的阴谋;他包含阅读的一切原则,而他也是我这整本书的试金石。博尔赫斯把莎士比亚这种宇宙性归因于莎士比亚明显的无我,但这个特质是一个大隐喻,用来说明莎士比亚的不同一般,这不同一般最终其实就是不同一般的认知力量。我们阅读,往往是在追求一颗比我们自己的心灵更原创的心灵,尽管我们未必自知。
由于意识形态,尤其是意识形态较浅薄的版本,对理解和欣赏反讽的能力是特别具有杀伤力的,因此我建议,也许可把寻回反讽作为我们恢复阅读的第五个原则。想想哈姆雷特的无穷尽的反讽吧,当他说某一件事时,几乎总是毫无例外地意味着另一件事,实际上还常常与他所说的相反。但是说到这个原则,我已濒临绝望,因为你无法教某人反讽,就像你无法指导他们去孤独。然而反讽的丧失即是阅读的死亡,也是我们天性中的宝贵教养的死亡。
我从厚板踩向厚板,
一条缓慢而谨慎的道路,
我感到头上的星星
脚下的大海。
我不知道下一步
是不是我最后的一寸——
这使我学到那岌岌可危的步态,
有人把它称做经验。
女人和男人都可以走得很不同,但除非我们齐步走,否则我们都往往各走各的。狄金森是一位岌岌可危之崇高的大师,但如果我们对她的反讽充耳不闻,我们就无法明白她。她正走在唯一可走的小径上,“从厚板到厚板”,但是她那缓慢的谨慎却反讽地与巨人精神并置,在其中感到“头上的星星”,尽管她的脚已差不多踏在海里。由于不知道下一步是不是她的“最后一寸”,这就使她有了“那岌岌可危的步态”,她不提它的名字,除了告诉我们“有些人”把它称做经验。她读过爱默生的文章《经验》,这是一篇顶峰之作,如同《论经验》之于他的师傅蒙田,而她的反讽是对爱默生文章的开头作出亲切友好的反应。爱默生在文章开头说:“哪里去找我们自己?在一个系列中,我们不知道它们的末端,于是相信没有。”那个末端,对狄金森来说,即是不知道下一步是否那最后一寸。“如果我们之中有任何人知道我们过去做什么,或我们现在去哪里,那么当我们思考时我们就知道得最清楚!”爱默生这番话更深一层的沉思,在气质上,或按狄金森的话说,在步态上,是不同于狄金森的。在爱默生的经验王国里,“万物游移闪耀”,而他和蔼的反讽与她那岌岌可危的反讽也是非常不同的。然而,两人都不是空头理论家,他们仍然活在他们的反讽的互相抗衡的力量中。
在失去的反讽的道路尽头,是最后一寸,超出它,文学价值将难以寻回。反讽只是一个隐喻,而一个文学时代的反讽,极少能够成为另一个文学时代的反讽,然而,如果没有反讽意识的复兴,则我们失去的将不仅仅是我们一度所称的想象性文学。二十世纪伟大作家中最反讽的托马斯·曼,似乎已经被失去了。他的新传记一部部出版,而关于这些新传记的书评,几乎总是集中于谈论他的同性恋情欲,仿佛他必须被我们核实为同性恋者,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从而在我们的学校课程中占一个位置。这与研究莎士比亚时主要研究他明显的双性恋相似,但我们现时的反清教主义的奇思遐想似乎是无限的。莎士比亚的反讽,一如我们会预期的,是所有西方文学中最全面和最辩证的,然而它们并非总是充当中介,为我们调停他的人物的激情,因为他们的情感幅度实在太广阔和太剧烈了。所以,莎士比亚将在我们时代消逝之后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将失去他的反讽,抓住他剩余的东西。但在托马斯·曼那里,每一种情绪,不管是叙述的或戏剧性的,都是由一种反讽的唯美主义调停的;向现时大多数本科生,哪怕是有才能的本科生,讲解《死于威尼斯》或《无序与早期的忧伤》,几乎是不可能的。当作者们被历史淘汰,我们正确地把他们的作品称为特定时代的作品,但是,当他们由于历史化的意识形态而使我们难以接触他们,我想,我们便是遭遇一种不同的现象了。
反讽要求某种专注度,以及有能力维持对立的理念,哪怕这些理念会互相碰撞。把反讽从阅读中剔除出去,阅读便失去所有的准则和所有的惊奇。现在就找找那贴近你的东西,那种可用来掂量和考虑的东西,它非常有可能就是反讽,即使你的很多老师并不知它是什么,或哪里可找到它。反讽将清除你头脑中那些空头理论家的虚伪套话,并帮助你像那位蜡烛似的学者那样炽烈地燃烧起来。
我快七十岁了,不想读坏东西如同不想过坏日子,因为时间不允许。我不知道我们欠上帝或自然一个死亡,但不管怎样,自然会来收拾,但我们肯定不欠平庸任何东西,不管它打算提出或至少代表什么集体性。
因为五十年来,我理想的读者一直是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所以接下来让我引述他的《莎士比亚序言》中我最喜爱的一段:
因此,这样说都是对莎士比亚的赞美:说他的戏剧是生活的镜子;说那些因读了别的作家而跟着这些作家创造的魅影走,从而使自己的想象力陷于迷津的人,可以通过读莎士比亚而治愈他们的谵妄的狂喜,因为他用人类的语言表达人类的情绪,因为在他描写的场面中一个遁世者也许会评价世界的事务,一个忏悔者也许会预言激情的进展。
要读用人类语言表达的人类情绪,你必须有能力用人性来读,用你全部身心来读。你远远不止是某种意识形态,不管你的信念是什么,而莎士比亚对你讲的话,绝不会少于你可以带给他的。即是说:莎士比亚读你,要远远比你读他更充分,即使你已清除了你头脑里的虚伪套话。莎士比亚之前或之后没有任何作家能像他那样控制透视力,这透视力超越我们强加给莎士比亚戏剧的任何社会语境。约翰逊令人击赏地觉察到这点,并促请我们让莎士比亚来治疗我们的“谵妄的狂喜”。也让我延伸约翰逊的话:促请我们好好认识深读莎士比亚就能驱除的那些魅影。其中一个魅影,是所谓的“作者之死”;另一个魅影是断言自我是一种虚构;再有一个就是认为文学和戏剧人物是白纸上的众多符号。第四个魅影也是最阴毒的魅影,是宣称语言替我们思考。
然而,我对约翰逊的爱和我对阅读的爱,终于还是使我离开论争,转向颂扬我不断遇到的众多孤独的读者,不管是在教室里或在我收到的来信中。我们读莎士比亚、但丁、乔叟、塞万提斯、狄更斯、普鲁斯特和他们的匹敌者,是因为他们都不止扩大生命。实际上,他们已变成天恩,真正的、旧约圣经意义上的天恩,也即“把更多生命注入没有边界的时间”。我们为各种理由而深读,这些理由大多数是我们熟悉的:我们无法足够深刻地认识足够多的人;我们需要更好地认识自己;我们不仅需要认识自我和认识别人,而且需要认识事物本来的样子。然而深读那些如今备受咒骂的传统正典作品的最强烈、最真实的动机,是寻找一种有难度的乐趣。我并不完全是一个“阅读的情欲”的推广者,而有乐趣的难度在我看来是对“崇高”的可信定义,但更高级的乐趣依然是读者的求索。有一种读者的崇高,而这似乎是我们能够获得的唯一的世俗超越,除了还有那甚至更岌岌可危的超越也即我们所称的“恋爱”。我促请你寻找真正贴近你的东西,可被用来掂量和思考的东西。不是为了相信,不是为了接受,不是为了反驳而深读,而是为了学会分享同一种天性写同一种天性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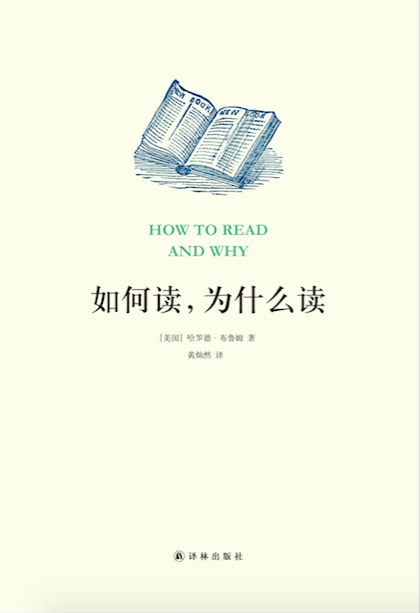
[美] 哈罗德·布鲁姆 著 黄灿然 译
译林出版社 2015-12
本文书摘部分选自《如何读,为什么读》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