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音通话、网银转账、线上购物、网络教学、家庭办公……互联网使得信息和资本的流动速度急剧增加。美国作家威廉·米切尔(William Mitchell)在1995年出版了一部名为《比特之城》(City of Bits)的科幻小说,将此类生活和工作方式做了建筑学意义上的考察:在“比特之城”中,电子邮箱地址成了一个人的居住地,万维网成为信息的跳蚤市场,工作和娱乐彼此缠绕甚至融合,社会公正则由人们对商务、娱乐和政治的虚拟空间的介入所决定。曾经形塑人类文化和社群和土地,以及个体的物理性流动和生物性衰退,被挤出了这座完全基于互联网科技而建造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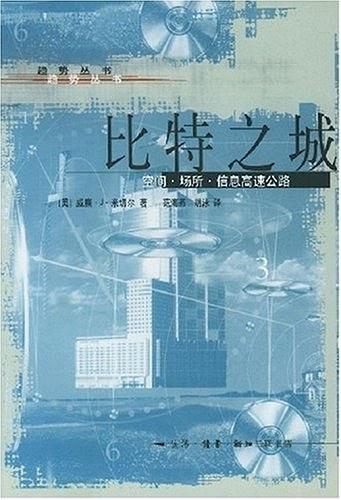
1989年,20世纪德裔加拿大著名物理学家、冶金学家、作家厄休拉·M·富兰克林(Ursula M. Franklin)在加拿大广播电台举办的梅西公民讲座中,借书中所描绘的“比特共同体”表达对资本和生产全球化的忧虑。他认为,互联网技术促进了比特共同体的扩展,使得投机和投资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由此带来了全球金融贸易与营利的牢固增长。而国家(nation state)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它们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为商业行为的实施制造政治氛围。学校、医院、铁路等公共领域向私人投资开放,孩童、老人或体弱者的需求和他们最信任的资源由此成为了处于地球另一端的资本家的利益来源。从历史中沿袭下来的规则和法律被曝露于“比特共同体”赤裸裸的金钱和权力关系之下,公平和正义亦被悬置于由资本和技术主导的博弈之中。
将视线拉回到富兰克林举行公共演讲30年后的今天。Facebook拟发行的虚拟货币Libra试图创造一个新的金融生态系统,《美国工厂》中所纪录的企业跨境投资行为势头不减,而与此同时,人们的信息安全正遭受着愈来愈严峻的考验,全球贫富差距亦不断增加。如果后者被视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代价,那么我们是时候思考:“人类文明的进步”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
《当全球化威胁人们赖以生存的根基》
文 | [加]厄休拉·M·富兰克林 译 | 田奥

我们把整个世界想象成一块圆形蛋糕,一块块的楔形蛋糕片是地区或国家。作为某一块蛋糕上的居民,我们与相邻的蛋糕片距离较近,与对面的蛋糕片距离则较远。在蛋糕片内部,我们可以把社会流动描绘成垂直结构的,比如在底层的面包屑、中间的葡萄干和顶层的奶油之间进行重新安排。由此,社群就是本地性的,代议制也是如此。民主有着本地的根源,它最初的实践就是在地方实现的:踢马道(Kicking Horse Path)地方议会的议员代表了名为加拿大的一块较大的蛋糕片中的一小部分。

在历史中,语言、法律和习俗被认为是依据地点而垂直分布的,而地点则取决于“切片”。外国语言或通用语的概念正是对于语言、文化和社群的当地本质的承认。然而“蛋糕切片”之间很少会完全孤立,跨越切口的交易——无论是国界还是族裔语言的边界——一直以来都存在,当然这更可能发生在相邻的两块蛋糕片而非相隔很远的蛋糕片之间。在历史中,人们曾穿越很远的距离到远方旅行,他们带着新见识、新知识和新货物回到家乡。我们可以把这种个人的、货物的和思想观念的交流想成一块“全球性蛋糕”的水平分层。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样的水平迁移受地理阻碍而减缓,并受到地方的或垂直的律法之限制。像护照、关税和边界监视这样的工具,保护垂直性活动免受水平迁移的侵蚀。许多技术创新,都设法推开对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水平迁移更容易实现:从改善海路交通的航行工具,到火车、汽车和飞机;从电报和无线电,到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这些东西都对跨界和跨国交易的增长大有裨益。还有一个事实是,现代生产技术所包含的规范性碎片,很好地给全球性工作分包和异步性的重新组装提供了帮助,由此你可以看到一幅全球化的蓝图。
我们都知道水平迁移日益增长的主导地位带来的现实状况:货物和部件在大洋彼岸制作出来,然后在本地出售;服务则由天知道在哪儿的电话中心的某位不知名通话员来提供;我们的新闻广播既报道全球各地的股票市场新闻,也报道本地交通信息。对于加拿大的公民来说,关于资金的全球流动路径的信息的即时更新,似乎与听到发生了一场可能导致自己上班迟到的交通事故的消息一样重要。
这些情形不是一夜之间到来的。水平运输日益增长的重要地位,需要助长与校准,从关税联盟、护照要求的放宽,以及旅行与货币管理力度的减轻开始。但是随着电子技术的出现,水平运输再次迎来了一次量子跃迁。说回我们的蛋糕模型,在一块蛋糕片的垂直内部,某些部分会比另一些部分从这些发展中获得更多的收益,而且往往——虽然也不是一定——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切片中所处的位置。
我们必须意识到,在垂直模式中,那些倾向于限制水平迁移带来的影响的律法,一定是由国家制定的,比如每个其限制和建构垂直模式的能力会被自发的水平迁移所阻碍的国家。水平迁移过程往往会将垂直模式的权力转移到水平模式之中,比如当一个民族国家让渡自己在跨国企业某些方面的管理权,或者当国际贸易协议相较于国家律法拥有优先权时。一个国家的统治装置常常会分裂成水平的小部分,这些小部分热衷于释放水平迁移活动,并由此试图削弱地方或垂直组件的黏性与力量,而后者只关注“蛋糕片”内部的情况。比如在加拿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或《多边投资协定》(MAI)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就呈现了水平力量与垂直力量之间的角力。

加拿大税务系统的变革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我们国家的垂直力量与水平力量之影响的更深刻的图景。1955年,加拿大政府所征的税收有43%来自企业,剩下的部分则来自个人。到了1995年,企业税收所占比例变成了11%。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产生这种截然不同的待遇的原因在于,当公民们被困在“蛋糕片”的内部时,企业能够在不同的“蛋糕片”之间滑行,直至寻找到更合适的全球避税港;而从公民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是关乎代议制和民主的,公民们可以发问:那些被选举出来的政府人员在制定法律和限令,或者同意相关律法的实施时到底是在代表谁的利益?是那块垂直结构的“蛋糕片”,还是构成了一整块“蛋糕”的水平切面?
蛋糕模型所能生动描绘出的全球化的另一个特征是,目前投资型资本主义相较于制造或生产型资本主义拥有绝对优势。在这里,我想引入“规范性技术”这个概念。这些规范性实践出现在18世纪中期,即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通过使用机器以及一种新的劳动分工方式,新技术极大地促进了材料货物的生产。在西欧以及之后的北美内部,规范性技术重构了工作,并为权力和资本的集中提供了新机会。在彼时逐渐兴起的技术秩序中,政府与商业的关系发生了改变,而且正如我曾用电力的分配作为例子所指出的,国家开始建立能促进随后的商业生产之增长的基础设施,同时鼓励消费与生产材料的获取。这种一般化的趋势一直持续下来,但其规模和范围扩张得更大,这基本上是依靠不断扩大的财政工作。这些事务还是可以被视作新技术与旧技术的应用成果之间的相互影响。
消费品的大量生产,即便是在高度自动化的设施和低薪酬、低开销的工作地点,也没有放弃无止境的收益,尽管有些人期待它们会放弃。这部分是因为那些最需要大量生产出来的货物—包括食物、药品和衣物—的人,就是生产出这些产品的人,但同时也是最缺乏购买这些产品的渠道的人。与此同时,那些拥有宽裕收入的人,则变得更加挑剔,对消费品也多少有几分厌腻。总而言之,消费主义已经不是它原本的模样了。
另一方面,比特共同体以及关于命令和控制的计算机技术,大规模促进了迅速的和异步性的现金业务。就比特共同体本身而言,它已然带来了全球金融贸易与营利的牢固增长。随着比特共同体的扩展,投机和投资活动范围也不断扩大。货物会在地方上有一个生产源头,通常是在垂直切片的某处,但钱币与投资基金不再被固定在某处。比如可以注意到,多伦多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场地不再是一个物理空间,它仅存在于比特共同体中。即便如此,交易所中的各种传输交易仍是真实的。因为它以二进制数字形式在全球做水平传送所具有的非透明化特性,会为真正存在的人带来收益或损失,给某些人以希望,给另一些人的则是绝望。

新出现的投资型资本主义对生产型资本主义的支配可以被视为商业与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转变:当对原材料的需求和对物质货物的贩售是营利的主导形式时,正如我在前面指出的,国家会在其中扮演积极的角色,通过使用管理和控制的相关工具,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为商业行为的实施制造政治氛围。由此,公民主要被视为消费者,并被鼓励变得像个消费者。营利方式从直接生产到投资的转变并没有改变国家积极支持商业行为的态度,但它极度改变了国家的支持策略。这些改变为国家与其公民的关系带来了显著的位移,这一位移我在前面提到的不多。
考虑到全球经济,它在世界的工业化国家的商业行为中已经变得十分明显,如果公共领域向私人投资开放,会带来极大的收益。从历史上来看,一个国家的非营利领域—从公路和公园建设到学校、医院和监狱—会被坚定地置于各自的垂直片区中。许多公共机构是被地方性的需求或普适性价值搭建和规训起来的,这些普适性价值中有一点是民主的信念,即认为某些人—比如孩童、老人或体弱者—的需求不能成为另一些人的利润来源。然而,最近许多公共领域功能的私人化,以及对这些领域的运作解除管制,意味着政府已经将垂直的、以社群为基础的工作(传统上委托给政府来监管)开放给了全球化投资的水平层面的力量。由此,国家将其公民最需要依靠的领域,以及他们最信任的资源,转变成全球市场的新投资机会。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个人是被公共范围还是私人领域侍候得更好,我想要争辩的问题是关于统治与责任的。摧毁公共领域,由于水平面的推力而失去垂直面的凝聚力,这些都深刻影响了社群以及人与人的联结。在没有对处于危机边缘的、更广阔的议题进行公共讨论之前,这一领域内的改变实在不应该开始。
并不是每一个技术上可能的事物,比如比特共同体驱动的投资型资本主义,对国家的福祉而言要么是可取的,要么是必需的,二者必居其一。在加拿大,对新技术施予人们生活的影响的公共讨论和地方性讨论很少影响到我们国家的政府管理,对此我深感悔恨。我害怕,我们这块“蛋糕片”正在我们没有首肯的情况下塌陷。
关于蛋糕模型就讲到这里。我希望这一模型能帮助我们看清,技术的真实世界—在这个世界,我们试图平静地生活和工作,只要一点点公正和平等—处于强有力的、相互竞争的力量之博弈中。蛋糕模型可以轻易地与我们前面的一些讨论联系起来。异步性是顺着水平切面的工作之基本特征,而同步性和共享模式则为垂直切面提供了大量的内聚力。清晰的是,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受到异步性实践和同步性实践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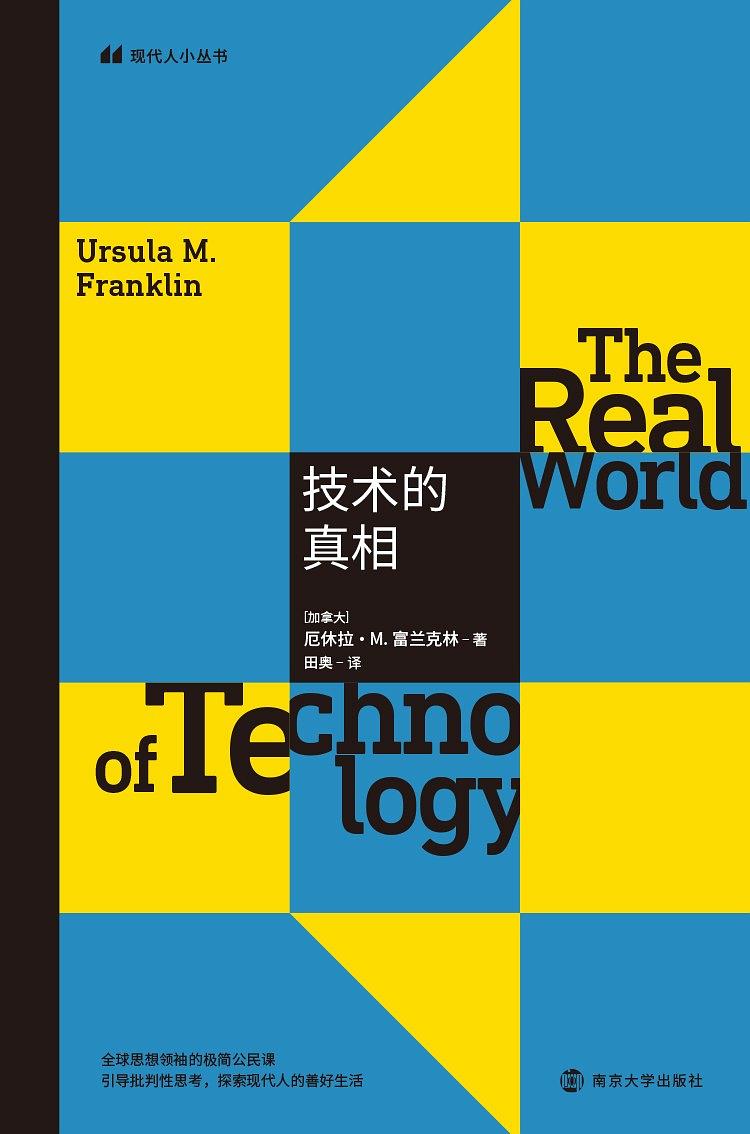
[加拿大]厄休拉·M. 富兰克林 著 田奥 译
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06
来源:三辉图书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