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想象中,北极是一片寒风呼啸的皑皑冰原,是一块未经触碰的极寒处女地,象征着原始与纯洁。但是,随着地球气候发生巨变,北极原本美好纯净的画面遭到了现代化进程粗暴笔触的破坏——这一切也许预兆着厄运将要降临。
芭丝谢芭·德穆思(Bathsheba Demuth)18岁时曾到位于北极圈内的加拿大育空地区(Yukon)学习训练雪橇犬,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带领我们前往白令海峡以及被海峡分隔的两边土地,使我们获得了一次拓展想象力的机会。读她的新书《漂浮的海岸:白令海峡环境史》(Floating Coast: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Bering Strait)令我们体会到:在一个曾在广袤的北极亲身游历和生活过的人的心中,北极是一个包容万象的丰饶之地,也是一个由人类以及数量不断起伏变化的野生动物种群共同组成的充满活力的动态系统。
德穆思是美国布朗大学的教授,她的这本新书呈现了她收集得到的第一手材料,并用抒情的语言为我们描述了北极大自然中正在发生的一切。听听那些驯鹿的声音:“鹿群移动时,无数只鹿蹄叩击大地的声响清晰可闻,每只鹿蹄上包裹着骨骼的筋腱都发出轻微的咔嗒声。但书中着墨更多的是发生在那里的历史事件,即有人类参与的事件。对于这些事件,德穆思以博物学家的眼光和学者的严谨态度来叙述。
作者写作《漂浮的海岸》一书的主要目的是调查和研究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末期,人类在白令海峡两边的陆地以及海上进行的各种活动。这是一本主要书写北极的书,地球的气候变化在书中只是顺便提到。该书的写作侧重点也聚焦于那片土地,而不是北极特有的诸如捕鲸、驯鹿放牧、金矿开采以及捕获海象的产业。德穆思揭露了这些产业对北极的生态系统造成的毁灭性影响——她用“外来者”来描述美国人和俄罗斯人,用“白令海峡人”来指代尤比克人(Yupik)、因努皮亚人(Iñupiaq)和楚科奇人(Chukchi)——她也暴露了这些产业在人类族群中制造的混乱与纷争,这些状况的标志就是对自然环境留下的影响深远的各种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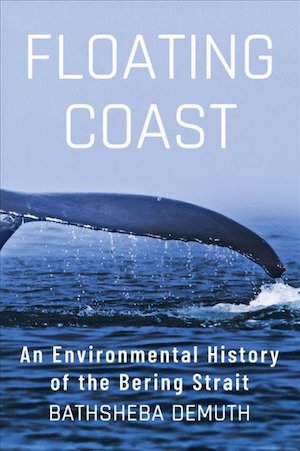
发生在北极的各种事件经常可以归结为能量的转换:“一切由动物皮草带来的财富都始于猎狐所付出的劳动:在雪地上奔走一天的长途跋涉,听到田鼠发出的响动时,像跳芭蕾舞一般轻巧地向前跃去等等。”精力和能量将田鼠、狐狸以及昂贵的皮草联系在一起,而且不断发生转化。能量也将人类世界与地球的其余部分联系起来。尽管人类抱有与此相反的幻想,但德穆思坚持认为,我们并没有与自然分离开来,也没有能够摆脱自然对我们的限制。通过像科学家跟踪观察狐狸行为一样来研究人类的活动,德穆思认为,人类的一些理念(例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自然的能量,类似于天气或病原体等。这些能量所产生的影响力也会波动和起伏。

德穆思写道,广袤的北极大陆见证了不止一种人类活动的模式,但是人类的活动只是“发生在白令海峡区域的众多生物活动中的其中一个主题”。她的书提出了一个关键论点,即其他非人类的生物也具有一定的能动性,而且整个北极的自然环境从来就不曾完全静止过。尽管如此,自从商业捕鲸业在白令海峡出现以来,那些外来者“已经将那里的生态空间从原本具有的多种复杂性,削减成为一个单一的商品来源地”。1848年,当托马斯·罗伊斯(Thomas Roys)船长和他的船员在如今的大狄奥米德岛屿(Big Diomede Island)附近捕杀了第一头弓头鲸后,他们将数千桶鲸油搬上了船,也将一种前所未有的、掠夺性的思维理念引入了北极水域。第二年,又有50艘捕鲸船抵达了这里。
这些捕鲸船都是受弓头鲸吸引而来,弓头鲸行动缓慢,庞大的身躯蕴藏着一只普通抹香鲸3倍以上的鲸油,还长有数量庞大的鲸须,鲸须可以用于制造从雨伞到医用刮舌板等数百种产品。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捕鲸者猎杀了数以万计的弓头鲸,据德穆思记载,“只有刚刚被杀死的鲸鱼才有商业价值。而这一切在鲸类动物生命的未来账簿上并没有留下记录。”从遥远的新英格兰航行而来的捕鲸者注意到了鲸鱼的智力,但是他们无法想象鲸鱼社群的状况,例如,鲸鱼发出的叫声,它们的叫声每年都发生变化,可以在鲸鱼之间传递各种信息。
捕鲸者也没有考虑过捕鲸行动对白令海峡区域原住民的生活造成的破坏和影响,原住民的生活原本是由熟练的传统技艺、独有的精神实践与社会秩序紧密结合在一起组成的。狩猎为原住民的生存奠定了基础,为充满诗意的各种宗教仪式提供了合适的场景。“居住在蒂基嘎格(Tikiġaq)的蒂基嘎格谬特族人(Tikiġaġmiut nation)在将弓头鲸的头颅骨推进大海之前,会用干净的水清洗它们,因为当回到大海后,其灵魂会游回自己的故乡,再次转世成为一头新的鲸鱼。”
20世纪初,科技进步(而非环保意识)减轻了北极弓头鲸的生存压力,遏制了弓头鲸的存活数量急剧减少的趋势。石油产品的应用使鲸鱼脂肪不再被大量需求,具有弹性的钢材的出现取代了对鲸鱼骨头和鲸须的需求。在情况最糟糕的时候,生活在北极的弓头鲸的数量只剩下约3千头。据德穆思记载,现在弓头鲸的数目已经不断增加。《漂浮的海岸》一书记载了一系列在工业化的影响下濒临灭绝的鲸鱼的故事,这些故事只是一个开头。生活在北极的鲸群在即将全部灭绝之前的最后时刻得到了暂时的喘息机会。

接下来受到影响的动物是海象,这时美国人的捕猎行动引起了俄罗斯的警惕,他们担心美国会在俄国的楚克奇半岛(Chukchi Peninsula)施加影响。与此同时,在19世纪晚期,美国政府也开始尝试将阿拉斯加原住民的生活方式改变成现代化的模式。这些原住民原本的生活方式已经因为外界的过度捕猎而被剥夺了。正当美国试图在白令海峡的东岸实施法律和经济方面的封锁时,与此同时,社会主义也开始在遥远的俄国城市显出雏形,但这时俄国的商人却发现白令海峡西侧的楚克奇人和尤皮克人聚集地出现了饥荒。
为了避免出现动物灭绝和人类饥荒等情况,美国和俄国都决定对捕猎海象设定法律限制。德穆思写道:“因为他们也同样也把狐狸和海象当作他们的经济基础,因此居住在白令海峡一带的原住民似乎也变成了美国人或苏联人。”对捕猎海象和狐狸养殖业进行监管是用于教化原住民的一种文明机制,而对于那些外来者,这种监管只存在于时间之外。
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在白令海峡的两岸此起彼伏地不断发生着。有时一些戏剧性的细节也使故事变得生动起来:例如,一位原住民猎人把浸满了海豹血的雪块扛回自己的村子用来煮汤;楚克奇族的一位萨满被苏联警察逮捕;还有二战期间驻扎在阿拉斯加的美国士兵从飞机上射杀海象。
如果美俄两国政府设法防止了海象的彻底灭绝,他们也以各自的方式迫使了白令海峡一带的原住民改变信仰。和居住在更南部的美国原住民一样,阿拉斯加的原住民被要求将他们的孩子送进政府开办的寄宿学校,在那些学校里面,孩子们如果使用自己的语言进行交流就会受到惩罚。在苏联,楚克奇人被迫从传统的雅阳嘎斯帐篷(yarangas)搬进现代的公寓楼房居住。
在逐渐消灭原住民文化的同时,美国的狩猎法也将原住民猎人归为“自然遗产的恣意挥霍者以及不文明的人”,并且以西奥多·罗斯福式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Theodore Roosevelt–style conservation,由前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20世纪早期发起,旨在通过法律和行政命令保护动物和土地免受商业活动的侵害,他认为“公众对自然资源的权利大于私人权利,必须首先考虑”——译注)的名义,禁止原住民猎人为维持生计而进行的狩猎活动。尽管如此,德穆思写道:“猎人穿越冰原,到国家司法权管辖的三英里界限之外去狩猎,然后再到阿拉斯加州诺姆市的后巷出售非法猎得的海象牙。”被困于这种侵入性的经济体系之中,尤皮克人和因努皮亚人想方设法将自己对海象的理解与新的市场现实结合起来,在他们的传统观念中,海象是一种在杀戮前和杀戮后都必须为之举行某些特定仪式的动物,因为它们日后可能转世成为人类,也可能继续转世成为海象。
随着德穆思的故事的继续深入发展,我们了解到当时社会主义的苏联和资本主义的美国在自然资源保护的问题上开始出现越来越混乱和不合理的现象。苏联人在他们制定的五年计划中表示,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无限量地繁殖和饲养驯鹿,想要多少就可以养多少——“完全突破极限这个概念”。美国人则试图在阿拉斯加“保存”一种驯鹿畜牧文化,而这种所谓的文化根本就不曾存在过。

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苏联政府,都拒绝承认驯鹿群的数量其实是会出现自然的增减波动的。两国政府都曾向狼群宣战,他们这种进行人为干预的想法,就是造成自然界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在冻原之上,一个狼群的存在就是对鹿群数量的一种适当限制,而且这种限制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德穆思写道。然而在阿拉斯加,政府为伊努皮亚特人提供了一项赏金,鼓励他们射杀在他们的族群传统中被奉为祖先的狼;苏联人则宣布了以彻底消灭野狼群为他们的奋斗目标。
《漂浮的海岸》在最后一章又回到了开头时讲述的捕鲸的故事,在这部分德穆思的叙述是最强有力的。美国捕鲸业衰落后,鲸鱼享受了数十年的安全和宁静,之后挪威和苏联的捕鲸人又开着威力强大的新式捕鲸船抵达了白令海域。这一轮捕鲸热潮的掀起主要是因为需要大量的鲸油来制造人造黄油。到了1920年代晚期,另一股热潮又开始了。
早在1931年,通过条例监管来保护鲸鱼的迫切性已经成为了当时的国际话题。但是直到40多年后,也是在进一步接近完全灭绝的境况之后,鲸鱼才得以逃过被捕猎的命运,从而安全地生活在大海之中。这段时期,苏联人再次将制定捕杀鲸鱼的配额当作他们的道德指南针,正如德穆思在书中所写:“他们的视线就停顿在海平面上,停顿在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之外,而动物的未来已经被他们剥夺殆尽。”如果你认为苏联捕鲸者的行为很残忍,德穆思还描述了鲸鱼幼崽为了跟随还在哺乳期但已经死去的母亲,试图游上捕鲸船的情景。西方国家的技术专家也显示出了同样的冷漠无情,在他们眼里,鲸鱼不过是供人类使用的一种资源。
德穆思写道:“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段历史,能够把19世纪和20世纪鲸类动物的惨痛经历用人类的语言描绘出来。人类对数代鲸类动物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这些话语所具有的道德力量是以这位博物学家早期谨慎的学术著作为基础的。
尽管大多数人对北极都没有任何深入的了解,但是每当我们思考气候变化这个问题时,都会想到北极。那里冰原的大幅减少就是危机即将到来的征兆。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部分原因在于人们总是错误地认为北极一直没有变化,直到全球的碳排放使北极的冰原从内部深处开始融化——一个永恒的反伊甸园。
显然,德穆思清楚,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她曾经在北极居住,并对它的历史进行过深刻思考。她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北极从来就不是一片静止的陆地。在有关自然进程方面,她的理论是令人信服的。她帮助我们看到北极正在发生着的变化,以下这段文字也帮助我们了解了气候变化周期如何影响驯鹿群的生存状况。
在炎热的夏季,北美驯鹿拒绝进食,因为它们的身体,尤其是腹部,深受四处肆虐的昆虫所害,母鹿的身体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使它们无法孕育小鹿。狼群很容易找到猎物(……)但是,在那神奇的十年里,北美驯鹿的数量出现了激增,当小鹿长大并且能够四处游荡时,驯鹿群的迁徙区域就会扩大。在一些地方,鹿群啃食地衣和灌木丛,直到它们经过的土地变成光秃秃——于是这又成为了对初生的生命的一个打击。
德穆思希望我们知道,白令海峡的人类历史同样也是一种动态的历史,同样充满了各种抗争和协商,而那些被她称作“白令海峡人”的原住民们,也绝不会是所谓的永恒的图腾。确实,使白令海峡区域的历史变得充实起来,会成为将人类毁坏原始荒野的默认叙述变得复杂化的关键。这一切都令人想起了美国记者查尔斯·C.曼恩的《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书中详细记载了在哥伦布抵达美洲大陆之前,那里的原住民社会已经拥有的复杂的文明,以及后来对他们的征服和各种动荡。
相比之下,书中对北极一带原住民的记载和叙述就显得有些过于简略,达不到曼恩的书的高度。她喜欢运用类似电影、电视的冷开场技巧(cold open,电影、电视节目中的一种叙事技巧,指在片头或片头名单播放之前就直接跳入故事情节,有理论认为这种作法能够让观众尽快融入到情节当中,从而减少他们在片头广告中换台的可能性——译注)为读者介绍居住在白令海峡一带的人。书中有一章是这样开头的,“当马凯卡塔克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夏天都是在位于辛计科的半地下的草皮房子周围玩耍度过的。”然后接着讲述了马凯卡塔克如何成为拥有驯鹿群的私营牧场主的故事,而“当地政府一直认为马凯卡塔克是汤姆斯·巴尔”。马凯卡塔克这个人物后来在本书的同一章中又出现过几次,而且总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突然现身。
这个人物和有关他的传记值得读者关注,但是在德穆思的书中,我们难以找到相关记述和资料,德穆思只是用一种客观而且保持一定距离的方式将该人物呈现。德穆思的书中还出现了一些读者不熟悉的地名,但又缺乏上下文语境或解释,对于读者在阅读中的定位没有什么帮助(阅读此书时,如果读者不用通过自己查找地图,就能够得知原来辛计科(Singiq)是位于阿拉斯加州苏厄德半岛的一个城市,那将会让人感觉很有帮助)。德穆思过于凝练的散文式文笔很难令读者对北极一带原住民的生活或历史产生深刻的感受,从而使读者改变对北极一带的固有想法。
由于《漂浮的海岸》一书只是对北极环境的持续恶化进行了一种线性的叙事记载,最后使读者感觉该书旨在讲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一个原本平衡的自然世界的侵入,因此读者需要在阅读时自行得出以下结论:有关气候变化这个几乎不言而喻的事实,只不过是人类漫长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又一个最新的悲剧。该书最终证实了一个我们早已确信的事实:在我们抵达北极之前,这片极寒的冰原大陆一直拥有着自己的和谐,而外人强行带给北极原住民的各种改变,最后几乎抹杀了他们因为独特的生活方式而产生并积累的各种智慧。
这造成了一种错失的机遇。几代人以来,我们一直坚持,排斥我们是原住民的入侵者的说法。原住民只不过被看成供现代文明社会掠夺的自然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德穆思的讲述令读者产生了一种挫败感,其实这是读者最不应该得到的感受。相反,读者应该通过阅读,对北极以及北极的原住民文化产生出一种更灵活、更有希望的理解。
本文作者Erika Howsare是一位居住在弗吉尼亚州的诗人、记者,著有《旅行如何以一种折叠的方式展开?》(How Is Travel a Folded Form?)一书。
(翻译:郑蓉)
来源:洛杉矶书评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