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源自美国时间用途调查(American Time Use Survey)的研究发现,父亲较母亲更快乐、压力与劳累度也更低。可以肯定与此有关的是,人们经常观察到,即便父母都是全职,母亲的家务和带娃任务也比父亲重。当母亲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时,她仍需肩负管理家事的精神负担,据美国网站Slate的说法,母亲从事和规划家庭活动、日程安排、假期和采购,管理家庭财务以及维护房屋的几率是父亲的三倍(自认为家务平分的男性比女性多一倍)。在其不成比例的贡献之外,全职母亲因工作影响育儿而产生的负罪感也比全职父亲强。就全职母亲的这种体验而言,一种常见的解释是——与其它许多社会病类似——其原因在男女没有“遵循自然的生活方式”。这种思路认为,男性自然而然地是统治者,而女性自然而然是持家者。
但父权制(patriarchy)不是人类的“自然”状态。这是个很现实也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数据,全世界至少有1.26亿妇女和女孩因源自性别选择的堕胎、杀婴或不加照料而“失踪”。在某些国家,女性无权无勇,本质上被当成不成熟的人,未经男性允许不能旅行、驾车甚至露面。英国虽然有平等相关的立法,但每周平均仍有两名女性死于男性伴侣之手,且暴力从少女时代就开始了:上个月有报道称,每16个美国女孩里就有1人的初次性经验是被迫的。从全球来看,有82%的部长级职位都由男性担当。诸如物理学这样的专业领域也基本都由男性主导(女性贡献的认可度也更低——只占科学类诺奖得主的2.77%)。
在某些坐拥教授席位、向来不缺追随者的名流(主要为男性,主要是心理学家)看来,社会中男女角色和地位的差异有重要的生物学理由。例如,史蒂芬·平克就认为男性倾向于和“事”打交道,而女性则爱与“人”打交道。他声称,这解释了为什么在(薪酬微薄的)慈善机构和健保领域就业的女性更多。在平克看来,“光谱上与‘人’一端最为匹配的职业就是社区服务组织的负责人。与‘事’一端最匹配的职业则是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程序员和生物学家。”
其他一些人甚至否认社会上存在性别歧视,坚称我们所见到的性别角色是基于认知上的差异——剧透一下:就是说男的更聪明。“那些认定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压迫性的父权制的人不愿承认,如今的等级制可能是基于竞争力的。”乔丹·彼得森就这样看。其论述认为,女性若去探索自己的传统性别角色,不去跟上述这点较劲的话,将会过得更幸福。诸如此类的理论已经被不少学者驳倒,如神经科学家吉娜·李彭(Gina Rippon)和心理学家科迪莉亚·法恩(Cordelia Fine)。
男女之间当然有生物学上的差异,如性解剖学和荷尔蒙等方面。但这种差异并没有表面上那么泾渭分明。例如,大约每50个人里面就有1人具有非典型的染色体或者荷尔蒙特征,即有“雌雄同体”的成分——这个比例大致与一头红发的人相当。男性的大脑总体上比女性稍大一点,基于大样本的扫描表明,男女特定脑区的大小和连通性(connectedness)存在差别,譬如海马体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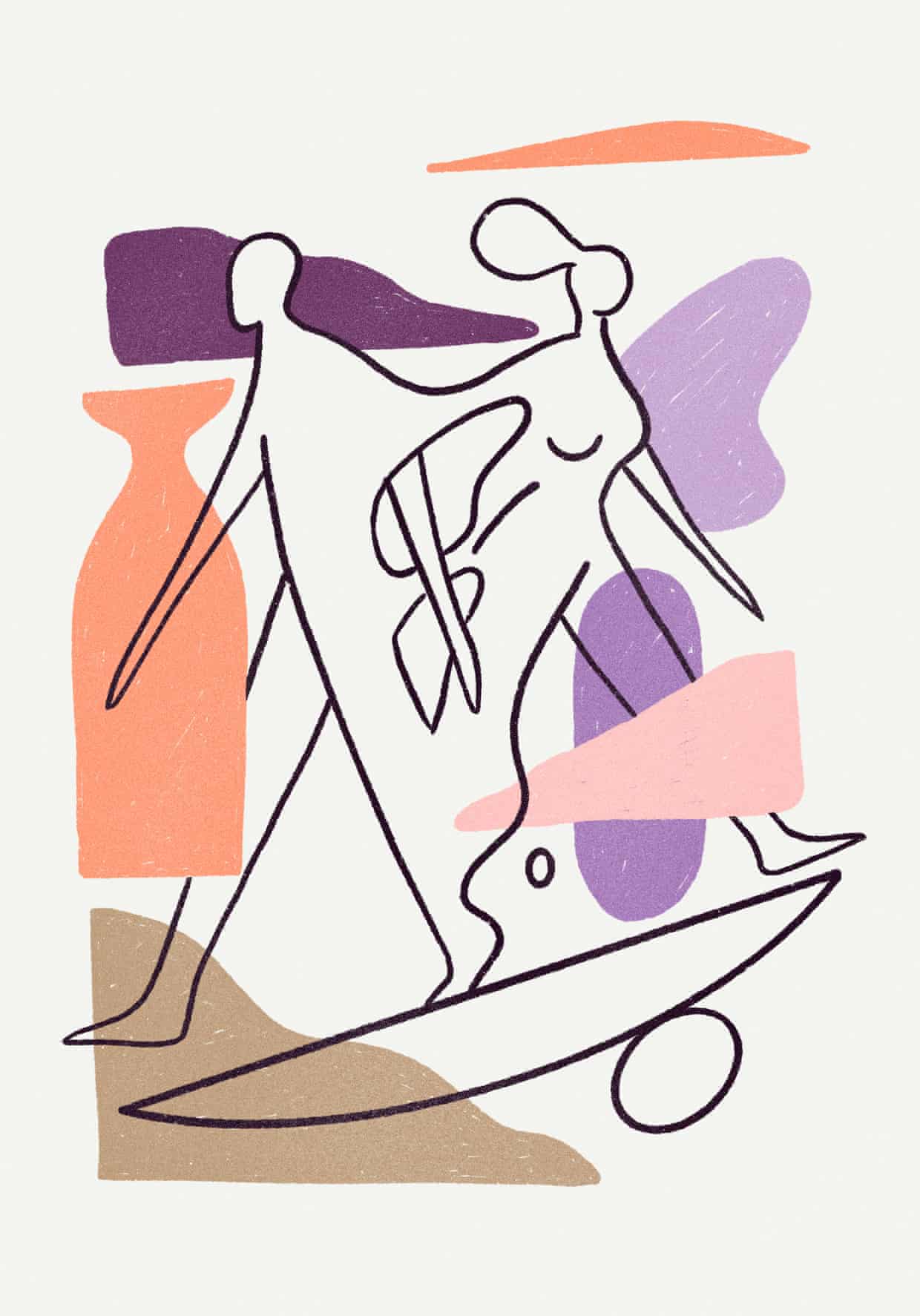
然而只有极少数的(比例在0至8%之间)男性和女性个体具有所谓典型的“男性”或“女性”大脑。不少研究表明,大部分人都是居中的,至于谁在数学、空间感、领导力和或别的与性别有关的属性上表现得更好,单靠生理性别无法预测。从解剖学以及认知上讲,某一性别内部的差异要大于两性之间的差异。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女性在进入多由男性占据的职业和社会地位时表现比男性差。当女性有机会担当某些“专属于男性的”角色时,其专业程度是旗鼓相当的。例如,近来有学者推算出,诺奖性别比例的失衡源自对女性的偏见,而不是女性参与度本身就低。换言之,我们在生物学里找不到父权制的根源。
男性霸权虽然无处不在,但它却出人意料地是个新现象。有坚实的证据表明,父权制社会的历史还不到一万年。人类最初很可能是平等主义的物种,并且将此生活方式延续了数十万年。证据之一在于人类的雌雄数量大致相同,在类人猿里是最均衡的,这意味着男性统治不是我们这个物种的驱动力。事实上,我们早期生活中的性别平等很可能在进化上是有益的。父母对女儿和儿子(及来自两方的孙辈)的一视同仁令我们的祖先有了一种生存优势,因为这有利于构建至关重要的、广泛的社会网络,以交换资源、基因和文化知识。
如今,狩猎-采集社会依旧因其性别平等而备受瞩目,这不是说男女必须做一样的事,而是说其它一些社会里并没有普遍的、基于性别的权力不均。在坦桑尼亚的哈扎人(Hadza)这样的当代狩猎-采集群体里,男女贡献的卡路里数目相同,且共同照料小孩。男女在决定群体生活地点及邻居时的影响力也大致一样。

在远古时代,母系社会或许是更加常见的。强力的女性关系有助于团结更大规模的社群,而可以请朋友来代管孩子这一点也让我们的祖先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来为群体提供食物或从事其它活动。事实上,有不少社会是以母权制(matriatchy)为纲的——我曾经到访过的就有哥斯达黎加以种植可可为生的布里布里人(Bribri)以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以种植稻米为生的米南卡保人(Minangkabaus)。这些社群的土地所有者和决策者都是女性。
换言之,人类并非在基因就注定要接受男性统治。父权制和母权制——或者说一个更平等的社会——并没有谁更“自然”。与此相似,坚持“石器时代”饮食的人和爱吃泡泡糖口味的棉花糖的人没有谁更自然;无论想要和男性还是女性发生性关系,抑或是三个男人群交,也是如此;想住在稻草小屋里的人和想住在海底的玻璃泡里的人也无所谓谁更自然。理由在于我们与动物不同,我们是文化性的存在者——对我们这个种群而言,文化就是我们的本性,也是理解我们行为与动机的关键。
社会性、技术性和行为性的发明是我们本性的一部分——亦即人之为人的意义之一部分。文化对我们的驱动力比本能(instinct)更强。我们的文化也影响着我们的环境和基因。这种高度灵活、易于积累的文化可以让我们进行自我创造,哪怕我们会把自己的成败归结到基因上。
这不是说某项文化特质只要出现了就一定是“好的”。例如父权制的规范就对我们的健康和社会有害,它带来了死亡和痛苦,也限制了人类的创造潜能。但我们既不是生理结构也不是社会规范的奴隶——即便我们很容易产生这种感觉。
人类的文化影响从出生就开始了,社会规范甚至在出生以前就开始发挥作用: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孕妇得知了胎儿的性别,其对胎儿活动的描述就会出现差异。得知自己怀了女孩的女性一般会称其活动为“安静的”“非常温和,翻滚多于踢打”;而如果知道自己肚子里是男孩,则会有诸如“动作非常有活力”“踢打和冲撞”“活脱脱一个小炸弹”。

许多我们认为具有普遍性的观念不过是我们自身文化里的社会规范。例如,自由、平等和博爱在法国可能是值得为之而死的价值,但个人自由对其它社会而言可能就不那么重要或者可欲,这些社会可能更强调诸如纯洁之类的价值。不妨想一下责任的观念。在我的文化里,如果你有意伤害到某个人或者其财产,那与无意间的作为相比就是更严重的犯罪,但在其它文化里,儿童和成人受罚的程度所参考的乃是行为的后果——意向性被认为是不可捉摸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不相关。
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或者族群之间的差异并不能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智力、同理心或者功绩究竟如何。现代人99.9%的基因都相同。虽然我们离开热带的进化舒适区已经有数万年,但还没有分化——没有变成两个或者更多的物种。我们的祖先并不需要作出剧烈的生物学调适来迁就我们所居住的不同环境,理由在于我们的进化发生在文化上,继而分裂出了具有不同适应性的多种文化,它们各有各的社会规范。
左右我们的思维、行为和感知世界的方式的并非基因,而是文化发展的熏染。例如,有研究比较了西方人和东亚人的神经处理过程,发现文化决定了人们如何看别人的脸(西方人会扫视双眼和嘴构成的三角区,东亚人则聚焦中心)。语言揭示了我们的规范并形塑了我们的思维。说希伯来语——一种性别色彩相当鲜明的语言——的小孩与说性别色彩不显著的芬兰语的小孩相比,知晓自身性别的时间要晚一年左右。英语使用者比日语使用者更容易记住事故的始作俑者,例如谁摔碎了花瓶。理由在于英语的表达是“吉米打碎了花瓶”,而日语在表达里不太重视因果关系的主体,他们会说“花瓶碎了”。语言中的一系列结构极大地影响了我们构造现实的方式——其结果就是,我们对现实和人性的认识高度依赖于我们所说的语言。我们所接受和响应的文化输入可以改变我们的大脑,重构我们的认知。
许多社会规范之所以产生,在于其有助于生存,譬如有促进群体团结的措施。但社会规范也可能有害。认为一个人的肤色或性别可以左右其品格或智力的看法没有任何科学根据可言。不过,社会规范确实可以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和生理结构。如果有社会规范把特定群体划为等级制中的底层,那就会有人在这上面做手脚,令这一群体在财富和健康方面的表现恶化,以维持社会规范。伯克利的学者主持的一项针对30000名轮班制劳动者的大型研究发现,拉丁裔和其它少数族群劳动者——尤其是女性——的工作时间表很可能更不规律,能感知其有害影响的不仅是劳动者本人,其子女的起居也变差了。
将我们的行动归诸于基因和生物学基础,可能会有一种危险,那就是个人和群体在生活中无法享有平等的机会并受到伤害。说到底,我们很容易认为穷人就是品格差、不配享有好生活、有道德缺陷或者愚蠢,而非深刻的、不公平的系统性偏见的受害者。类似地,我们也很容易认为某个人的成功就是源自其天赋才能,而非运气和社会地位。
如果我们一定要认为存在某种自然的——以及最佳的——做人之道,那我们就蒙蔽了自己的双眼,无视了多种多样的、潜在的存在、思想和感受方式,并把社会限制强加给了那些生活选择并非比我们更不正当的人。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我们以往坚信有生物学根据或者来自上帝诫命的规范已经被社会改变了——这种改变有时还十分迅速。如果我们发明了它,那我们就能改变它。一种广为接受的、存在了上千年的“自然”状态可以在区区几个月里就翻天覆地。
(翻译:林达)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