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棒的博物馆往往坐拥数不完的艺术珍品、宗教文物、金银珠宝以及各个年代不同地域的玩意儿,而它们的创造者,正是历史上殖民地的原住民。他们的劳动创造被掠夺,然后输送到各处博物馆里。在这条进出口的物流之路上,考古学家、传教士、探险家、艺术收藏家,甚至连走私犯都作出了杰出贡献,而其目的地往往都是欧洲或者美国。今天,这些文物转移的航线似乎掉了个头——诸如牙买加、希腊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正在对美国和欧洲喊话,要求那里的博物馆归还文物古器和早期人体遗骸。人类学者、博物馆高级策展人奇普·科威尔(Chip Colwell)今年4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博物馆归还文物,似乎是不久前才开始的。它们每送回的一件文物,都不仅是一笔孤立的文化遗产,“而且象征着一场战争,事关历史上殖民地的臣民,以及博物馆的未来。”
有时博物馆不肯轻易投降归还文物,他们往往会用稳定的制度保障作为托词,有了这一点保障,玻璃箱中的文物就能与更加广大的观众见面。这些博物馆在19或是20世纪得到外面的宝贝时,也随之开发出一整套保存与陈列文物的方式,并且不断优化。大英博物馆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我们相信,藏品的力量在于其广度和深度。这也让成千上万的游客得以通过展览,了解世界的各种文化以及相互之间的关联。”
这么看似乎没毛病,但这条逻辑依赖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展览方式——博物馆从一开始就挪用了艺术文物,将它们抽离出其原本所在的环境。特别是展览用的玻璃柜,它们将展品与其原生文化割裂开来,孤独地摆在博物馆中,然后百般尊敬祭上神坛,这样一来就为这件文物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语境。展览的过程中,文物被周围的环境同化了,而且逐渐化为博物馆藏品的一部分,让人们以为,“博物馆中的一件展品”,就是这个物件本质的真实属性。我们关于文物归还的讨论往往会忽略这一同化的过程,因此没有意识到,正是这种展览的技巧创造出一种对所在博物馆的虚假归属感,这一点正是文物回家路上的绊脚石。
2018年的西班牙电影《博物馆》(Museo)就通过强调其故事本身的复刻,从而捅破了博物馆文物这个似是而非的真实性问题。这部电影以真实事件为蓝本,重新演绎了1985年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Anthropology)里大量中美洲珍贵展品一夜之间不翼而飞的故事。《博物馆》放大了博物馆一开始在把某个物件纳入馆藏时带来的这种文化位移,在电影的描绘中,这是一个有借无还的世界。这部电影本身就是一件赝品,复刻了我们失落的历史——尽管这个版本永远没法满足我们的愿望,人们依然想要把原件切切实实地捧在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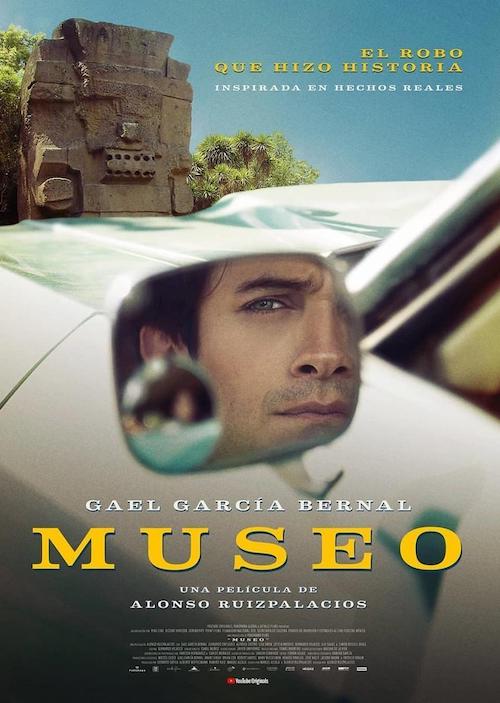
关于1985年博物馆失窃案,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推敲:警备松懈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窃贼在圣诞节前夕潜入博物馆,馆内基本没几个安保人员值守,窃贼只需要撬开玻璃柜、搬走文物就大功告成。这些安全系数低到令人发指的玻璃箱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遗物,曾经也称得上是一种新潮的方法,用来封存大英帝国四处搜刮来的战利品,并且展示给大众。玻璃比以往的材料都坚硬且便宜,让十七、十八世纪私家住宅里厚重古董橱上的文物被一件件搬下来,在公共机构里继续自己的使命。

在今天看来,玻璃柜和博物馆展览似乎已经成了同义词,这一状况也多亏了19世纪的发展演变。在那个时代,一整套关于文物收集、保存和陈列的规则惯例迅速建立起来,玻璃箱还有着归类文物的作用,昭示着其收藏的深度和广度。它们还能保持观众与文物之间的距离,令其可远观而不可亵玩,此举同样也彰显了展品的价值——必须采取措施来保护它们。博物馆的展览不仅能让人认识到这些文物的价值,更能让观众通过标本增进对灭绝物种或者是远古人类的了解。有学者称之为“博物馆效应”:一件物品与其所在的原始环境分离,来到博物馆中便成为了标本、艺术品,以孤立的形式存在。在这种语境下,参观者就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他们会将柜中文物理解为整个信息系统的一部分——从原来的文化背景中抽离、分类,打上标签并被吸纳到一个新的系统中。这样一来,博物馆可以理解为一个庞大的知识帝国。
放眼一个单独的国家,“博物馆效应”可以很好地解释1985年博物馆盗窃案在民众当中引起的反响。馆中的奇珍异宝被盗了两次——第一次是从文物原本的环境中被转移到博物馆的展柜里,而公众往往只会关注到第二次的偷窃,在他们的认知中,这些物件是统一的墨西哥文化遗产,而不是在殖民地环境中被攫取,而后被陈列在帝国首都一个单独的展室里的东西。这样的博物馆效应导致文物断了历史的根,在人们的眼里,它们只是现代墨西哥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隐去了背后带有地区特色、中美洲文明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墨西哥的官员和媒体纷纷立马把矛头指向偷盗策划者,说“外国势力虎视眈眈,这些犯罪分子是收钱卖命”。专栏作家乔尔·赫尔南德斯·圣地亚哥(Joel Hernandez Santiago)曾经在《Punto》周报上如此评论美国,“这是一个没有自己独特的宝贵文化传统的国家,因此只能从别的国家抢劫、偷盗和购买。”这让本身就令人唏嘘的抢劫案填上了一层黑色幽默的味道。另外,1985年盗窃案的真正劫匪是几位年轻的兽医学生。在电影《博物馆》中,编剧对此做了一番文章,给嫌疑人安上了胡安·努涅兹(Juan Nuñez)和本杰明·威尔逊(Benjamin Wilson)的身份,这两人都是一事无成的无业游民,因为人生步入歧途而想到一些出格之举,跑到博物馆来偷东西。
胡安是这场盗窃案的罪魁祸首。他多年来备受家人的奚落和嘲讽,决心做一桩惊天大事——偷窃博物馆。最终,与家人坐在一起看新闻快报的时候,他还在电视上发现了自己的丰功伟绩。博物馆公开向墨西哥的百姓发出警报,“这些小偷是墨西哥历史和文化遗产的敌人。所有墨西哥人应该团结起来,反对这种可耻的、不爱国的盗窃行为。”警方把“反派角色”定义为“不爱国”,博物馆就又能抓住机会,将文物收拢到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统摄之下——当然这么做就抹去了它们更为复杂的过去。不过历史的痕迹在胡安和家人的脸上可见一斑。他们生活在首都,算得上是个中产之家,地位更像是殖民者,被殖民者的属性比普通人淡了许多。甚至连警官都把胡安叫做“白鬼”(whitey)。
胡安全家人得知博物馆失窃的消息,纷纷对此嗤之以鼻。胡安的父亲字字铿锵,说这些文物是“我们的历史”。这部电影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谁?玛雅国王的死亡面具能代表胡安的民族吗?胡安的父亲接着说,“这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这是文物唯一的价值。”电影对这句话是肯定的。他们已经尽量找最轻便、最珍贵的物品带走,但到头来还是发现这些东西毫无价值。随着小偷跑路,《博物馆》也大体上沿着抢劫案电影的套路发展,但因为这些赃物辨识度太高,到处都被通缉,他们的出逃之路也戛然而止了。一位富有的英国艺术品收藏家给了他们一个忠告:“它们可能一文不值。”

《博物馆》改造了原本没多大价值的真实事件,充分挖掘虚构的叙事潜力,电影一开头就宣布,“这是原件的复制品。”文学家塞蒂亚·哈特曼(Saidiya Hartman)曾说过,“所谓过去,‘当时发生了什么’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对当下的欲望与不满。”为了勾勒这种欲望与不满,《博物馆》创造出新的故事,填补真实事件里留下的空白:在玛雅古迹里奔跑的野鹅、家庭闹剧,以及一个全新的结局。电影的创作团队希望电影本身的“伪造”能让人们看清所有历史背后的虚构成分,并且看到我们失落的过去。
在这样的思路底下,电影中的人物会充满爱意地抚摸着偷来的文物——其中包括萨巴特克人雕像、阿兹特克风格的黑曜石花瓶,以及17世纪玛雅国王帕克尔的玉制葬礼面具——目不转睛,爱不释手。摄像机的镜头也锁定在这些物件上,两个小偷沉醉在没有玻璃柜保护的绝对触感中,不停地抚摸,甚至想要出动舌头,简直停不下来。从玻璃柜里取出藏品的场景长达12分钟,镜头紧紧盯着敲开一个个玻璃箱的工序。锁被撬开,木制外壳掀起,有机玻璃也被热丙酮融化了。窃贼的手电筒取代了博物馆的陈列灯,以奇特而不专业的角度映照着这些宝贝。

这部电影的戏剧性不在于他们最终会不会被绳之以法,而是拆卸玻璃柜子、将每件文物从神坛上拎起,再放到人间日常柴米油盐中的这个过程。胡安和本杰明轻手轻脚,用旧T恤将它们包裹起来,穷尽一切心力来照看这些东西——尽管他们的照顾,不管是对文物、对家人还是对彼此都远远不够。这些宝贝离开了玻璃柜之后几乎立刻失去了光环,最终落得和日常物品一样的下场,被拿来装水、喝可乐或者是搭沙堡。
没法把赃物变现的确失策,胡安和本杰明最后还是怂了,决定给把这些文物还给博物馆(在历史上,1985年盗窃案悬而未决,拖了3年)。哪料想胡安最终玩火自焚,没能控制住自己,去参观了原本收藏这些东西的博物馆。他手握着帕克尔国王的葬礼面具,全然不顾观众和保安,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其放在玻璃箱顶部。终于迅速被警察拿下。
然而,在这个展示柜里,这幅玛雅面具已经被一件复制品代替。旁边立了一个标志,写着“这是原件的复制品”,与电影的开场白遥相呼应。尽管电影不是百分之百照搬真实事件,博物馆里的面具也不是真品,但它们还是揭示了某种真理:过去只是现在的一个版本。胡安抱怨说,他不喜欢历史,因为“它们都是编出来的”。但电影也通过“编造历史”,反驳了这位主人公的观点。当被问到电影的历史真实性时,导演阿隆索·帕拉西奥斯说,“为什么要为了讲真话而毁了一个好故事呢?不忠于历史的捏造戳破了准确还原历史的假象,但却让虚构电影更有深意。”
虚构故事和复制品的制造也许是一条更好的出路,唤醒人们,关注到我们到处都是文化错位的历史和失落的过去。在电影结尾,空空如也的展示柜恰如其分地捕捉了这种失落。所有失窃物品的展柜里,只有那个翡翠面具被复制品占了坑,其他的都特意留空。胡安久久徘徊在空荡荡的玻璃箱之间,陷入了如梦似幻的回忆中。在这里,每一个展示柜都是一座闪着光的纪念碑,吸引着如潮的游客——可是在柜子里保护着文物的时候,博物馆反倒是门可罗雀。此时传来画外音:“每个人都想看空箱子,博物馆盛况空前。”
《博物馆》虽然没怎么提及更大的文物归还问题,但依然点出了陈列柜背后的暴力,以及展览的合法性问题。电影指出,打开玻璃柜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种暴力,这些被偷走的文物身上没有保存着真实的历史,它们实际上也都是复制品——是来自古代文明货真价实的原件,但套上了一个改写过的历史,他们的真实故事只能通过虚构作品表达出来。
本文作者Megan Ward是俄勒冈州立大学的英语助理教授,著有《恍若真人:人工智能和维多利亚时代的现实主义特质》(Seeming Hum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Victorian Realist Character)一书。她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故事、当代文化与政治领域的文章多发表于《大西洋月刊》和《华盛顿邮报》等刊物。
(翻译:马昕)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