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宗教狂热和政治上的溜须拍马猖獗不已、为害尤甚,令人鼓舞的是,对某些人而言,成为世界公民仍是最高的理想。
奥兰多·费格斯(Orlando Figes)的《欧洲人:三人行与普世文化的建构》一书告诉我们,19世纪的画家、音乐家和作家能够通力合作、彼此学习而无关各自的国家出身。这种充实健康的国际主义造就了一批堪称西方文明最高成就的艺术巨作。比较之下,英国退欧后的边境墙无论是象征性的还是实质性的,都只是地方主义、小肚鸡肠和衰颓的不祥信号。
标题中的三人分别指女高音歌手宝琳·维亚多(Pauline Viardot,娘家名García),她的法国丈夫、艺术收藏家、经理人路易·维亚多(Louis Viardot)以及“偶尔情人,长期友人”的俄国小说家伊万·屠格涅夫。这三人一同或分别与同时代几乎所有文化名人都打过交道。你大概找不到几个不为宝琳的歌声而陶醉的人——其力量让沙皇也为之折腰,令查尔斯·狄更斯也不禁潸然泪下。而路易也是学富五车,曾出版过一部论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影响的历史论著,还推出过此后极为畅销的欧陆艺术博物馆导览手册。而屠格涅夫也是厉害角色:其雅致且不乏忧郁气息的小说赢得了托尔斯泰、福楼拜、莫泊桑和亨利·詹姆斯——不是你们这些普通的迷弟——等人发自内心的钦佩。

虽然三人的传奇经历令费格斯的故事内容充实、八卦不断,但他并不打算把这本书写成单纯的名人传记。相反,三人彼此交叉的生活里的各种细节和桥段,乃是费格斯用来讨论当时的社会和文化史的素材:早期的铁道旅行,音乐的发行,作家的合同与版权法,画作在艺术馆里的展出,外光派(plein-air)绘画的兴起,甚至还谈到了因煤气灯而大为延长的闲暇时间。
从某种意义上讲,费格斯的书和《项狄传》一样,几乎处处都在偏题。屠格涅夫想要宝琳的照片这件事引发了下文有关摄影术之诞生的一长段讨论。当这位俄国作家提到自己在意大利旅行时手里有一本约翰·穆雷(John Murray)的导览时,费格斯由就组织化旅游业的兴起写了几大页的评注。在别处,费格斯还对杂志上连载小说的市场空间、文学翻译的勃兴、帕格尼尼与李斯特等艺术名家的明星效应、家里的钢琴对开明女性生活的影响以及保健温泉的流行进行了一番反思。
这样一来,“欧洲人”这个范畴就成了一锅大杂烩,尽管里面大都是名流。你知道屠格涅夫1852年——与哈丽叶特·比切·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同年——出版的《猎人笔记》曾推动了俄国的废奴运动吗?你知道1868年时意大利已经有了775家生意还不错的歌剧院吗?你知道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里的阿玛维瓦伯爵这个角色是专为宝琳之父曼努埃尔·加西亚而设置的吗?还有,宝琳最为著名的歌剧造型是画家德拉克罗瓦设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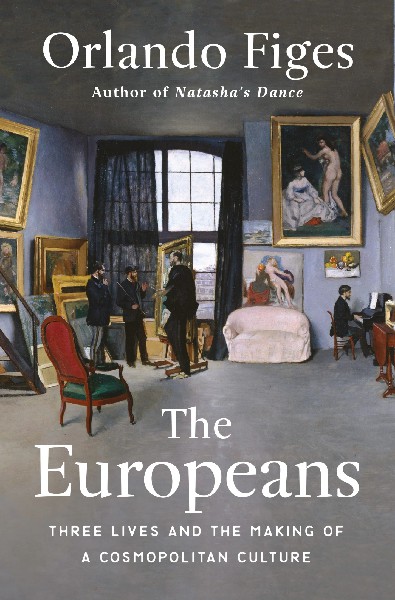
我们的女主角相貌平平,但其个人魅力和引人入胜的声音却让一众男性名流为之倾倒:诗人阿尔弗雷德·德·缪塞曾向她求婚,她与好友乔治·桑德之子有过一段青春恋情,作曲家古诺、梅耶贝尔和柏辽兹都爱上了她。在一次私人演奏会上,宝琳与理查德·瓦格纳一同负责《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里情感最为充沛的第二幕的二重唱。妒火中烧的柏辽兹听着歌不禁勃然大怒。
欧洲文化的一大优点,在于其坚信理性、自由、古典传统和普遍的人类尊严并从中汲取力量——简言之,就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一系列原则。而19世纪的主要特征则是文化交流、“跨越国界的持续对话”以及“不同艺术传统融合为一个更大的欧洲世界”。难怪这一时期也是伦敦世博会(1851年)及巴黎世博会(1867年)的全盛期。费格斯化用肯尼斯·克拉克的话说,“一切伟大的文明进步……都发生于最有国际主义气氛的时期,此时人群、观念及艺术创见均可在国家间自由流通。”
不谈宝琳的话,屠格涅夫就是这一可敬的普世主义的杰出代表。年轻时,他曾和卡尔·马克思一同在柏林学习,并结识了后来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米哈伊尔·巴枯宁。身为一个旅行狂人,他“能够同时以柏林、巴黎、巴登-巴登、伦敦或圣彼得堡为家”,并且他真的做到了。他的书房里有九种语言的书籍。归根结底,虽然屠格涅夫热爱自己的祖国俄罗斯,但他对“国家的召唤无论何时都先于人性的召唤”这类观点是坚决拒斥的。
恰切地说,眼下的费格斯自己就是他所赞颂的文明的代表之一。母亲伊娃·费格斯从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之下逃脱,在英格兰将他抚养长大,但他赖以成名的却是有关俄国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论著。书皮上的小传提到他如今往返于伦敦和意大利的翁布里亚。不过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桥段或许是,在致谢的最后部分,他表示自己在英国公投脱欧后已经恢复为德国国籍。
且不论书中偶尔出现的重复啰嗦以及一些小错误——马克·吐温的《傻子出国记》是关于蒸汽船而非火车旅行的,约翰·戈兹华绥(John Goldsworthy)显然应为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欧洲人》确实是这个冬天值得一读的书。这本书篇幅长、娱乐性强且信息量大。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依照费格斯在全书结尾处的说法,该书旨在“使人回忆起欧洲文明的统一力量,欧洲各国若忽视它必将自食其果”。
(翻译:林达)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