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卢森堡裔美国科学家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发明了“科幻小说”这个词,打这天起,有几个谬误就一直与这种生机勃勃的商业形影不离。头号误解就是“科学教育谬误”,下面举个经典例子: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领军人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小说里写到了科学与粒子物理学,所以如果我去读《基地》三部曲的话,也许就能搞懂中微子为何物。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还曾经在他1960年出版的大热之作《前往地狱的新路》(New Maps of Hell)中指出,退一万步讲,科幻小说的目的就是“为自然法则正名”。通过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增长科学知识,从理论上来说并不是不可能,但为了学习而去研读整套“基地三部曲”实在有点蠢——书中的“心理历史学家”对未来的历史做出惊人预言:帝国即将土崩瓦解,整个银河注定化作一片废墟,黑暗时期将会持续整整三万年!事实上,如果你读了《基地》三部曲,放下书的那一刻,脑子里想的只有“啊!一颗中微子”的话,那你错过的可真是一整部荒诞不经又让人无法自拔的小说。
其次是 “预测谬误”,这一点更加恼人。这个理论相信,喜欢小说能够精准预测未来,通过读书我们就能知道这一代人死后100年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太空旅行的预言可以说是最老生常谈的例证了:“亚瑟·克拉克在1968年写出了《2001:太空漫游》,结果你猜怎么着,过不了几年人类就在月球上踏出一小步了!”还有的人会拿电视机、微波炉、电梯和电话视频这样的科技来说事儿,在这些东西没发明之前就有故事描述了这些科技,于是人们会说:瞧啊,这些奇思妙想统统成为了现实!当然了,不管是科幻小说中描述的是好事还是坏事,总会有情节成为现实,也有许多东西至今也没能实现。尽管小说能构想未来的某些新新事物,但作者可能永远预料不到,这些科技是以怎样的形式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有哪本小说预测过《福克斯和朋友们》(Fox & Friends)或者著名访谈节目《观点》(The View)呢?你举不出这样的例子——啊,话也不能说死了,也许CM·科恩布鲁(C.M. Kornbluth)的《行进的白痴》(The Marching Morons)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呢。
最后,“警世说”也是一种常见的谬误。人们误以为科幻文学给人类敲响了警钟,作为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一分子,我们有着紧迫的共同义务,为彗星撞地球、核战争、气候灾难、极权主义思想控制等等未雨绸缪。为了支撑这一谬误,“人们可能会说,乔治·奥威尔早就警告过我们,未来会出现‘思想警察’了,看看吧,我们现在不就出现南希·佩洛西(美国众议院院长)了吗!”因为雷·布拉德伯雷(Ray Bradbury),我们还得出一条名言:“我不想预测未来,我想防范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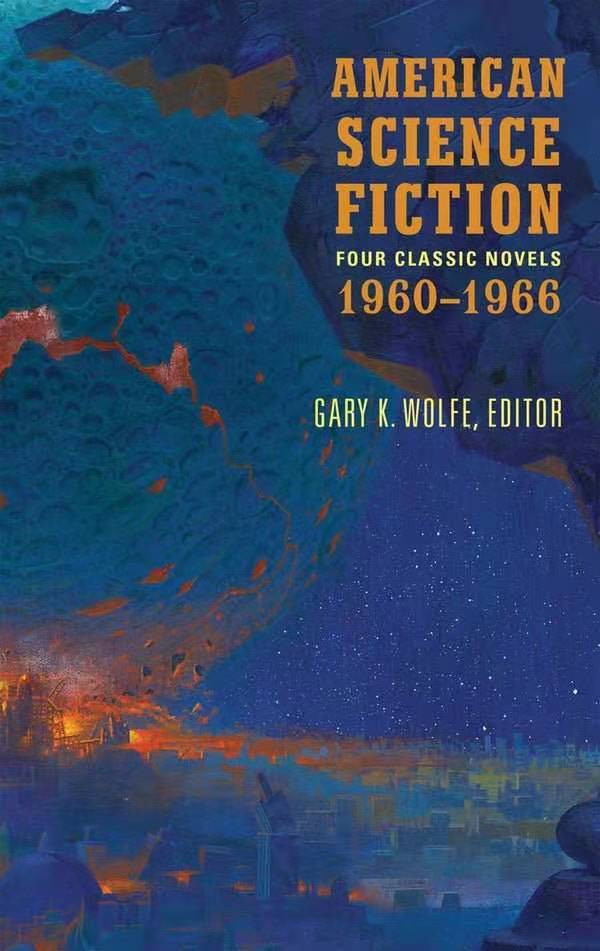
人类期望科幻文学能为自己愈演愈烈破坏世界的行为发出警告,这样的想法是徒劳无益的。难道不是吗?科幻小说早就告诉读者,气候灾难不是妄言,结果并没有带来什么实质性行动;多少虚构作品描绘了黑云压城的极权主义,甚至连核武器荒谬的自杀式恐怖制衡(确保相互毁灭以达到相互制约)都预测到了,我们又做了什么呢?不过是炸弹火药越造越多罢了。
《美国科幻小说》中收录了八部各不相同的1960年代科幻文学经典。这些作品到今天仍令人津津乐道,恰恰就在于它们的预言一个都不准,这些小说并没有准确预知未来,既没有描绘出今日太空旅行的样子、后核战争时代是怎样一片光景、星系间的法西斯主义该如何终结,也没有给出什么正确答案。这些小说没能在歧途的分岔路口竖立警告牌,因为它们认为我们肯定会踏上歧途,我们甚至都无法获知中微子的正确含义。
但在另一个层面上,那个年代的科幻小说确实搭建了一个虚构文学史上最天马行空也最广阔的商业空间,在写作的形式和概念上也是最多样化的。每一本科幻小说的各个方面都是无法预测的,这种模式几乎成为了独树一帜的文学体裁。

就拿塞缪尔·德雷尼(Samuel R. Delany)来说吧,他最具影响力的太空歌剧《新星》(Nova)就提出了人与电子融合的“控制论”(Cybernetic)概念。这本书构建了一个奇异的宇宙:星际飞船漫天飞舞,由脊椎生物机组人员掌舵。社会成员之间的性关系与家庭关系奇妙怪诞,视频艺术机器充满动感。如果说这些都不算什么,那么动词后置的语法结构可称得上是一大创举了——“不太好将会,生疏我是”(正确表达应该是这将会不太好,我生疏了)。在这一妙想产生之时,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灵光乍现打造的尤达(Yoda,星球大战里的要角、善者精神领袖)还要等几年才出生呢。德雷尼行文风格独具,轻快自然,充满了年轻人的野心,他不到二十岁就开始发表作品了,并且老早就得了许多大奖。不仅如此,他的作品总有创新的点子汩汩流出,每一段都对未来提出了全新的畅想。
杰克·万斯(Jack Vance)也不得不提。他笔下的未来同样不可思议,但和爱德华‧艾默‧史密斯(E.E. Doc Smith)或者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Robert Anson Heinlein)所呈现的世界完全不同——并没有刀光剑影的星际军队,也没有科幻黄金时代经典中那样的斗争冲突。万斯构建的是一个全景式的社会经济系统,《埃姆菲瑞尔》(Emphyrio)是他最受好评的作品之一,主角是一位年轻的经济冒险家,到了成人的年纪,他的生活充满起伏——雕刻家之子吉尔·塔沃克(Ghyl Tarvoke)生活在一个由“贵族老爷”和“小姐”统治的星系,这些高端人口享受着奢华的星际交通系统,在一个又一个星球之间穿梭不停,而工匠技师则处处受限,他们的天职就是为统治者制造精美的产品,供他们消费赏玩。在万斯的作品中,鲜有人们用激光武器轰击彼此的情节。他们往往通过买断另一个人的财产和权利,或者是打破生产分配链来实现剥削。从某种程度上看,他和同时代的朋友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在这一点上十分相像。话说回来,和德雷尼一样,万斯也能够在寥寥几句中表现一个浩瀚无边、无法想象的怪诞世界,他的“展蓬郡”(County Pavilion)就是一个例子,在这个地方,出身名门的精英纷纷飞出“巢穴”,和那些身份卑贱的庶民厮混。
“舞者们在地板上来回踱步,散发着一种古怪的优雅,优雅的古怪(graceful-grotesque, grotesque-graceful)。在这个空间里,千奇百怪的人汇聚一堂:小丑、恶魔、英雄比比皆是。从遥远星球和远古时空而来的人奔赴于此。神话、噩梦、童话故事中走出的生物也不计其数。“展蓬郡”富得流油,金属遍地都是,丝绸柔滑,闪着光泽,薄纱之中,光怪陆离。再有就是黑色的皮革、黑色的木材,以及黑色的天鹅绒。”
要是你读过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早期的作品,不可能看不到德雷尼德影子。同理,在吉恩·沃尔夫(Gene Wolfe)的超现实未来幻想中,读者也不难发现万斯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波尔·安德森(Poul Anderson),就算是他最“传统”的星际交响,也从未让读者合拢啧啧称奇的嘴。《满天飞翔的十字军》(The High Crusade)最早在《惊奇故事》(Astounding)杂志出版,这本科幻杂志的主编约翰·坎贝尔(John W. Campbell)既名声在外又十分可气。阿西莫夫、海因莱因的一些作品也都经过他的手面世。罗恩·哈伯德(L. Ron Hubbard)早期被奉为“科学教理论基础”的《戴尼提:现代心灵健康科学》更是有他一份功劳。和许多受到坎贝尔启发的作家一样,安德森也是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他曾写过一本科幻小说,其中的世界深受邪恶的社会主义帝国压迫。在《满天飞翔的十字军》中,一群中世纪英国十字军在外星残暴独裁者的入侵下被迫从法国转移, 然而这些外星入侵者闹出了笑话。骑士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了敌人,骑着马入主被俘的太空飞船,然后摆弄着上面的按钮,最终搞明白了如何穿越太空,并且发射未来武器。下一步——飞向太空!安德森的小说常常被奉为“硬核科幻”,这都仰仗了其中科学描述的准确性。不过换个角度想,身穿铠甲的骑士在飞船上跃跃欲试,这个画面可真是“科学”呢!
想要把以上各种形式、各个主题的星际故事压缩到这个美国图书馆系列中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许多杰出的科幻作品也根本用不着离开地球。美国作家丹尼尔·凯斯的《献给阿尔杰农的花》(Flowers for Algernon)主人公就是一个智力有缺陷的年轻男子,整本小说讲述了他服用一种提高智商药物的故事。克里福德·西马克的经典科幻小说《星际驿站》(Way Station)则作为“乡村科幻”为人所称道,在书中,一个在南北战争中参战的士兵被银河的联邦征召入伍,在威斯康星州的树林里守卫一个秘密的星际中继站。西马克信奉坎贝尔等人的“真实科幻”主义。罗杰·泽拉兹尼(Roger Zelazny)斩获雨果奖的《不朽》(This Immortal,他个人更偏爱当时的标题《叫我康拉德》)又是另一个典型例子。这本小说放眼于一个虚构的后核时代。地球文明岌岌可危,经过一场屠杀之后,地球上同时存在着战前文明以及主角因辐射而发生变异的猛兽怪人的文化——与之相比,真正经受了核战争屠杀之苦的人类到该感到幸运了。
最后,这本书中还谈到了另外两本特别的小说。在乔安娜·拉斯(Joanna Russ)的《天堂的野餐》(Picnic on Paradise)中,一位未来来客在一个年轻的蛮族妇女指引下,进行了一场过去与未来的时间旅行。RA·拉夫尔提(R·A·Lafferty)的《最后一位大师》(The Last Master)则描绘了人类军团和“机器杀手”大军的斗争。在这场较量中,生于十五世纪的哲学家、《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爵士(Saint Thomas More)被唤醒,从历史穿越过来当救兵。其中的逻辑是:当人类需要一个能做“对的事”的人的时候,既然曾经干过好事,不妨再让他放手一搏。这自然是整本书中看似可行度最高的一部分了,要是少了这一桥段,这部小说就充满了拉夫尔提暴躁而幽默的创想。如果说疯狂的爱尔兰小说家弗兰·奥布莱恩(Flann O'Brien,《第三个警察》作者)在小时候就被送到俄克拉荷马州,并且攻读工程学位的话,可能也变成另一个拉夫尔提。
不管是针对这本书的故事研究还是回顾评价,我们都应该提出一个问题——还有什么应该加上去的东西被遗漏了?我认为,唯一的遗憾就是那些黑暗、绝望而令人捧腹的小说。在这本书中的黄金时代科幻小说里,人性总是能在宇宙克服万难,努力奋斗成就明天,而托马斯·M·迪斯科(Thomas M. Disch)和约翰·斯莱德克(John Sladek)就呈现了另外一种态度。在迪斯科的《种族灭绝》(The Genocide)中,崇拜上帝的人类高举旗帜反对外星入侵者,却一下子惨遭屠杀。斯莱德克的《黑金高墙》(Mechasm)中的军工联合体则发明了一种机器,其目的只有一个——吞噬目之所及的所有东西,并且穷尽所有材料,不断进行自我更新迭代。在我看来,这两位作家对我们集体未来的预测算是靠点谱了。
本文作者Scott Bradfield最新作品《眩晕的华丽:流浪狗历险记》(Dazzle Resplendent: Adventures of a Misanthropic Dog)出版于2017年。
(翻译:马昕)
来源:新共和
原标题: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55978/science-fictions-wonderful-mistakes
最新更新时间:12/26 11:05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