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阿多诺在1951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那之后十年,欧洲电影人也开始思考类似的窘境:是否应该,又或者说如何,在电影中表现大屠杀的野蛮。比如1960年吉洛·彭特科沃执导了一部关于大屠杀的电影《零点地带》,贾克·希维特便在法国《电影手册》上对其发表了评论。影评集中谈论了该电影的一个跟踪镜头:法国女演员艾曼纽·丽娃在影片中饰演一名绝望的犹太囚犯,被挂在集中营的电围栏上。电影镜头聚焦在她一动不动的身体,就像耶稣挂在十字架上,这个镜头和女演员的身体都有一种特殊的美感。但这种美激怒了希维特:“在这种时候,导演决定采用跟踪镜头,精心构图拍摄尸体——小心地把举起的手放在最后一个画面的角落里——这个男人理应得到最极端的蔑视。” 希维特认为,大屠杀不应该成为审美愉悦的对象,尤其是性特征化的那种。
自那以后,大多数导演都试图用类似的的跟踪镜头来表现大屠杀。不过,也有人遵循希维特的反唯美主义,完全避开对大屠杀恐怖的视觉表现,比如克洛德·兰兹曼执导的法国大屠杀纪录片《浩劫》——又或者通过眼花缭乱的叙述来模糊处理,比如拉斯洛·奈迈施执导的电影《索尔之子》。许多电影谨慎或间接的描绘大屠杀,并没有把大屠杀放在电影的中心叙述角度,比如帕贝尔·帕夫利柯夫斯基执导的《修女伊达》,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执导的《辛德勒的名单》,艾伦·帕库拉执导的《苏菲的抉择》和罗曼·波兰斯基执导的《钢琴家》。也有一些电影制作人指责像希维特这样的人相当虚伪:《零点地带》的跟踪镜头激发了观众的性欲,它将观众牵涉其中,让观众承认——他们也参与了那种难以言说的、被禁止的颤栗。这些指责可能会让你想到莉莉安娜·卡瓦尼执导的《午夜守门人》和皮尔·保罗·帕索里尼执导的《索多玛120天》。
当然,如此分类并不准确。就像悲剧一样,制作精良的悲剧小说有时会让人流泪,也会让人紧张地大笑——有些电影,比如罗伯托·贝尼尼自编自导自演的《美丽人生》就有意识地利用了这种效果。一件艺术品自我严肃的信念和道德明晰的要求,有时也会使它在无意中成为一个平庸的观众的笑料。奥斯卡·王尔德有句名言是这么说的:“要读到小内尔之死而不发笑,必须有一颗铁石心肠。”王尔德这句话并不是说狄更斯笔下的小内尔不值得同情,而是说,这是一本为资产阶级的读者所写,让他们在光亮的壁炉下阅读的小说,如此而言,这些读者的感悟不过是鳄鱼的眼泪。而我对于马克·赫曼执导的《穿条纹衣的男孩》便有一种相似的感觉。

近来,瓦茨拉夫·马尔豪尔执导的《被涂污的鸟》重新引发了关于创作意图、观众反应和大屠杀背后伦理道德的讨论。这部电影讲述了二战中一个年轻的犹太男孩在一个无名的东欧乡村试图生存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小男孩经历了一系列暴行:被埋在土壤和粪便中,被扔给狗和乌鸦,被男男女女以各种方式剥削。评论家对这部电影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悲剧杰作,有人认为是一部悲喜剧杰作,也有人认为这部电影是对暴力的剖析和美化。在威尼斯、多伦多和伦敦电影节上,一些观众不满电影而选择了离席。这些离席者和电影支持者的对比,让人不禁想起1913年巴黎市民对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的反应。
《被涂污的鸟》想要给人们留下何种印象?人们又该如何看待这部电影?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部王尔德式的电影,一个关于表和里的无休止戏剧。电影《被涂污的鸟》改编自同名小说,该小说自出版以来,已经收到了无数的赞美与贬损。原著作者耶日·科辛斯基是一名从波兰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该书1965年初版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成为了畅销书,并备受埃利·维瑟尔(美国作家、诺贝尔奖得主与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译注)和辛西娅·奥齐克(美国女作家——译注)的称赞。但后来,这本书的名声一落千丈,备受争议。科辛斯基被指控歪曲虚伪地把《被涂污的鸟》陈述为自传,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对于故事是否完全捏造,是根据真实幸存者的叙述拼凑起来的,是修饰过的,还是从罗曼·波兰斯基的口述中摘录的,众说纷纭。一些评论家甚至怀疑科辛斯基1965年时候的英语水平是否足够写出这本书,也有人怀疑这本小说,乃至科辛斯基的其他作品都剽窃自西方不甚了解的波兰国内。
这一情形与马尔豪尔改编的同名电影颇有相似之处。正如阿尔弗雷德·雅里说的那样,它的背景是“虚无之境”,虽然是一个有着典型斯拉夫民俗风情的乡村,让人想起东欧的传说,但却并没有定位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在这个不那么特殊的世界里,许多演员——包括饰演主角的彼得·科特拉尔——都是首次在国际甚至欧洲的电影中亮相。在他们看似有目的的匿名中,我们却不断地看到当代西方电影中非常知名的人物:斯特兰·斯卡斯加德、哈维·凯特尔、乌多·基尔、朱利安·山德斯等。这些明星的登场彻底打破了这部电影对准纪录片真实性的幻想。当他们一出现在银幕上,人们的目光就会聚焦在他们身上,而面对电影中不熟悉的面孔,人们也会期望其他演员看到他们时的惊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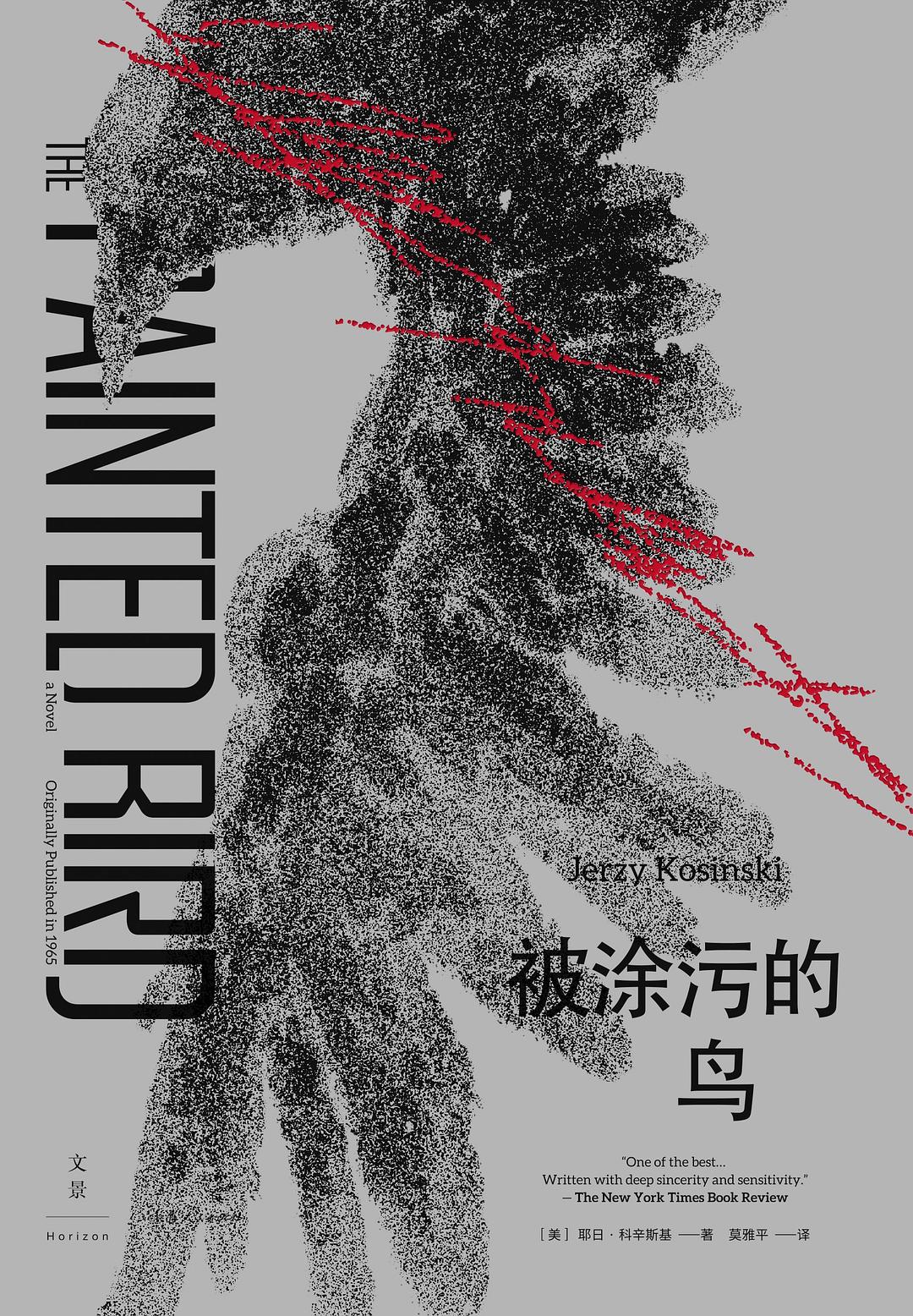
[美]耶日·科辛斯基 著 莫雅平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3
除了这些偶尔打破第四面墙的时刻,这些明星和非明星共同参演的短暂时刻毫无悬念,甚至到了拙劣模仿的地步。《被涂污的鸟》更像是一个快节奏的噩梦,每一个参与者都很难真正难理解它的内涵,与其让我们停留在悲剧的一方面,不如更加深入。这部电影用萨德式的详尽描写使观众对人性失去兴趣。每个敏感的人都是强奸犯;每一个好斗的人都会杀人;每一个表面上善良的人——本来就很少有这样的人——都死得很快。历经重重磨难,年轻主人公的生存带有一种残酷的命运诡计或寓言的意味。他沉默、忧郁,对所看到的一切都不感到惊讶,就像一个精灵,被一种更高的力量派来一次又一次地检验这个世界的恶。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或群体之间都不尽相同,各种遭遇就显得更加零散,与其说是叙事,反而更像是一种象征主义——到了某一点,这个男孩开始因为看到的东西产生了情感波动,这种突然的改变让人猝不及防。
在这种唐突的变化和省略中,《被涂污的鸟》似乎显得相当混乱且优柔寡断。人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种困惑不仅仅是在严肃的戏剧和后现代戏剧仿之间摇摆不定的挣扎,而是来自一个更复杂的源头。这是一部关于大屠杀的电影,也是一部关于东欧的电影——对东欧的描绘相当敏感且专注。这部电影在对大屠杀中犹太受害者的同情和斯拉夫人极端的自我憎恨之间分裂。这种自我憎恨的特殊情感,让《被涂污的鸟》某种意义上有了帕索里尼的意味,但与《萨罗或索多玛一百二十天》不同的是,这些情感来自于受虐,而不是施虐。
《被涂污的鸟》影片中斯拉夫化倾向的线索缓慢但不可逆转地聚集在一起,电影中刻画的形象更多的是斯拉夫农民而不是德国士兵:前者比后者数量更多,更可预见,也更加邪恶。这些斯拉夫人说的是一种东欧世界语,叫做斯拉维亚斯基语或国际斯拉夫语,这是一种有着相当悠久历史的人造语言。对于初次接触此种语言的西方观众而言,很难将其与捷克语、斯洛伐克语或波兰语区分开来。对于像我这样的东欧人来说,勉勉强强可以理解。19世纪80年代,世界语由一个东欧犹太人创造,其有意合成、简化和通用的语法有一种对全球化的乌托邦式回应。相比之下国际斯拉夫语的历史要长得多,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由中世纪的古教会斯拉夫语演变而来。国际斯拉夫语的发展与19世纪的泛斯拉夫运动密切相关,体现了一种希望——以及一种准种族化的信念——即所有拥有共同情感的斯拉夫人民,应该成为一个国家。20世纪初,这种意识形态遭到苏联的强烈反对,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将其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下的反动思想。

这两种斯拉夫国际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在《被涂污的鸟》中以近乎寓言的方式表现了出来。来自东部组织精良的苏联红军,把当地乡村说着国际斯拉夫语的斯拉夫农民从纳粹手中解放了出来。但这些苏联士兵说的不是国际斯拉夫语,而是俄语,尽管国际斯拉夫语应该包括他们的语言,但这些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便显而易见。那些斯拉夫农民散漫、迷信,堕落而原始,而苏联红军则组织严密,精练而强壮。我也许稍微夸大了这种对立——但确实如此。但是对于一个后共产主义的捷克导演来说,在共产主义苏联和泛斯拉夫人之间创造出这样一种准种族的区别,无疑是极具争议性的。
回顾马尔豪尔之前的电影作品,比如《托布鲁克》——一部关于捷克士兵卷入二战利比亚战争的黑暗反战电影,也许能看到更加强烈的罪恶感。《被涂污的鸟》和苏联导演依莱姆·克里莫夫执导的著名电影《过来看看》之间的呼应也加深了这种感觉。马尔豪尔和克里莫夫的两部电影都是从一个身陷战争中的小男孩的视角来讲述,两部电影中小男孩面对战争时的情感和道德上的崩溃,电影所描绘的暴力场景与周遭环境也是惊人相似。但有一个点不同:在《过来看看》中,斯拉夫农民是受害者。而在《被涂污的鸟》中,斯拉夫农民是加害者。
从区域角度来看,《被涂污的鸟》带有一种预兆。泛斯拉夫人对美好地区命运的梦想破灭,变成了不可避免的自然诅咒。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因生活方式和万物有灵的习俗而接近自然,这片土地对他们似乎相对友善,但对陌生人却充满敌意。这里不像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荒凉冷寂,廖无人烟。相反这里是东西欧洲之间的中间地带,地缘辽阔却也足够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天气寒冷却也足够养育这里的居民。这片土地的慷慨让人感到恐惧,让人不禁思考自然是为了什么来哺育居住在这里的生命。收获和生育既充满希望,也令人恐惧:这或许是一种打破暴力的方式,但也是一种让当地人扎根于此的方式。这种压倒一切的诅咒感,让人很难进行所谓的结构性或政治性分析。我们所看到的种族和宗教的冲突似乎出人意料地自然而不可避。
马尔豪尔用明快华丽的黑白镜头,记录下了这部泛斯拉夫噩梦:溺水的人、被挖出的眼睛、麦田里阴郁的乡村妓女和被烧成灰烬的黄鼠狼。马尔豪尔屏息关注每一个关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细节。在电影宣传片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镜头:一个女巫把发烧的主角时候埋进了地里,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来退烧。男孩活了下来,不知是因为埋进土里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但没等女巫回来把他挖出来,他就被乌鸦袭击了,乌鸦把他啄得鲜血淋漓。这并不是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电影《群鸟》中的鸟类的恐怖袭击。那些农民害怕男孩是魔鬼,便把他扔进了河里。在影片的最后几秒钟,小男孩并没有远离这里的乡村,而是逐渐深入。不管人们如何坚持他不属于这里,他也不能离开。
《被涂污的鸟》并没有把大屠杀的作为一种现象来观察,而是把关注放在了大屠杀的背后亘古以来的偏见。这种偏见是人们一直在恐惧知晓,却潜藏在自身最深处的东西。在这部电影中,为数不多的西方著名演员与众多的斯拉夫演员的对比,似乎增加了其整体上自我憎恨的斯拉夫偏见:这部电影在自我审判,但这种斯拉夫式的自虐式反省可能会令人厌倦。在这种反叛中,缺少了个人心理的描绘和发展,显得非斯拉夫人物和背景相当平淡。这些自我谴责的普遍性,也几乎是在重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挑起意识形态斗争的种族成见。
《被涂污的鸟》成功地向斯拉夫和非斯拉夫观众呈现了一种绝望的、没有完全表达出来对于地区罪恶的哀婉。但其自我谴责的特殊性削弱了其批判的锋芒。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将受虐描述为一种欲望,即精心安排一个人表面公开的惩罚。这种乐趣既来自于一种被剥夺权力的经历,也来自于一种事先详细描述这种被剥夺权力的感觉。希维特不满《零点地带》,因为其得到的反馈太含糊,太不和谐。《被涂污的鸟》让人失望,因为电影里的世界,尽管很有戏剧性,但却太过连贯而自足。
(翻译:张海宁)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