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比卡咖啡树是一种热带灌木,生有绿叶和亮红色的果实,四百年前,除阿拉伯世界及埃塞俄比亚局部地区以外,几乎没人知道它,直到19世纪它才广为人知。相传有一名牧羊人发现,自己的牲畜只咬了一小口咖啡树的果子就兴奋不已、彻夜不眠。自从人们发现咖啡对我们也有类似效果以来,这种植物为人类贡献良多,反过来也是如此。全世界的咖啡树种植面积超过了2700万英亩(约合1.64亿亩),照看和培育咖啡树的农家也达到2500万户,而咖啡的价格也不断攀升,一跃成为全球贸易中最具价值的作物之一。这个结果对一棵既不好吃,又不算漂亮,还难以种植的灌木而言已经算不错了。
咖啡在全球的蹿红,得益于一场偶然但却是革命性的意外:这种植物原本用来防范昆虫袭击的化学成分,能够以我们所欲求的方式改变人类的意识,让我们变得精力充沛、效率倍增——即成为更优秀的工人。这种化学成分当然就是咖啡因了,它是全球最受欢迎的精神类药物,80%的人每天都会使用它(而它也是唯一一种我们会每天喂给小孩吃的精神类药物,其形式是苏打水)。与叶片中含有同样成分的茶树一道,咖啡恰好造就了一个它赖以繁盛的世界:这个世界受消费资本主义驱动,由全球贸易辖制,其统治者则是如今没有咖啡连起床都会有困难的人类。
咖啡因的效果与对资本主义的需求以数不清的方式紧密地关联着。在1600年代咖啡和茶来到西方之前,酒精——它比水更卫生——是占主导的药物,能让人陷入迷醉。在工作几乎就相当于户外劳动的时代,酒精不仅可以接受,甚至还受到欢迎(小憩期间来一杯酒是很常见的),但酒精的副作用在涉及机器或数学运算的工作日益占据主导的新时代却成了一个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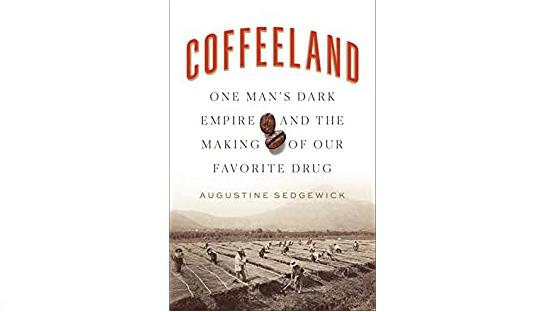
咖啡这一新型饮料不仅比啤酒和葡萄酒更安全(此外,用来冲咖啡的水还必须烧开)而且有助于提升表现和精力。在1660年,也就是咖啡落地英国后不久,有人观察到:
“人们已经发现,咖啡让各个国家都变得更稳定了。以前的学徒和文员等等每天早上都会来一杯酒,导致头脑发沉,不利于开展业务,现在他们有了咖啡这个好伙伴,一种既提神又文明的饮品。”

“既提神又文明的饮品”也让我们可以不受制于身体的昼夜节律,阻止自然袭来的一波波倦意,这样我们就能工作得更久、更晚,人工照明与咖啡一道帮助资本主义征服了黑夜。钟表上的分针与咖啡和茶差不多同时问世,这或许并非巧合,当时的主流是工作的室内化以及分秒必争的作息安排。
咖啡与资本主义的复杂关联,构成了历史学家奥古斯丁·西季威克(Augustine Sedgewick)处子作《咖啡庄园:一个男人的黑暗帝国与最受欢迎药物的产生》一书的基本背景。故事主角是个叫詹姆斯·希尔的英国人,他1871年出生在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贫民窟里,18岁时远渡重洋去中美洲找寻发财机会。在那里,他以曼彻斯特工厂为蓝本,将萨尔瓦多的乡村改造一新,建立了自己的咖啡王朝。希尔后来成了“十四家族”之首,这群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控制着萨尔瓦多的经济与政治命脉,1951年希尔去世时,其旗下的18座种植园拥有5000余名雇员,圣安娜火山山坡上2500英亩的肥沃土地可产出2000多吨用于出口的咖啡豆。多年以来,希尔(不如说是他的工人)的产品就是大家熟悉的小红罐“希尔兄弟牌”咖啡。
“以日常用品将遥远的人群和地点连接起来,这意味着什么?”西季威克开篇发问。《咖啡庄园》对此问题有精彩的思考,使一系列原本晦暗的线索变得条理分明。
要填满希尔兄弟牌咖啡的小罐子,免不得某些形式的残酷性。培植咖啡需要海量的劳力——种植、修剪、拣选和处理——种植园主的成功有赖于在乡村找到足够的具备工作意愿的人。西季威克提醒我们,对未来的资本家而言,核心问题向来并且永远是“什么可以促使人们工作?”

奴隶制为巴西的咖啡农场主提供了一个好答案,但希尔到达萨尔瓦多的时候已是1889年,不可能再采纳奴隶制这个答案了。身为一个聪颖而无情的商人,希尔明白他需要大量的雇佣劳动力,身为一个在曼彻斯特贫民窟长大的孩子,他知道促使人们工作的因素其实无比简单:饥饿。
只有一个麻烦。作为人称“助理(mozos)”的印第安人,萨尔瓦多农民大多数都没有陷于饥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火山旁社群所有的土地中分得一小块耕地,而这里的土地差不多是全国最肥沃的。如果萨尔瓦多能有一种出口作物,情况或许就能改变。这样,在咖啡种植园主的授意以及“发展”的名义之下,政府启动了土地私有化进程,强迫印第安人迁往边远地区或在新成立的咖啡种植园找工作。
实际上一开始还没有这样的两难选择。甚至于刚刚种上了咖啡的土地也仍能提供许多可供自由捡拾的食物。“繁盛的血脉(veins of nourishment)”——其形式为腰果、番石榴、木瓜、无花果、火龙果、鳄梨、芒果、大蕉、西红柿和豆类——“穿梭于单独种植咖啡的区域,哪里有食物,哪里就有不工作的自由,哪怕食物只有一丁点,哪怕这种自由转瞬即逝,”西季威克写道。种植园主解决这个“麻烦”的方式——自然的恩赐带来的麻烦——就是禁止在咖啡区种植别的作物,此举造就了一种极权主义式的单独种植区,排斥一切咖啡之外的东西。假如事有凑巧,鳄梨树确实在不起眼的角落里长了出来,那么被抓到吃鳄梨的农民就会被控盗窃,运气好的话挨一顿打,运气不好就被枪毙了。私有财产的概念就这样被强加到了印第安人头上。
用西季威克的话说,“操控萨尔瓦多民众的意愿,使其聚焦到咖啡生产上来的方式,除了土地私有化之外,就是种植园自身所制造的饥饿。”詹姆斯·希尔推算了一番,发现假如自己把工资划分为金钱和食物两部分——女工每天15分钱,男工加倍,食物则包含两份塞满了豆子、两头均衡的卷饼(当地饮食习惯和地貌一样单调)——那么工人的出勤率和工作效率就会大大提高。 以这种方法,希尔成功地把数千名自给自足的农民和采收者变成了雇佣劳工,从其身上剥削到了任何曼彻斯特工厂老板都会嫉妒不已的剩余价值。
西季威克指出,剩余价值的概念当然来自卡尔·马克思,马恩二人分析了詹姆斯·希尔祖国的工业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是另一样在圣安娜生根发芽的曼彻斯特出口品,在大萧条期间,咖啡价格暴跌,失业的咖啡工人无法再以土地维持生计了。事态表明左派也有“变饥饿为权力”的能力。西季威克的叙事于1930年代前期达到高潮,许多农民在有国外经历的本土共产主义者的组织下起来反抗咖啡业巨头,夺取了种植园并占据了市政厅。

至少到了1932年,革命已在酝酿中,咖啡种植园主控制下的萨尔瓦多政府发起了一场恶毒的反扑。任何长得像印第安人的人都被抓了起来,士兵将他们驱赶到城里的广场,而后以机枪射杀。政府打压咖啡工人的这一行为后来被称为“大屠杀(La Matanza/The Massacre)”,其记忆在萨尔瓦多的乡村有燎原之势。半个世纪后萨尔瓦多第二次陷入动荡时,咖啡大亨又成为了斗争的焦点。詹姆斯·希尔的孙子海梅·希尔被叛乱分子绑架,要求数百万美元的赎金,对希尔家族而言这笔钱倒完全是拿得出来的。
我的转述可能比西季威克自己的故事要更有章法一些。他对咖啡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确实出自马克思,但他的文学天赋和扎实的研究也带来了令人满意的阅读体验,故事里还不时有一些小惊喜。西季威克旁征博引,“偏题”之处不乏亮点,兼及萨尔瓦多和更广阔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作为消费品的咖啡在数量上不断攀升。他特别擅长刻画咖啡是如何被推销给美国人的。回到独立战争时期,美国人为了与爱喝茶的英国人划清界限,多以喝咖啡为爱国之举。他还表明,在美国推销咖啡一般不会说它口味醇美或体验愉悦,而是会宣扬它可以帮人达到某种目的:“一种即时的能量——一种工作用药物。”
20世纪早期的美国科学家对咖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试图理解这种低热量饮品何以能为人类供能,这几乎有打破热力学定律之嫌。咖啡的生产及消费均能产生极大的剩余价值,书中讲述咖啡歇(coffee time)历史的桥段把这点说得十分透彻。
西季威克讲述了丹佛一家做领带的小厂“棚屋编织者”的故事。1940年代早期,公司因战事吃紧,招不到优秀的年轻男性来操作织布机,老板菲尔·葛莱内茨便招募了年龄较大的人来替代,但这些人的手脚不够麻利,无法满足厂方精工细作的要求。后来他又开始招收中年女工,女工虽然在工艺标准上合格了,但其精力又不足以完成全套工作流程。葛莱内茨召集全公司开会讨论此问题时,有职员提出了一项建议:每天休息两次,每次15分钟并提供咖啡。
葛莱内茨将咖啡歇制度化后,工人们很快就有了起色。女工在六个半小时里的工作量追平了老年男工八小时的产量。葛莱内茨进而将咖啡歇改为强制性的,但他又不打算为这半小时休息时间支付薪酬。此举引发了劳工部的起诉,后来到1956年,联邦上诉法院的一项判决将咖啡歇定为了美国人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法院裁定,鉴于咖啡歇能够“提高效率并增大产出”,公司从中获得的收益与工人相仿,故而应算作上班时间。与咖啡歇这一术语的流行几乎同步,由中美洲咖啡种植者成立的贸易组织泛美咖啡局1952年发起的公关行动也促进了咖啡的本土化。其格言是:“奖励自己一个咖啡歇……并收获咖啡所赐予你的。”
在《咖啡庄园》临近结束处,西季威克试图计算一磅咖啡究竟能为一名雇主创造多少价值(或者换个说法,能从一名雇员身上汲取多少价值),所用的案例正是希尔的种植园和上文提到的领带厂。据他的估计,生产一磅咖啡将耗费萨尔瓦多人1.5小时的劳动。这足以生产出40杯咖啡,相当于20名领带厂员工两次咖啡歇的消耗量,按葛莱内茨的计算约等于多出了30个小时的额外劳动时间。换言之,希尔的种植园1954年为一个半小时的劳动付出的6分钱,到了菲尔·葛莱内茨那里可以转化为22.5美元的价值,这一炼金术般的过程既体现了咖啡因的神奇功效,也凸显出剥削的直白事实。
但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咖啡和资本主义的共生关系在眼下来看可能不会有好结果。阿拉比卡咖啡树是一种很挑剔的植物,其生长环境极为苛刻:日光、水、排水系统乃至于海拔都必须刚刚好。世界上适合生产咖啡的地方就只有那么多。气候科学家估计目前种植咖啡的土地里至少有一半——在拉美甚至会更多——到2050年将难以为继,气候变迁成为了咖啡面临的最直接威胁。资本主义可能正在杀死那只为自己下金蛋的鹅。
然而,如果不懂得变通,资本主义就什么也不是。目前提供咖啡歇的雇主或许在不久后就会改用人工合成的咖啡因片剂,一片早晨吃,另一片下午吃。这对于雇主而言有若干优势。药片比咖啡便宜,而且更容易打理。鉴于药片一口就能吞下去,咖啡歇也不再有存在的必要,如此一来公司就有很好的理由把法院在64年前为工人争取来的30分钟宝贵时间又收回去。萨尔瓦多的咖啡工人的命运更不容乐观,但也许“繁盛的血脉”——大自然恩赐的食物——在咖啡的独霸地位崩溃后又将涅槃重生。
作者Michael Pollan系作家,现居湾区,著有有声书《咖啡因》以及纸质书《如何改变你的心智:新致幻剂科学论意识、濒死、成瘾、抑郁与超越》。
(翻译:林达)
来源:大西洋月刊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