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幸福的好日子应当成为我们生活的目标吗?在好日子之上还有一种良好生活吗?良好生活的标准又是什么?哲学家陈嘉映的《走出唯一真理观》日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他近年来的对谈、采访和讲演,书中反复触及的核心问题就是良好生活与好日子的区别以及对话的重要性。结合此前陈嘉映的《何为良好生活》一书,我们得以了解他所说的“良好生活”究竟包括哪些要素,以及为什么对话对于良好生活而言至关重要。

“幸福”距离“良好生活”有多远?
陈嘉映认为良好生活并不是完全的世俗意义上的好日子,比如挣钱养家、送孩子出国留学这些本身并不能构成良好生活,良好生活有德性与灵性的要求。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良好生活与“幸福”生活也是不同的,因为“幸福”是以一个人安享的状态而不是他的作为来决定的,更多地与天真、善良相关,而良好生活更多与品格、灵性和有所作为相关。正因如此,“幸福”是属于老年和童年的,而祝福一位正值壮年的人“幸福”则显得奇怪。“成年人身上,夺目的总是品性与识度,”陈嘉映写道,“少年还未形成稳定的品性,老人身上,品性已经沉潜,我们也不再期待他大展宏图,于是,幸福不幸福就成了首要问题。”他所说的“有所作为”不仅包括建功立业,也包括德修有进,但都与流行的成功学无关。陈嘉映写道,今日所谓的成功人士和不成功人士一样,有的过着良好生活,有的品格低下、灵魂干瘪。
而如今,世俗意义上的“好日子压倒一切”似乎成为了所有人的目标。他认为这与平民化的生活理念成为基本理念有关——现代社会的第一大特点就是平民化——“纪念碑”消失了。

“以前它(纪念碑)是人间最大的事,法老一辈子就是建金字塔……那个时候人对世界的看法是往上看的,下面的都不重要,生生死死,你爱了死了,没人在意这些……我们好像不再通过纪念碑的方式来感受一个人的成就了。”
在古代the few处于中心,而今the many才是关注的重点,人们的生活拉平了,不再向上看,而是向下看。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更接近上帝与神性,艺术借助神性的光辉来改变世界,尘世的变化是次要的;而今人们通过政治、技术和实业让世界变得更好,即便仍然有艺术、哲学和社会思想,却都已经失去了提升生活的作用。
陈嘉映相信,好日子之上的需求是人性的一种需求,就像古希腊人把参与城邦生活视为更高的生活。参与城邦生活的政治生活与当代从政的意义不同,本质上是一种人性的实现;中国古代皇朝时期读书人也要读书做官、过好日子,同时也需要一个治国安邦的舞台,精神上也归属于同一个传承与道统。在今天,好日子缺乏这样的精神寄托,传承与道统分裂,大的精神共同体分裂成无数的小型精神共同体,人们的追求更为多元化。陈嘉映认为,如果失去了这种“人性的实现”,好日子就会成为一种乌托邦,生活变成了平稳的不断重复,历史也将终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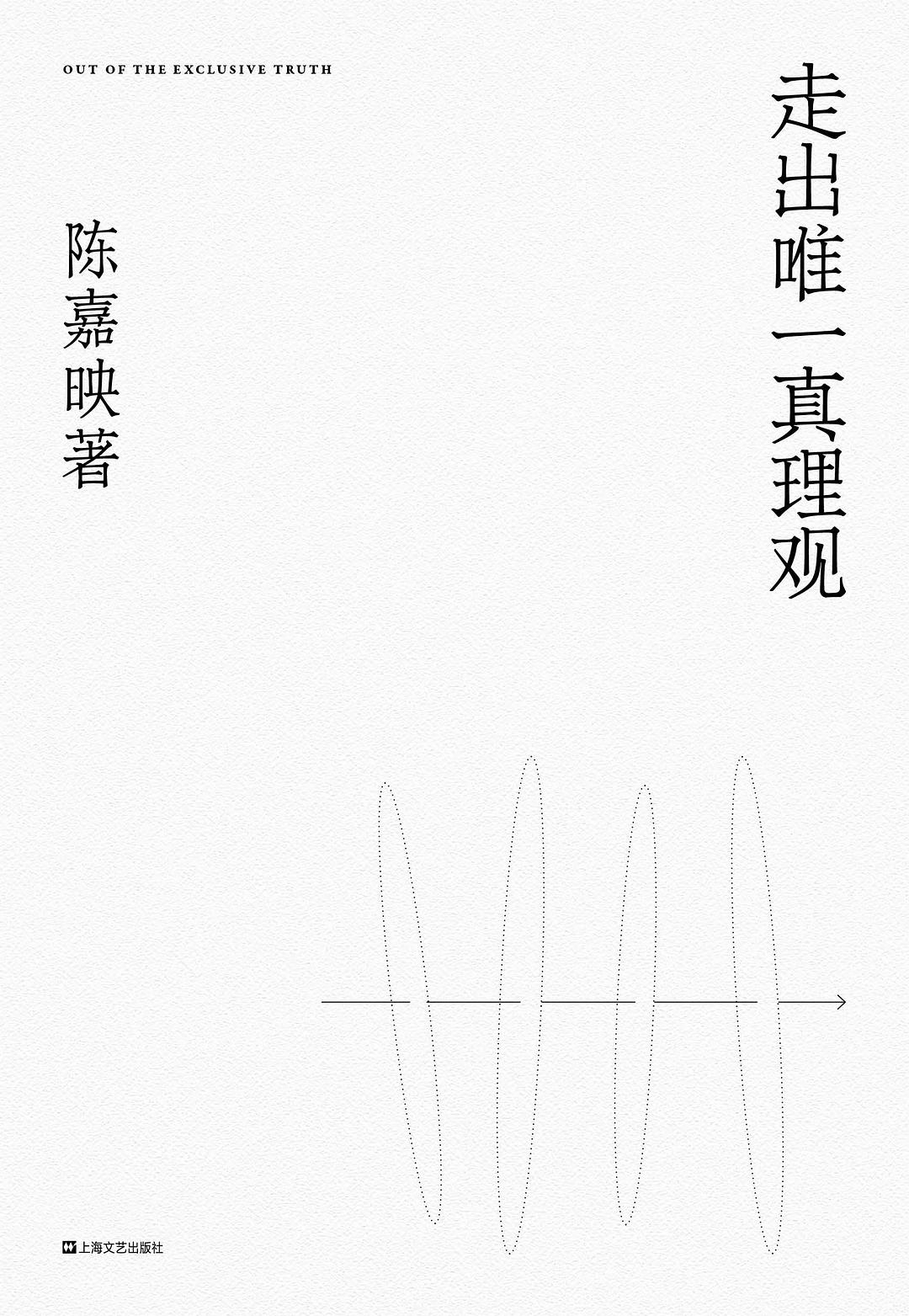
陈嘉映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年5月
精神意义的当代替代物也许是爱情,在今日的话语体系中,爱情占有顶尖的价值,但陈嘉映认为仅仅将男女私情当成绝对的指令,也有虚矫的成分。他在书中指出,“甜甜的恋爱”与真正深挚的爱情应当是有区别的,比如钱谦益和柳如是,他们面对的是朝代更替的大问题,在古典诗词唱和时也融入了国仇家恨,所以他们的爱情才是那样不可重复、深挚感人,而仅是白开水般地“我爱你你爱我”是不具有此般意义的。他还提到,男女私情应当保留在私人领域,公开示爱并不能称为“勇敢”,在公共领域表达自己的公共意见才是“勇敢”的,因为前者不会招致任何危险,而后者顶着具体的风险——“勇敢”应当是属于公共生活的德行。
那么陈嘉映所谓的“良好生活”,是否随时随地可以追求和拥有呢?他认为我们最不应该忽视的一点就是,良好生活的提法并不适应极端的情况,在极端的处境中——比如奥斯维辛集中营——人的品性依然分为三六九等,但那里丧失了良好生活的任何可能,那些大德大勇之人的品格远远超出了一般良好生活的范围。而对生活于平顺时期的人们来说,想象极端环境也许太远,眼前能做的就是多少做点事情,“改善我们的环境,防止暴君和暴虐局面的出现。”
如无法达成共识,是否还需要对话?
在与新书同题的讲演篇目《走出唯一真理观》中,陈嘉映回顾了自己从年少求学到留校任教、致力学术的整个过程,尤其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哲学与关于社会问题的思考与科学的思考之间有哪些不同之处。科学的思考有一套标准答案,而社会问题的思考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陷入了“什么都可以”的相对主义。他写道,事实上我们从来不是生活在一个纯粹事实的世界之中,讨论美丑善恶不可能脱离我们的感知和感受,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讨论就只是主观表达各自的看法。他并不赞同科学之外没有道理、知识、学问,只有零七八碎的主观体验这一观点,要不就是普适理论,要不就是灵星感想的二分法,两者之间有着广阔的领域。对话式的探究的目的不是科学真理,而是对话式的、翻译式的理解。
在对话和争论中,人们总在调整自己的视角,了解自己相信的到底是什么,并实在地为自己所信之事有所作为。通过对话和讨论,人们得以将真理性说明白,这就是他所说的“放弃唯一性,坚持真理性”。
“在具体的思考和行动中跟其他的生活理想对话、互动。是的,他有虚假的虚幻的东西,因此你要与他争一争,但这个过程是双方的,你也有你的虚假和虚幻,你也要在这种争执中变得越来越实在。”
关于对话在当代学术界的现状,陈嘉映提出,现在大多数学术会议都向我们证明了学术生活已降到了怎样的低点——三百人参加的大型会议蔚为壮观,但十几分钟的大会发言和三分钟的举手发言不过是走走形式,高度专业化的讨论也许还可以实现,而思想讨论是不可能的,因为思想讨论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聚焦问题。讨论思想问题,三五人最好,大家都关心同一个问题,也知道问题的焦点何在。他将共同的问题理解为一个连环套,几个圆圈各有圆心,但互相关联,而有效的对话就是连环套式的对话。
所谓的对话要想成立,需要注意许多事项,比如对话中专家不要动不动就拿出专家的身份,不同的学科背景不应当成为对话的阻碍,更不能依赖各自的理论——毕竟专业背景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共通问题,而不是用专业门槛来限制共同问题,对话时可把专业训练的能力带进来,而不是把专业内容都带进来,即使读的书不同,所熟悉的理论不同,关心的问题却是共同的,而寻找共同的问题是重要的。“现在的体制要求哲学工作者成为专家,你是王阳明专家,他是维特根斯坦专家,你我之间没有共同问题,”陈嘉映写道。现代学术体制会给人以一种确定性,然而这种确定性可能会遮蔽掉最重要的东西,他认为这与西方分析哲学传统有很大的关系,因其只接受“institutionalized questions”(体系化的问题)。
至于对话和说理的目的,在陈嘉映看来,论证的结果应当更富柔性的教化作用——他认为高高兴兴地得到教化、学到与生活相关的东西是文科生得到的好处,与此相关,“心性”在学习哲学方面也是重要的,因为哲学并不是智力游戏,而应当直通内心的感受——而不是争论对错,“一般人在谈论证的时候把论证的目的想得太窄了太急了太刚性了……整体观念的教化往往比一事上谁对谁错更重要。”也不在于达成一致,有时也无法达成共识,但即使不能达成共识,也可增进互相之间的理解。在说理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到,以理服人与以权力压服是不同的:“弱者无权无势,往往只剩说理可以救援。”因此应当培养说理的文化,要求强权讲点道理,也让有理的一方学会说清道理,而平等理性公开地展开讨论,就有了自由民主的最低共识。

陈嘉映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年4月
值得指出的是,书中周濂对陈嘉映的采访《行之于途而应于心》也补充了陈在《何为良好生活》中没有着重书写的良好生活与制度的关系。陈嘉映回答说,良好生活须在制度之前,而不是相反;以良好生活来判断制度的好坏,如果好生活只是GDP,那么制度也是如此,如果好生活还包括德性,那么事情就比如此复杂得多。他援引亚里士多德“青年人若不是在正当的制度下面成长就很难培养成具有德性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揭示了伦理生活与制度建设之间的关系。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