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科学家开始研究苏必利尔湖皇家岛上的狼群。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狼群中发展出了广泛的脊柱畸形以及眼部病变,并且情况迅速恶化这可能是杂交与岛屿封闭所致。然而在1997年,一名新成员——一只公狼——造访了这座岛屿。它的到来预示着当地种群的重大转变,随着这次基因革新的爆发,狼群重新焕发了活力。生命的延续仰赖于迁徙。
科学记者索尼娅·萨哈在她的新著《下一次大迁徙:流动生命之美与恐怖》(The Next Great Migration: The Beauty and Terror of Life on the Move)中披露了许多这类故事。在这场对我们迁移倾向的随兴探索中,她的报道从喜马拉雅山脉村庄延伸到希腊岛屿,再到南加州的荒凉山丘,萨哈认为,迁徙是一种深深植根在人类与动物世界中的特性,比我们所料想的更加基本和普遍,且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
在我们这个生态和政治动荡的时代,大规模迁徙常常被视作严重的危机。人口迁徙的数字确实惊人——共有6000万人为躲避战争、迫害或气候变化的影响而迁徙,而这个数字在2050年或许会上升到1亿——我们也熟悉一些政客,他们把移民描绘成“犯罪祸根”,面目模糊的人群蜂拥进入西海岸——或者,正如罗伯特·D·卡普兰在他1994年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文章中所说的,是“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是非常不稳定的社会流动中的松散分子”。
但是,萨哈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重要的人道主义观点,与将移民视为社会灾难的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她将人类迁移的历史与自然界的寓言交织在一起,将移民重新定义为一种生物和文化规范,而不是静态世界中的一个例外——一种应该被接受而不是被畏惧的规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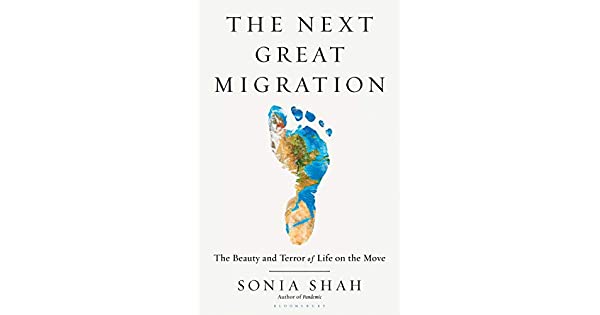
“几个世纪以来,”萨哈写道,“我们压抑了移民本能的事实,将其妖魔化为恐怖的先兆。我们构建了一个关于我们过去、身体和自然世界的故事,在这个世界里,迁徙是异常的。这是一种幻觉。当它被打破时,整个世界都会改变。”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深入探讨了这个僵化世界神话的起源,以及它对公共话语和政策的影响。莎首先调查了18世纪分类学家卡尔·林奈的工作,林奈的生物分类系统将每个物种与特定的地方联系在一起。林奈受基督教信仰的指引,认为事物的等级和自然秩序是固定的,这一思路最终战胜了他的竞争对手:法国博物学家乔治-路易·勒克莱尔·德·布丰(George-Louis Leclerc de Buffon),后者有远见地提出“想象一段迁徙的历史”——“质疑自然的持久性,挑战造物主的完美性”。
《下一次大迁徙》追溯了早期对物种间地理差异的强调如何促进了“种族科学”和19、20世纪优生学运动的兴起。随着来自欧洲、亚洲、加勒比和中美洲的数百万移民抵达纽约港口,像麦迪逊·格兰特这样忧心忡忡的精英,煽动起了对移民身体“杂交”和“种质”的恐慌,认为这可能会污染民族血统。萨哈描述了种族理论家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寻找科学依据的疯狂追求,这是阻止移民的灵丹妙药。这样的研究大多以失败告终,从未具体化或有效地坐实种族主义假设;然而,把移民塑造成有毒和低等生物的形象,却有流行文化和政治文化渗入其中。格兰特1916年的著作《伟大民族的逝去》宣扬了由移民带来的颠覆种族等级制度的风险,这帮助促成了1924年的一项法律,该法从根本上限制非白人移民美国。该书也是阿道夫·希特勒的范本,希特勒称它为自己的“圣经”。

这些意识形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断回荡,萨哈循着这些意识形态,证明了仇外心理、人口控制、环境保护和白人至上主义是如何相互交织,并推动了限制人口流动的系统化行动的。它们也建立了“林奈式的自然观,即生物上不同的民族也在地理上不同的地方生活”,正如她指出的,这一立场直接导致了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她援引总统的一位国家安全官员的话说:“多元化不是我们的优势,而是软弱、紧张和分裂的根源。”
萨哈将这种对移民的诋毁,与阐明我们人类深刻的流浪本能的科学进行了对比。从20世纪80年代揭示人类在非洲的共同祖先和随后大规模迁徙的研究,到最近表明更早的古代人类迁徙浪潮和其他令人惊讶旅程的突破,她探讨了“定居的过往和种族秩序的神话”是如何开始瓦解的。例如,“埋葬在瑞典南部的一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农民遗骸,被证明与如今生活在塞浦路斯和撒丁岛的人有基因关联。”现代的美洲原住民与西伯利亚东北部的楚科奇人有共同的基因,这表明他们的祖先先从亚洲迁徙到美洲,然后再次返回,”萨哈论证道,“我们并非从遥远的古代到靠近现代的漫长时期内一直保持静止。我们一直都是移民。”
她坚持认为,我们也低估了野生物种迁徙的能力,她用下述故事来证明她的观点:猎豹会横穿多个国家,佛罗里达海牛饮用鳕鱼角码头的水,在相距约1.1万英里的海洋中分布的树木,它们的生物相似性却可以相类比。这样的类比很有趣,但并不总是合理。为了证明她的论点,她把许多因不同原因迁徙的物种行为——从每年周期性的迁徙到因人为因素导致的栖息地破坏——都放在迁移的大旗之下。她强烈地驳斥“入侵”或“非本土”物种的概念,认为它们是自然界中反迁徙言论的类比,而没有认真对待引入的动植物对生态系统造成的严重破坏。她聚焦于赞颂迁徙,却没有考虑迁移的人类对地球造成的生态危害,而这种危害正日益加剧。
在全球静止的时期阅读全球迁移史显然是一种讽刺,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已经被限制在所处环境中几个月之久。萨哈认为,我们的仇外倾向可能是对外界携带新病原体的恐惧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免疫反应,在疫情加剧人们分歧的情况下,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理论。然而,她写道:“在一个充满变化、资源分布不均、活力十足的星球上,如果我们将迁徙接受为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就可以有更多方式继续前行。”她简要谈及了一些方案,如可渗透边界、合法移民途径,以及将破碎的生物群落缝合在一起的野生动物走廊。当我们开始从这场强制的暂停中复苏,或许准备好了新的迁移时,莎的著作便是一份挑衅的邀请,它邀请我们将未来无可避免的迁移视为一次机会,而不是一场威胁。
(翻译:马元西)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