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几乎所有与地缘有关的概念都需借助坐标才能确认,南方也不例外。历史上,荆楚是相对“中原”的南方,江南是相对长江以北的南方,华南则是行政上的一个明确的地理分区。文学史上的“南方”也指向模糊,无论是江南还是潮汕,似乎都可以被纳入“南方”主题的书写。
浙江作家张忌的《南货店》与广东作家林培源的《小镇生活指南》两部小说的文学空间都属于南方。前者写江南城镇的生活图景,借由一家典型南货店的故事记录二十多年的变迁;后者以潮汕为原型,作者虚构了一个神秘莫测的清平镇,记录小镇居民的失意、破碎和绝望。支撑文学空间的要素是什么?对比这两座南方城镇,我们可以发现,风景、物产、习俗、方言与居民都能让一座城镇野蛮生长,但人与地方之间建立起的情感联结,才让每一座城镇独一无二。美国人文地理学学者段义孚把这种情感纽带称为“恋地情结(topophilia)”,认为人在对环境投注情感时也能认识自身。
对于这两位作家来说,无论是否生活在故乡,只要开始写作记忆中的南方,就是在重新发现家乡与自我。在上海书展期间,张忌、林培源一起从南货店和潮汕小镇出发,围绕着南方所联结的情感与回忆进行了对谈。

风物和方言
浙江大学教授、诗人江弱水曾提出“肌理(texture)”的赏读方法,指的是“要肉感地去感知一首诗的文本的肉身”。他分析莎翁早期传奇剧似丝绸柔滑,晚期悲剧则像土布坚韧。将这个概念借用至小说领域,我们会发现小说中也有许多彼此呼应的元素,它们构成了独特的文本风景,共同呈现微妙质感。如果将南方看作张忌和林培源作品的骨架,那么他们笔下相异的风物和语言,就是骨架上生出的不同肌理。

南货店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南方小镇常见的生活场景,它售卖日常杂货和南方风物。《南货店》提到的食物也充满了江南风味:扣肉、鲍鳗、年糕、汤圆、酒酿、白蟹、碱水面……“这些蓬松末节的东西很难总结,说得俗一点,更多时候是有一种乡愁在维系,但具体的东西很难描述,”张忌说。
《南货店》的故事背景设置于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是一个从物质由匮乏走向富足的过程。有观点认为,张忌不厌其烦地对食物进行描写,是想通过列举旧时物件展开怀旧。其新书责编任柳却认为,张忌更想表现的是个人在时代中的命运,比如南货店的二把手齐师傅每次受批斗后都会去吃一碗阳春面,这个仪式般的过程让他感到难得的慰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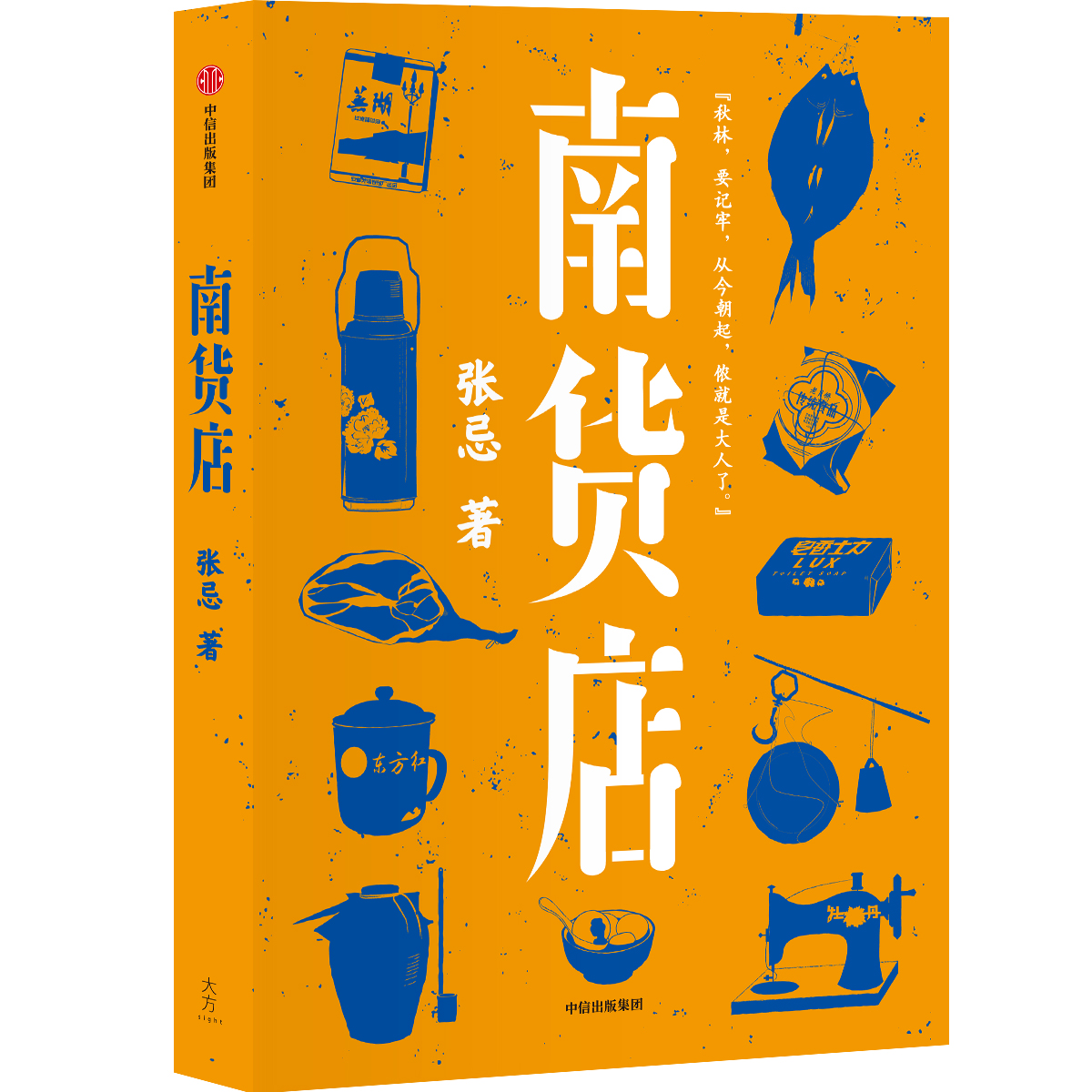
张忌 著
大方·中信出版集团 2020-07
生活在潮汕小镇、直到18岁上大学才离开家乡的林培源,在列举牛肉火锅、鹅肉饭、卤鹅、砂锅粥等潮汕食物时如数家珍。他觉得食物应该与故事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在《小镇生活指南》中,他尝试将食物作为调配故事情节的要素。在《最后一次“普度”》一篇中,他花大量笔墨刻画了当地农历七月半的民俗卤鹅,意在用卤鹅的过程烘衬和描画关键人物卤鹅工。《青梅》中的青梅酒见证了十年的时间跨度,林培源写道:“人世变换,风雨流转,酒还在。”
在语言维度上,方言词汇让这两本小说变得鲜活立体。相比北方官话,南方方言既多样又难以辨清。汉语言研究学者郑子宁曾分析认为,南方地区多山,战乱不多,语言会持续性分化;南方以外的地区汇聚大量移民,需要用通行官话交流。所以,如何将方言融入小说,在不造成阅读障碍的同时体现出地域色彩,是创作者要面对的难题。
张忌认为,作者的语言和审美会直接塑造南方面貌,他意识到这一点后开始在语言上颇下功夫。他从小受古典文学影响,想用类似的语言风格写作,但一直没找到落脚点,最后他选择从家乡方言入手:“我庆幸我生长在江浙地区,因为我们的方言在延伸到书面时相对容易,能与传统的语言习惯形成有机对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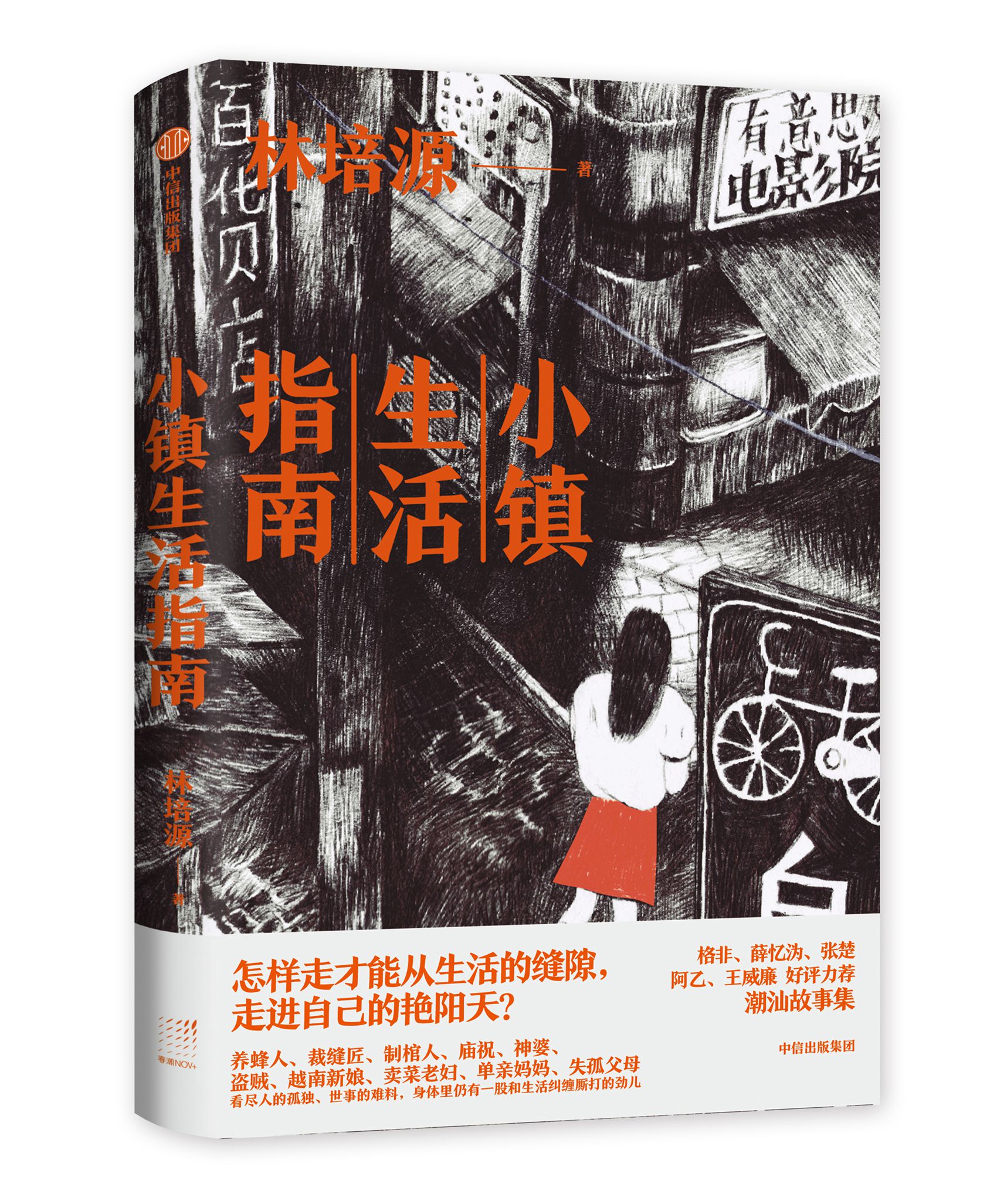
林培源 著
中信·春潮 2020-07
相较于张忌的江南方言,林培源面对的挑战难度更大。潮汕方言异于标准汉语,“言文不一致”,无法在汉语中找到方言俚语中的对应汉字。林培源最终找到折中的方法,“在涉及叙事的部分,我使用通行汉语;涉及对话,就模仿人物的语气强调,适当用方言词;叙事过程中的动词,则尽量用方言词。”这样,读者在阅读中遇见陌生化的字词时,就会产生奇妙的阅读体验。不过他也谈到,马华作家们在方言使用上更加肆意,作品也表现出更生猛的南洋野性。他也表示,自己想在下一部作品中更大范围地使用方言来进入人物、社会与历史。
节奏与人物
除了共同关注风物与方言对文本风景的塑造,张忌和林培源在小说节奏上也都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张忌觉得小自己九岁的林培源与他拥有相似的小说观,都意识到了把控节奏的重要性。林培源回应称,小说家需要用隐忍克制的态度创作,在情感迸发的时刻保持一种引而不发的状态。他举了《南货店》中几处关于死亡的情节为例:齐师傅与大儿子齐海生之间的关系非常糟糕,当齐海生被判死刑时,张忌并没有进行正面描写,却在齐师傅如何收尸上着墨颇多;杜家大女儿杜梅在生活和生意中多次失意,最终选择自杀,张忌只用一两句话陈述结果,却对杜梅临死前的行程详细描写。林培源认为,这样的写法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合适的留白带来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失落感。
此外任柳认为,两位作家都注重对“人”的书写,对人物的细致描摹使得故事在残酷中呈现出温情。《南货店》是一幅时代众生相。主人公秋林从南货店店员成为百货店公司老板,原先惴惴不安的性格也发生了微妙变化。张忌把问题抛给读者:时代冲击如此之大,一个想保持不变的人真的能始终不变吗?在这本书末尾的创作对谈中,作家弋舟认为张忌的风格是“在无差别的世相中体恤众生”,他关注的是“一个个具体生命本身,这生命所处的时代或许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南货店》刻意模糊了具体时间,但三部曲式的架构分别对应了70年代末、80年代与90年代初,暗含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变动。林培源用“不倒翁”形容其结构:“张忌对于人的理解支撑了这个匀称形式,小说就有了一以贯之的审美标准。”
《小镇生活指南》中的十个短篇故事也聚焦边缘和底层人物,写庙祝、神婆、养蜂人、失孤父母、离异女性、游戏厅老板娘等等。林培源说自己故意将人物与故事齐头并置,在一些主题中点明灵感,比如《他杀死了鲤鱼》的题目就代表着故事梗概。任柳认为,对比张忌的人生百相,林培源的书写更有力量感,主人公在开篇就被放置在较差的环境里,随着故事走向继续被向下拉扯,像是从悲剧走向更深的悲剧。《秋声赋》中的父亲固执地认为“读书无用”,断绝孩子“走出去”的愿望,令昔日的小神童彻底发疯。林培源对读者解释道:“写小说一定要进入到人物的精神状态中,触摸他的灵魂深处,这样的作品才立得住,能给读者一点灵魂的刺痛。”

民间神秘习俗也是《小镇生活指南》的一大特色,例如《濒死之夜》写一位年轻人与算命神婆,《他杀死了鲤鱼》写守庙老人如何面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最后一次“普度”》里的母亲因过度思念走失的孩子而精神失常,小说用模棱两可的手法处理结局:镇上人的传言母亲和“孩子”笃定地在大街行走,谁也说不清这是不是“大白天见鬼”。
远走与驻留
文艺作品中的南方并非具体的地理概念,而显现出些许暧昧和空洞,但故乡的经验与写作的尝试却为这一并不实际的指称注入了血肉。
张忌一直生活在浙江的小县城宁海,只在大学读书时短暂离开。随着年纪渐长,他感到自己与宁海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投身以江南县城为背景的写作更加剧了这种情感。他坦言:“南方对我来说,是写作一切可能性的源泉。”
张忌久居南方县城的经历也让他有充足时间接触民间的叙事传统,寻找到真正想书写的东西。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张忌认为与五年前的小说《出家》相比,《南货店》的写作令自己变得更加坚定。
林培源提到,“故乡或者说‘南方’这个概念,对我来说,意味着部分可能性的源泉。”在《小镇生活指南》的后记中,他称自己是从潮汕走出来的小镇青年,与其他人大同小异,多年来辗转求学的生活更让他在地理空间上离潮汕越来越远。但写作却让他觉得“在小说中,在情感认知里,我和故乡反而越来越近”。
在前一部短篇小说集《神童与录音机》里,林培源进行了许多先锋文学的尝试。他更注重叙事的形式、结构,在故事中巧设机关,用大量变形、夸张和寓言的技巧掩藏文本的机密。相较之下,《小镇生活指南》有着更强烈的社会关怀和现实主义色彩,侧重完善人物、环境、故事等传统现实主义要素。两部作品集风格不一,但林培源称它们都是“同一个泉眼里冒出来的泉水,这个泉眼就是潮汕世界”,是个人历程的改变使得根植在潮汕乡土上的文本生长出了异质性的经验。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