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后真相”一词来自美国剧作家史蒂夫·特西奇,2014年开始被西方政论界广泛应用。在今天的媒体环境里,人们对于真实性的追求,转换为对于情感接受性的追求,价值中立、客观的论辩立场,退化为相互攻讦的政治。特朗普利用自媒体登上政治舞台,同时也遭逢以媒体为武器的党派斗争;甚至国际政治,也充斥着近乎“信息战”的真假消息。因此,看似各自独立的三个问题,在当代西方政治的框架下,是彼此连带、彼此作用的力量。
《后真相、党派斗争与信息战》
文 | 胡海娜(《读书》2020年10期新刊)
“欢迎来到虚幻世界”(Welcome to Shadowland),美国《大西洋月刊》新设的网页专题如是说。该专题辑录了数篇调查和评论文章,从解构阴谋论的角度,对美国当代政治和社会生态做了详细描述。这些阴谋论中最显著者,当属于二〇一七年在美国兴起的QAnon(“匿名者Q”)运动,它由一个匿名人士Q发起,在特朗普支持者之间广泛传播。这些人认为一群崇拜撒旦的恋童癖者统治着世界,他们通过民主党的组织秘密地在美国渗透,特朗普因为揭露了他们的阴谋,而成为自由派精英和媒体攻击的对象。特朗普应对疫情不利,引发美国媒体的广泛指责,这非但没有动摇这些人对特朗普的支持,反而更加确信了民主党正在策划一起推翻特朗普的“政变”。而特朗普更是借助这种情绪,散播诸如高温和潮湿能够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羟氯喹药物能预防新冠病毒、病毒来自生物实验室等观点,回避自己的抗疫失职,对这些言论予以质疑的媒体机构,都成为特朗普口中的“假新闻”。

透过这些现象,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阴谋论就像是黑压压的乌云,紧密排布在美国上空,这是后真相时代的隐喻。这是一个迎合比尊重更重要、感觉比真相更真实、利益比道德更高尚、攻讦比论辩更受欢迎的时代。它表现为理性时代的终结,西方启蒙主义价值观的破产。跟这种幻灭相关,人们对于真实性的追求,转换为对于情感接受性的追求,价值中立、客观的论辩立场,退化为相互攻讦的政治。在各种利益和情感诱导下,坚持独立报道真相,捍卫职业精神的美国媒体,跟两极分化的政治信仰不谋而合,彻底扭曲了美国政治的公共空间。
01 后真相与媒体的党派化
国人对于美国向来存有“新闻自由”的印象,人们相信美国捍卫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鼓励观点讨论和思想交锋。但与此不同的观点认为,新闻报道从来都是党派政治的产物,从来没有奉行专业和独立精神的报刊,所有传媒都是政党宣言和立场的传声筒。《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福克斯新闻节目主持人马克·莱文(Mark R. Levin)二〇一九年出版的《新闻不自由》(Unfreedom of the Press)一书,对美国新闻的党派性进行了深刻描述。他指出,美国建国早期的出版商都是真正勇敢的人,他们冒着一切危险,推进和捍卫一个独立国家和公民社会。但在建国后不久,美国新闻就被政党化,大多数报纸与政治家、竞选者或政党公开结盟。莱文认为,当代的媒体环境与十九世纪似乎并无差别,党报又回来了,而且发展得欣欣向荣。在早期政党报刊时代,报刊还能在不同党派间均匀分布,但现在的新闻媒体几乎压倒性地支持民主党,敌视共和党,尤其是保守派。大部分媒体的记者与民主党政府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媒体从业者跟奥巴马时代的民主党政府形成一个“旋转门”,至少有二十四名记者从媒体工作过渡到在奥巴马政府工作。这些人大多对美国的建国原则、传统和制度充满敌意,他们就像是社会的滤镜,企图强制读者以进步的意识形态为中心,作为社会思想和政治活动的统一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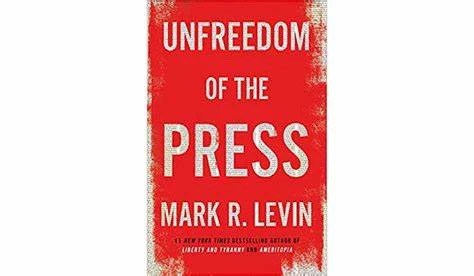
这一切都充满了神秘和不透明的色彩。如果有谁胆敢质疑或批评这些报道的动机,这些记者就会群起而攻之,义愤填膺地将质疑者或批评者描述为对新闻自由抱有敌意的人。他们对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及其支持者,以及他们出台的政策充满了强烈的敌意,并通过各种不实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将特朗普扭曲为一个法西斯独裁者、新纳粹分子、白人至上主义者、种族主义者。而特朗普也不甘示弱,利用脸书等新兴媒体平台,攻击主流媒体的政治偏见。二〇一六年的政治竞选宣传,成为特朗普利用社交媒体,精准定位并引导选民意识的巅峰之作。根据二〇二〇年三月《大西洋月刊》文章《为了赢得总统选举,发起数十亿美元的虚假信息运动》(The Billion-Dollar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to Reelect the President)报道,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利用大数据,为美国的每一位选民建立了详细的“心理档案”,并尝试利用某些性格特征来激发选民的偏执症和妄想症。从当年六月到十一月,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利用这些数据,在脸书精准投放了五百九十万个广告,而希拉里团队所投放的只有六万六千个。成千上万具有目标性的微广告涌入互联网,把特朗普描绘成一位打击外国腐败的英勇改革者,而民主党人则被描绘成为正在策划政变的小人。

在当选总统之后,特朗普与福克斯新闻网结盟,打造能替自己说话的传媒“喉舌”。《纽约客》专栏作者简·迈耶(Jane Mayer)撰写的长篇深度调查报告《福克斯新闻白宫的诞生》(The Making of the Fox News White House),披露了美国收视率最高的有线电视台福克斯新闻与特朗普白宫的利益关系。该文章指出,在上任美国总统之前,特朗普跟福克斯新闻网的背后大佬默多克结成了共赢关系,特朗普以其放荡不羁的形象,出现在默多克掌控的《纽约邮报》上,从而提高知名度,而默多克则通过报道特朗普的爆炸性新闻来出售报纸。在成为美国总统后,特朗普通过系列人事任命,巩固了这一利益联盟。二〇一八年七月福克斯前联席主席比尔·希恩被任命为白宫公关总监兼人事副总监,而希恩的前任、白宫前公关总监霍普·希克斯(Hope Hicks)则被任命为福克斯公关部门的最高领导。不仅如此,特朗普还任命了前福克斯成员本·卡森(Ben Carson)为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前福克斯评论员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和K.T.麦克法兰(K. T. McFarland)分任正副国家安全顾问。
这一结盟形成了白宫和福克斯的反馈循环机制,双方在不断地重复互动,兜售着各种阴谋论思想,并将谎言包装成真相,传递给它们的受众群体。在美国国内两党政治极化的挤压下,媒体不再是真相的拥护者,观点变成了相互攻讦的武器,电视新闻采取夸张的方式来报道政治新闻,并采用情绪化的方式,宣传自己支持的领袖,贬低其竞争对手。在资本和政客们的操盘下,进步变成激进,保守变成疯狂,不断侵蚀着真相的生存空间。集体情绪带来的利润非常可观,而当读者们食不果腹地蜗居在恶臭的汽车旅馆中,为这些情绪化的假新闻激动或愤怒时,这些媒体大亨正坐在他们的私人飞机上,喝着红酒,抽着雪茄,俯瞰着这些因他而躁动的人。
02 当情感战胜了理性
在《紧张状态:民主和理性的衰退》(Nervous States: Democracy and the Decline of Reason)一书中,英国政治经济学者戴维指出理性优于感觉的时代,开启了科学的革命,但现在这一时代已经终结了。通过对建立在理性和事实基础上的真相观的思想史追溯,戴维意图为这种政治混乱提供解释。他指出,西方之所以能够能形成对于真相的共识观念,完全是宗教冲突的结果。由于无法就宗教真理达成共识,欧洲社会产生持续的暴力冲突,这驱使人们探索理性主义的思想和政治方案,它认为人们可以发现真实,并基于事实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提出解决问题之道,从而将欧洲从宗教冲突的苦难深渊中拯救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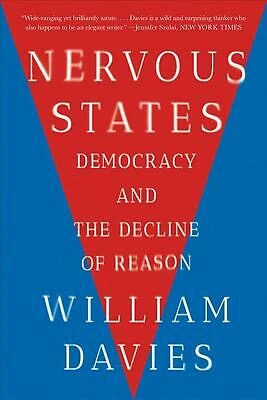
戴维指出,维持这种机制的关键有两个环节,其一是社会精英能够基于事实分析问题,其二是公众和精英之间存在基本信任。这些精英分布在政府、学术和媒体领域,媒体通过对事实的收集、核实来展开报道和评论,学者通过对事实的收集和分析,摸索社会规律,并对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政府官僚机构处理和收集数据,勾画社会改革的蓝图并予以实施。它们的权威取决于立场的客观性,与政治无关,而社会公众也愿意相信这些人,认为他们能够克制自己的情感和个人观点,不是为了一己私利或者政治意图,而是通过发挥自己的知识专长和职业技能,为公众服务。
戴维将此称为和平主义或维持和平的心态,并指出这种维和思想将特定问题排除在政治范畴之外,为解决分歧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愿景,有利于达成实现社会合作所需的最小限度的共识。这种思路建立在启蒙开启的真理观之上,人们相信,感官只是一种片面的直觉,具有欺骗性,只有理性才能获得普遍的、必然的认识。基于理性的政治活动,要求人们通过深思熟虑和激烈的辩论达成共识,并以宪法的形式将这种共识变成文化和制度化。作为这些活动展开的平台,公共空间成为自由社会得以开展的前提,而组织和传递这一空间的媒介,就成为自由社会健康运行的关键。
但与理性主义传统并行不悖的还有另外一个思想传统,那就是感觉的传统。这一传统认为知识不是可确证的,而只是需要被核实的,知识不是为了提供客观的世界图景,而是感知这个不断变化着的世界的一种方式。这种认识论发展出基于情感的伦理观念,它认为人类丰富的情感不仅仅有爱和同情,在心灵与身体、战争与和平之间的阴暗空间里,还存在一种紧张的状态,它让人恐惧、痛苦和焦虑。它让人越来越依赖感觉而不是事实,来认识和看待世界,它使得人们对于政治的期待,不再是建立在专家基础之上的技术化解决方案,而是希望它能够安抚内心的恐惧和焦虑。这就为政治家利用人们的情感进行煽动提供了空间,并使得政治过程不再是形成共识,而是动员群众,公共领域不再是基于理论论辩基础上的协商过程,变得更具有冲突性和战斗性。
戴维指出,十九世纪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正是建立在这一情感认识论基础之上。二十世纪晚期全球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运动,将包括知识生产在内的一切领域都商品化,知识以“知识产权”的形式被法律保护起来,在市场上当作商品被出卖,带来特权群体对知识的垄断。基于算法科学和偏好设置开发的数字技术,更是加剧了公共空间的瓦解和断裂,社交媒体的精确定位功能,不断将公共社区部落化,网络空间的开放性特征被这种数字围墙所打破,缩小了交流的范围;各种精准推送,加剧了人们的彼此疏离和猜疑。

其后果就是十七世纪确立的共识政治崩塌了,媒体变得不可靠,传统政治家被忽视或质疑。人们普遍认为,各个行业的专业机构除了保护自己的特权之外,别无他用,民粹主义煽动者在世界各地兴起。频发的社会冲突,给人一种找不到解决方式的错觉。当一九九二年美国剧作家史蒂夫·特西奇(Steve Tesich)首次使用“后真相”(post-truth)一词,他力图传达的正是这种“情绪的影响力超过事实”的生存状态。二〇一四年,拉尔夫·凯斯(Ralph Keyes)敏锐地捕捉到西方精神的蜕变,将当代社会描述为“后真相时代”,认为在当今媒体驱动的世界,欺骗越来越普遍,谎言不再被视为不可原谅的东西。
03 “信息战”的内外之维
后真相不仅改变了国内政治的运作逻辑,而且发展出了更新的国际斗争形式,这主要体现为“混合战争”(hybrid warfare)的理论和实践。在《俄罗斯的“混合战争”:复兴与政治化》(Russian “Hybrid Warfare”: Resurgence and Politicization)一书中,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研究人员奥费尔·弗里德曼(Ofer Fridman)对混合战争的概念进行了细致梳理。他指出,混合战争概念来自美国军事理论家弗兰克·霍夫曼(Frank Hoffman),他试图用这个概念去解释美国面临的诸如恐怖主义、犯罪行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在这之后,一批俄罗斯军事理论家在俄罗斯政治经验、军事经验以及对战争现象的理解基础上,重新定义了混合战争的概念,将它演变成政治行为体通过侵蚀对手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合法性和稳定性来削弱对手的方式。经过这种改造,混合战争就变成一国动用所有的机制,对他国政权进行渗透、影响和颠覆的政治行动,它不是将特定冲突升级为直接的物理军事对抗,而是在内部腐蚀和破坏对手,以实现某些政治目标。

在信息时代,混合战争的主要形式表现为信息战,它将战争理解为一场争夺精英和社会群体思想控制权的信息斗争,主要目的是通过控制和操纵信息趋势,散布虚假消息,来颠覆对手的政治力量,这些信息趋势决定了精英阶层的行动,特别是公众舆论。弗里德曼指出,混合战争在俄罗斯已经从理论付诸实践,被俄罗斯广泛地应用于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东欧和西方世界其他国家,二〇一六年俄罗斯对于美国大选的各种干预,也成为混合战争的突出表现。
初看起来,信息战似乎是信息时代的新战争形式,但与其说它是国际斗争问题,不如说它是国内政治的外延,西方有关信息战的大讨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作为这些讨论的主导者,北约集团、学术界和西方政治的建制派,将这些议题政治化,通过不断渲染俄罗斯混合战争的威胁,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对北约而言,在一九九一年华约解体之后,它就陷入了关于自己存在必要性的辩论之中,在这场认同危机背景下,俄罗斯威胁的复活被证明对北约领导层是有利的,它能够迫使北约成员国将资源投入到传统军事挑战之外的一系列活动中,并强化该机构作为西方价值观主要捍卫者的地位,为中东欧国家寻求西方盟友的保护,提供了借口。而对西方学术界而言,通过宣扬俄罗斯混合战争对西方世界的威胁,学者们获得更多参与政策制定的机会,并获得更多体制内的资源。对西方政治建制派来说,俄罗斯干预他国事务这一观点被不同的政治团体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所利用。在英国,俄罗斯被指责影响了英国脱欧公投;在德国,俄罗斯被指责破坏了总理默克尔的连任机会;在美国,俄罗斯被视为为了确保特朗普当选而干预大选。
由此看出,围绕混合战争和信息战的学术和政策研究,本身已经形成一种产业和一种叙事结构。在这种叙事中,俄罗斯是否真的发动了信息战本身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叙述所营造的话语生态,为军事官员和政客们推动自己的议程提供了机遇,并利用这种危言耸听的形象来获取国内政治利益。于是,一个地缘政治斗争背景下的国际秩序问题,在后真相时代下被不断放大,被不同党派拿来用作政治宣传和攻击的武器。
各种虚假信息运动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竞相上演,“灰色地带”成为战争主战场,理性和科学不再被信奉,专家和机构不再被信任。在这个意义上,后真相时代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历史进程,启蒙所启示的真理被激情的宣泄取代,共识的破产意味着党派时代的回归,多维度的大国竞争正在加速,如此真能开启下一轮的“百年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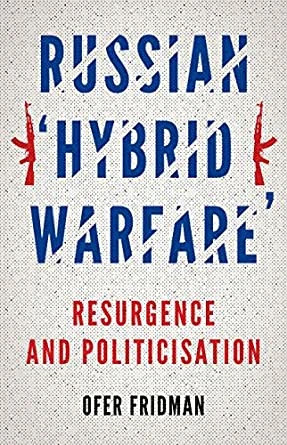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