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1784年2月22日,“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港启程,前往中国广州贸易。由于美国没有单独与中国交往的经验,在国会颁给这艘船的航海护照(customary sea letter)上,撰写者毕恭毕敬地把所有可能遇到的官员、贵族和统治者的称呼都写了上去:
“致所有的不管是否是奉教抑或世俗的好的城市和好的地方的至贵的、至高的、无上的、受人敬仰的、尊贵的、高贵的、权威的、睿智的和英明的君王、皇帝、国王、共和国主、亲王、公爵、伯爵、男爵、贵爵、镇长、议员、法官、将官、司法代表和摄政代表们。”
彼时这个刚打完独立战争的新兴国家面临英国的经济封锁,美国商人迫切希望能够与遥远、陌生却充满机遇的中国通商——在那之前,中国的茶叶早已风靡北美,商业嗅觉敏锐的美国人意识到,如果能够亲自前往中国采购茶叶,将是一门一本万利的生意。开展洲际远洋贸易是中美相遇的初衷,然而这段初遇在接下来一个世纪里中国与欧洲列强的强烈冲突面前黯然失色,湮没于历史长河。
在《中美相遇》一书中,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元崇从追溯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开始,回顾了1784年至1911年中美早期交往的历史。处于太平洋两岸的两个“最年轻”和“最古老”的大国,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相遇相知,在中国长久以来的宗藩朝贡体系和远道而来的西方国家急欲建立的现代国家外交体系的冲撞之间、在大清帝国日薄西山和美国走向霸权之路的强烈对比下产生种种恩怨情仇——重温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当下中国与美国、与世界的关系。
日前,王元崇接受了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电话联线采访。他表示,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既有中美国际关系变化导致的现实关怀,也有对中美两国年轻人未来的考量——在他看来,中国恢复世界大国和东亚地区领导力量的地位已经是一个势不可挡的趋势,在这样的条件下,中美两国都应该跳脱出自己的认知局限,重新认识对方。“我要做的就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个‘历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事’的视角,为理解当下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提供一些帮助。”除此之外,他还与我们讨论了他对长期存在于中国历史教育中的线性和屈辱历史观的批评、对历史学家从事通俗写作的看法和对海外中国研究的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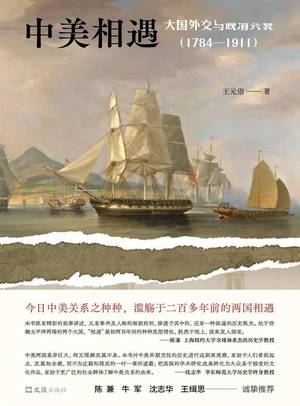
王元崇 著
新经典·文汇出版社 2021-1
01 中美两国都存在认知局限,加强知己知彼是这本书最重要的关切之一
界面文化:你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王元崇:这个系列起源于我从2016年开始开设的中美关系史课,这是一门给高年级本科生开设的讨论课。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变得不那么温馨了,在朝一个不太良好的方向发展。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非常片面和狭隘,不像我们对美国了解那么多。我的学生中有两个很大的群体,美国学生和国际学生,其中国际学生中最大的群体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对我来说,这些同龄的孩子迫切需要做的就是了解他们彼此的国家——虽然他们现在坐在同一个课堂里,但他们对彼此国家的了解差别很大。我就想开一个中美关系史的课程,讨论之前发生过什么事。
后来澎湃新闻的编辑单雪菱知道我在做这件事,建议我写一写教案里的东西,我想也好。中美关系的著作大多是围绕冷战、朝鲜战争叙述的,关于之前的历史不是很多。这本书本来是给澎湃写的专栏“中美浮梦录”,集结成书时重新调整了结构,加入了近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大框架,因此书里不只是说中美两国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相关著作,这不是我要做的事——我关心的还是在中国方面,所以成书的时候增加了中国外交、中国自身的体系。
另外,我在康奈尔大学读书的时候发现图书馆里有很多中美关系史的资料,但(学者)都没有用过。我看到蒲安臣的照片曾经广泛刊发过,有很多图书馆都有原始的照片副本,背后还有签名什么的,就想为什么不用呢?所以应该说这本书是一连环的反应:有中美国际关系变化导致的现实关怀,也有对同龄中美两国学生的未来考量。
界面文化:书中你数次提及美国教育对世界史缺乏关注,值得玩味的是,在美国高校内,后殖民理论、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潮已出现多年,理论上来说应该会影响历史教学。为什么没有呢?
王元崇:美国对世界史教育其实很重视的。我们系很多教员都在教世界史,但它面临的一个问题就和我们中国人学世界史一样,每个国家都不可能深入,走马观花。另一个现实因素是从幼儿园开始美国学校没有统一的历史教材,各个州可以自选。中美两国这一点差别很大,这对历史记忆的形成甚至身份认同有很大的关系。导致的现象是,很多州的学生根本没怎么学习世界史,欧洲史都很少学,都在学美国史。稍微好一点的州会在中学开设世界史,但世界史中的中国,就是用一两章的篇幅概括从秦皇汉武到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全部内容。我接触到的绝大部分美国学生,不光对中国了解很肤浅,对日本这种跟美国关系很好的伙伴国家、越南这种曾经有过深刻痛楚的国家都是印象一片模糊。这个现象绝对不能拿中国的中学生和美国同龄的学生对比。
界面文化:某种程度上来说,关注自身是大国普遍存在的一种“历史包袱”。你在书中提到的一个细节——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沿用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中把中国放在地图中心位置的惯例,而美国出版的世界地图则非常“欧洲中心主义”。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你认为我们是否需要以及应该如何逾越这种认知局限?
王元崇:这个例子是我到美国之后才发现的,它和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全球史密切相关。利玛窦到中国后奉行耶稣会自上而下、本土化的传教策略,他在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时融合了中国的天下观,把中国放在了世界中心——他应该知道这和欧洲的惯例完全不同,是一种迎合中国人观念的表现。恰恰因为如此,中国人进一步认定了中国是文明中心的概念。我们曾经有“泰西”的说法,“泰西”是“极西”的意思,从中国地图上来看,你会感觉欧洲在中国的左边,隔了那么远。泰西真的是泰西,而美国就成了“远东”了。但我们从来不会说美国是远东,“近东”“中东”“远东”这些词都是欧洲人从他们的地图出发发明出来的。
这完全是欧洲殖民话语在过去数百年全球化的结果。我们不可能跳脱出这个东西,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国家国民记忆再生产的问题。我想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大家,甚至在一些非常直观的认识上,中美两国都存在着彼此的认知局限。虽然逾越这种认知很难,但加强知己知彼是我写这本书最重要的关切之一。

界面文化:你指出,中美关系史的著作主要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大事件为主,对中美两国最初相遇的时期着墨较少。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感到,起码在大众的认知当中,我们对“中美相遇”的源头是缺乏认识的,甚至可能还不如我们对日本1853年“黑船事件”的认识。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情况?
王元崇:也不能说历史学家不重视,但一般的做法是关注历史事件比较集中爆发的时期。比如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线索基本都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等有着比较剧烈表现的时代。对那个时代有更多的关注,是因为它产生的后果也比较剧烈,比如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甲午战争的马关条约。
早期中美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因为美国没有明确的亚洲政策,所以表现得相对平稳。从1784年前往广州,到1898年抢占菲律宾,美军真正来到中国还是两年以后的八国联军。这100多年里美国的对华政策相对温和,因此两国之间没有什么波折。这段时间历史学家关注比较多的还是中英、中法关系。两次鸦片战争都是英国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也参与了,所以表现比较剧烈的还是所谓的欧洲列强。
中国当代记忆是另一方面。对共和国人的历史记忆来讲,清代的中美关系已经是前前朝的事了,是一个非常“历史”的事件,20世纪的历史记忆是更鲜明的。所以从历史编撰法的角度来说,大家侧重的还是20世纪发生的、美国已经崛起为全球帝国主义国家以后跟中国发生的若干交往。事实也确实如此,比如美国支持国民政府、二战,紧接着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是20世纪中后期发生的。无论是历史现象本身出现的时间段,还是我们中国人自身的历史编撰法中的渐进记忆,都导致大家把重点放在了20世纪。
02 中国恢复大国地位不可避免,但不能再延续线性和屈辱史观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出,“闭关锁国”是我们长期以来对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的刻板印象,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与其说是“打开国门与否”的矛盾,不如说是宗藩朝贡体系和现代国家外交体系的矛盾。能再展开讲讲这一点么?
王元崇:这主要是针对我们历史教材的叙述而说的。长期以来我们认为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是闭关锁国的,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加快了,相比之下之前的状态好像就是“闭关锁国”。但这种叙事背后的逻辑是欧洲中心主义,就是把历史进步的标准放到了欧洲语境内。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多:美国打开了日本大门、日本打开了朝鲜大门、英法打开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大门……感觉他们来之前我们都“关着门”,来了之后我们才有了开发和变化。
但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已经在自己的系统中相当开放稳定,是一个和世界各国有广泛交流的国家。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已经在广州住了起码240年了,对这一基本的事实,如果用“闭关锁国”来形容的话,就是违背现实的。另外,“打开国门”还有一个“谁来打”的问题:施动者是文明的载体,但我们忘记了中国本身同周围国家的交流一直存在。这个叙述模式不仅是欧美中心主义的体现,还消解了中国文明本应具有的地位。就清代而言,中国和越南、朝鲜、琉球、蒙古、俄罗斯有频繁的交流,但后来这个“外国”的概念出现了窄化,变成了专指欧洲和美国。其实宗藩朝贡体系已经运行了数百年,和现代国家体系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关系,鸦片战争之后宗藩体系还是同时存在,一直到甲午战争之后才算是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历史编撰法的问题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现实的考量,即今天的中国人为何要批评闭关锁国叙事。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总量即将超过美国的国家,19世纪的屈辱史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常态,放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来看不过是100年的非常态。中国恢复到稳定的大国世界地位以及东亚世界的领导地位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够再延续以前的屈辱史观——如果还继续把自己放在一个被欧美殖民主义侵略、积贫积弱国家的位置上,一方面无法担任起一个大国应该具有的世界领导责任,另一方面也会给新一代的集体记忆产生一种负面影响。
界面文化:书中的记述是从清朝建立开始的,我们知道,也是从17世纪开始,国际交流加快,跨国贸易开始极大地改变世界的面貌,对此卜正明在《维米尔的帽子》、彭慕兰在《贸易打造的世界》中都有所论述。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当时的中国面临的“冲击”,其实是西方向往的贸易和它所需的制度安排在中国缺失所导致的?
王元崇:就是这样。美国人、英国人来了要签条约,中国人是不知道这套规则的,我们有自己的法律制度。大清法典甚至比英国的法律完美得多,当时英国没有如此严密的成文法典。但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中西之间之所以会产生冲突,就是因为中国缺乏一个西方国家可以进入操作的系统,他们想把这个系统建立起来。所以鸦片战争之后建立了条约体系,产生了上海这种通商口岸,然后辐射到其他地方。有了这样一个制度之后,就可以绕过中国本身的秩序办事。
界面文化: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来到广州;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四艘军舰来到日本。前者淹没在历史中,后者则因促进了日本近代化转型而在史书中留下了重要一笔。从甲午中日战争至今,中日两国在面对西方冲击时走上的不同道路被一代代的知识分子所分析讨论。你作为研究清代中国外交史和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史的学者,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王元崇:的确,到今天好像很多人还在比较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洋务运动。从一定意义上来讲,1853年黑船来航之于日本相当于鸦片战争之于中国,而1784年美国商船抵达广州则什么都不是,就是做生意来了:当时美国刚刚成立一年——1783年巴黎合约正式认定美国是一个独立国家——美国人迫不及待地来到中国,目的不是改变中国的秩序,只是要去打开国际市场赚钱。当时的美国需要中国,因为中国的茶叶对当年的北美殖民地来说是一个一本万利的生意,他们把皮毛运到中国,把茶叶换回去,茶叶就相当于今天的巧克力、咖啡在中国的地位。实际上,1853年美国人前往日本也不是为了征服日本,就是想签个贸易条约。
但日本对这件事的反应很大,这在日本国内导致了连锁反应。当时的日本处于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将军而非天皇掌握实权,但将军没有资格签订条约,必须找天皇。这样的话就要实行“大政奉还”,把权力重新还给天皇,所以才出现了明治维新。因此黑船来航直接导致的不是所谓的打开日本大门,而是造成了日本内部非常重要的政治权力转移——大权从幕府将军手中历史性地转移到了天皇手中。可以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完成了大规模的内政改革,而这种改革在中国是没有的。
我们羡慕日本,是因为日本相对成功地完成了近代化,也就是说我们认可了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而在“打开大门”的这条单线进化史观上,我们认定日本取得的成绩比中国要大得多,以至于很多人对此感到惋惜,觉得中国没有实现日本那样的近代化真是糟糕。但我们忘记了,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那样剧烈的改革,是因为中国秩序本身是很稳定的。日本黑船来航以后是王政复古,然后马上出现了内战。明治维新派在内战中取胜才能够继续推行下面的政策,但内战对日本的消耗也很大。

今天要做中日比较,我们当然要看为什么中国洋务运动最终没有达到日本明治维新的近代化结果,但我们也要看中国自身好的方面。虽然中国有很多屈辱的历史,国家也的确曾经疲弱不堪,但中国没有演变为一个像日本那样的殖民主义国家,也没有给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当下的日本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甚至不是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美军就驻扎在家门口,宪法是美国人制定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是不是我们中国人需要的?长远来看,我觉得中国未必做错了。可以预想,如果中国像日本那样发展为一个所谓的“大中华帝国”,给整个世界带来的灾难远远不止一个大日本帝国带来的程度。
界面文化:贸易其实是美国在建国之初就迫不及待地与中国建立联系的初衷。在了解到这一点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当下的中美贸易争端呢?
王元崇:过去几年中美关系变化较大,我们很多人面临的一个大任务是重新认识美国,要重新认识美国,就要去看美国历来的外交政策是怎样的。美国也开始重新反思自己的对华政策。所以在这个历史关头,我认为我们应该去了解历史上,尤其是早期中美外交史上,当中国还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大国的时候,和美国的交往是怎样的。看看当时发生了什么,对了解后来的大国关系,我觉得会有所帮助。
当下的经贸摩擦,难道就一定要一条胡同走到黑么?我觉得也不见得。中国是全球消费人群最多的一个市场,有望在未来几十年内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国家。长久来看,美国必将降落到大清国看初来乍到的美国的那种地位,中国将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庞大统一的市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变化,它正在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如何应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作为历史学家我知道的也很有限,我要做的就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个“历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事”的视角,为理解当下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提供一些帮助。
03 追捧史景迁却看不起二月河,这真是个悖论
界面文化:在前言中你写道,“当代中国学界的专业历史学者在大众读本的写作方面,用力仍嫌不足,这导致了历史学家的很多专业知识无法很好地服务于社会与大众,两个群体距离越拉越远。”之前北大历史学教授罗新也指出过类似的问题:中国的历史学家似乎认为面向公众的书写是“不入流”的。但我们看到近年来外国的历史作品大量引进国内,很受大众读者欢迎。据我的观察,此类作品既通俗易懂又能保证学术严谨度,能够做到雅俗共赏。根据你的观察,海外历史学者是如何看待面向学界的书写和面向公众的书写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王元崇: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它是我们中国学界长期以来的顽疾。美国学界没有学术和通俗的划分,一般大学出版社面对的是专业读者,但在美国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历史学家在商业出版社出版非常通俗易懂的著作,认为这样才真正对公众有所帮助。史景迁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耶鲁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他写的作品很难区分是史学还是文学——他能够用非常文学化的手法,把一些事情讲得通俗易懂。他的《追寻现代中国》当年冲上了《纽约时报》的阅读榜单,此前没有任何一位历史学家做到过。这个路数对不对?也很难说。虽然他对清史的理解可能和二月河都没法比较,但中国国内有大批的读者追捧史景迁,另一方面我们很多人又不太看得起二月河,这个问题发生在哪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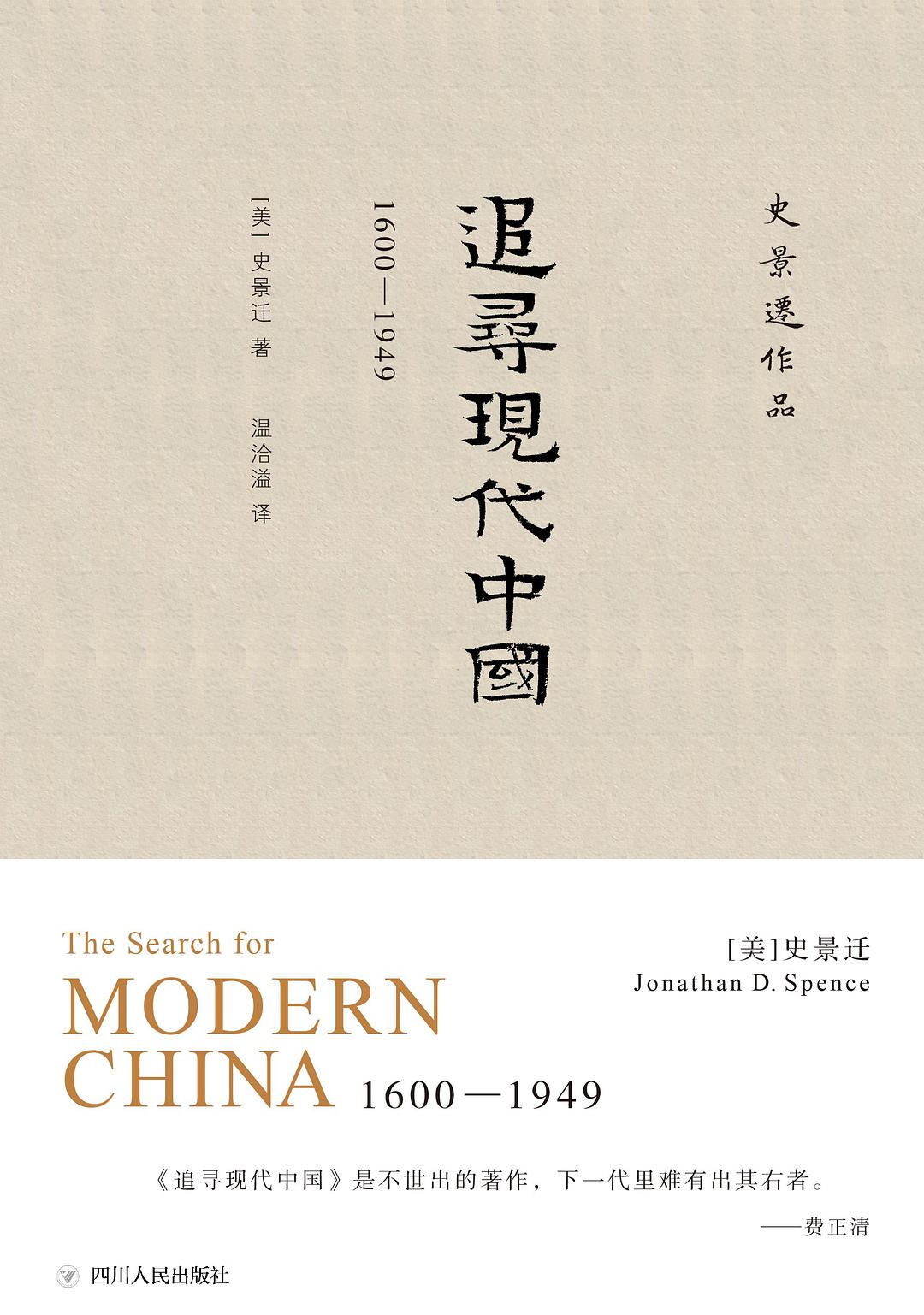
[美]史景迁 著 温洽溢 译
理想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05
这真是一个悖论。我们长期以来盲目地以欧美学界的话语为中心,好像美国人这么做我们可以接受,而本国人这么做就觉得你是在“下海”,其实没有这个必要。这个方面日本韩国表现得也很突出。比如日本的岩波文库,就是一套给大众读者看的丛书。但中国的同仁大部分都在做比较学科化的研究,很少有人去写面向大众的作品,逐渐这两个群体距离就越来越远了,失去了经世致用的价值。我有的时候和学生开玩笑,说如果司马迁活在当下,连大学教授都评不上,因为人们会觉得他的作品不算是历史学著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悖论,但我想随着我们慢慢发展,情况应该会变好。
界面文化:我去年采访了艺术史学家包华石(Martin Powers),他表示在当下的地缘政治情况下,美国有可能会重现冷战风格的学术生产,即确立欧洲中心主义,证明“我们”比“东方人”更优秀。你是否有这样的担忧呢?
王元崇:很多人会有这种担心,我个人倒是没有,我觉得冷战风格的学术生产是很难回去的。欧美中心主义在学界早就被解构,七八十年代以来对欧美“东方主义”的反思的兴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讨论这样的东西,包括我这本书在这个时代出现,本身就是西方霸权破产的结果。而且有那么多东亚国家的学者、印度的学者、非洲的学者融入美国学界,他们是回不去的。唯一值得警惕的是学术在多大程度上会受现实政治的影响。
界面文化:我注意到这两年国内也有一些对海外中国研究的批评,对新清史的批评即为一例。你怎么看海外中国研究的价值?
王元崇:我上大学的时候,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系列”丛书对我们形成了很大的冲击,无论是写法还是多元的分析角度,都对我们冲击很大。海外中国研究不适用于中国的观点我也可以理解,有的美国学者有一些在我们看来不好理解的结论,比如清代不是中国——中国人绝对不会有这种想法,因为清朝就是正统的中央王朝。但美国学者注重少数民族的主体性,这是因为他们在美国社会中接受学术训练,特别关注族裔身份问题,从印第安人到非裔、华裔和所有有色人种,这是他们非常敏感的点,于是在中国研究领域的这种表现可以说是美国社会和政治转向在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再反映。
对研究结论进行批判是应该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学习。比如新清史的研究虽然可能存在一些错误陈述,但在研究中采用汉文史料、满文史料、蒙文史料、藏文史料的做法,是不是我们应该吸取借鉴的?我们不能老集中在政治路线上去批评,长远来看没有必要。而且美国学者本身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就是美国本身政治社会的理念变化投射到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中。我觉得对话是必要的,不管是肯定还是批评。最重要的是要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我们现在好像就是知其然,但不知道它背后的原因。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