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火线》主创大卫·西蒙(David Simon)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照片,内容是俄勒冈州某处高尔夫球场外已经燃起熊熊山火,打球的选手们却依旧泰然自若,不紧不慢地将球推入洞中。“在当今美国诸多视觉隐喻的万神殿里,这个镜头是最出彩的,”他就这张图片谈道,照片是某位业余摄影爱好者拍下的,她在准备从飞机上跳伞时捕捉到了这一抓拍机会。与这个故事有关的一切——图像和背景——看起来似乎比小说还要荒诞不经。
在西蒙发布这条推文之前一年,印度小说家阿米塔夫·高希在其里程碑式的论战性著作《大混乱:气候变迁与不可思议之事》(The Great Derangement: Climate Change and the Unthinkable)当中拷问了为何作家们——包括他自己——在小说里几乎都不去触及世界上最为紧迫的问题。然而,如今极端气候已席卷全球,导致冰川消融、森林大火、区域性洪水以及物种灭绝,气候危机业已将许多不可想象的东西带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文学。在杰西·格林格拉斯(Jessie Greengrass)富有挑衅性的新作《高巢》(The High House)里,一名幸存者总结道:“整个现代性的复杂系统把我们高高举起,使我们脱离地球,而今它摇摇欲坠……我们也再一次变成了自己以往的样子:冷漠,恐惧天气,以及恐惧黑暗。不知为何,在我们日理万机,忙于各类有利于提高生活质量的琐碎小事的同时,未来却从当下溜走了。”

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尝试以新兴的气候变迁类虚构或曰“气幻”小说(climate fiction/cli-fi)来直面这场渐次展开的灾难,格林格拉斯正是其中一员。再如,爱尔兰作家尼尔·伯克(Niall Bourke)的《线》(Line)构思出了一幅博斯式的(Boschian,耶罗尼米斯·博斯为15-16世纪荷兰画家,以刻画堕落与沉沦著称,其作品晦涩难解、想象力丰富且大量运用象征和符号,被认为是20世纪超现实主义的先驱——译注)图景,讲述了一群难民在干旱的土地上守望了许多个世代的故事;而贝塔尼·克里夫特(Bethany Clift)的《派对上的最后一人》(Last One at the Party)则是一个三十来岁的无名女人的日记,身为一场疫病的唯一幸存者,她打定主意要游戏人生、娱乐至死。今年8月,亚历山德拉·克里曼(Alexandra Kleeman)的《太阳底下有新事》(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则将带领我们体验因气候变迁而毁于一旦的近未来加州。9月,以《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获得普利策奖的安东尼·多尔(Anthony Doerr)亦将推出新作《太虚幻境》(Cloud Cuckoo Land),背景设定在15世纪的君士坦丁堡、2020年的爱达荷州以及未来某一时刻的宇宙空间。多尔曾就此书表示:“我们繁衍生息的世界充满了各种挑战:气候的不稳定、流行病、扭曲的信息。我希望这部小说能反映这些焦虑,但同时也提供有意义的希望。”
那么,自高希推出《大混乱》以来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我想,是世界改变了我们,2018年是转折点,”如今他这样说道,“原因部分地在于那一年的许多极端气候事件——加州山火、印度洪水、层出不穷的狂风暴雨,但还有一部分因素关乎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树语》一书的出版。”

[美]理查德·鲍尔斯 著 陈磊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九天译文 2021-7
对一部小说来讲,这种提法未免托大。但高希表示,他的要点在于,重要的不仅仅是书本身,还在于它收获的广泛好评(包括入选布克奖短名单)。“它并没有再度落入气候变迁或推测性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的窠臼,反倒被视为了一部主流的小说。我确实认为这是一件大事。自那时以来,该领域涌现出了许多作品。我的个人收件箱每天都会收到两三份手稿。”
鲍尔斯这部获得普利策奖的小说,将人类的生活简化为了更为宏大的树木生命历程中的一圈细细的年轮,书中各个角色的故事相互独立而又有短暂的交织,这些故事围绕着个人与制度、良心与贪婪等一系列决定着人类未来的冲突展开。加拿大作家迈克尔·克里斯蒂(Michael Christie)于2020年再度套用上述结构,创作了鲜活的生态寓言《绿林》(Greenwood),时间跨度设定在1908年至2038年,其间一种致命的新型孢子在所谓的“大凋零(the great withering)”中杀死了所有的树木。

两部小说的核心均指向一场辩论:构成生命本身的究竟是什么?在《树语》里,一名研究人员因胆敢认为树木也有其自身的意识形式及社群而遭到了众人的排挤,而一名天赋异禀的电脑高手则意识到,树木向万物隐藏了这一秘密。在《绿林》里,杰克在一处富有未来色彩的自然主题公园里担任导游,他反思道:“一棵树即便是在生命力最为旺盛的时候,其细胞组织里也仅有10%——即最外面的那一圈年轮和边材——能够被称为是活着(alive)的。每一棵树都有其自身的历史作为支撑,那是它一代又一代先祖的骨骼。”

考虑到方兴未艾的 “自然的权利(rights of nature)”运动,此说也并不那么异想天开,罗伯特·麦克法兰(Robert Macfarlane)形容这一运动为“新生灵主义(the new animism)”。两年前,麦克法兰曾提到过,美国托莱多市居民为伊利湖紧急起草了一部“权利法案”,赋予其法律人格,并规定它在法律上享有“存续、繁盛与自然生长”之权。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生态系统并非人类,它们绝无可能承担任何人类的责任,”法案的起草者们如此主张,“毋宁说,自然要求其自身的特殊权利,以承认它的各项需求和特质。”
这部法案也表明,现行的法律和智识框架要容纳人类之外的实体理念殊为不易。“(气候)危机要求某种形式的文学表达,以将它从既有知识的藩篱中提炼出来,并使它对读者产生深入骨髓的影响,”一名颇有见地的读者在亚马逊网站上的气候变迁类虚构小说集《暖上加暖》(Warmer)评论区这样写道。该书出版于2018年,其中的各个故事皆独立成篇。
我们究竟还需要怎样的故事?如何才能开启新的篇章?“一个人可以讲述许多不同种类的故事,但就小说写作来讲,并没有一般性的答案,而只有特定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说道,她的“末世三部曲”探讨了环境崩溃之后的余波里可能发生的一切。气候变迁类虚构作品通常以一种人们熟悉的隐喻为基础:大灾变催生而来的噩梦般的、全新的现实。在约翰·兰彻斯特(John Lanchester)的新作《壁垒》(The Wall)里,“变迁”侵蚀了海滩,把英国变成了一个要塞国家,年轻的守卫在岸边巡逻,奉命摧毁一切接近的船只。凯特·索耶(Kate Sawyer)的处女作《搁浅》(The Stranding)6月24日刚上市,该书揭开了一幅震撼人心的图景,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藏在一头搁浅的鲸鱼口中,以此为掩体躲过了致死性极强的辐射。
不论是《高巢》还是鲁曼·阿拉姆(Rumaan Alam)2020年的一鸣惊人之作《把世界抛在身后》(Leave the World Behind),均有非同寻常的建树。阿拉姆笔下的主角们生活在长岛的度假别墅里,该处因一场神秘莫测的噪音灾难而与“文明”相隔绝,这股噪音的尖锐程度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声音。“你无法听到这种噪音:你只是体验它,忍受它,幸免于它,见证着它。你可以恰如其分地说,这些人的生活乃是截然二分的:听到噪音以前和听到噪音以后,”他写道。在《高巢》里,一间充实的谷仓使自给自足成为了可能,书中某角色的科学家母亲在里面装满了各种过往文明的器具——运动鞋以及各种食品罐头。

格林格拉斯称自己的小说是罗素·霍本(Russell Hoben)的著名乌托邦幻想小说《瑞德里·沃克》(Riddley Walker)的“某种前传”,在没有书写材料的情况下,语言发生了退化和变异。她的《东英吉利》(East Anglia)和阿拉姆书中的长岛类似,都处在沦为反面乌托邦的边缘,但实际上又没有彻底堕落。两部小说里的角色皆被困在“以往”与“此后”之间,或者说正好身处一种难以用笔头来形容环境崩溃的尴尬境地。
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洪水之年》到芭芭拉·金索沃的《飞行行为》(Flight Behaviour)里犹如“燃烧的灌木丛”的橙色蝴蝶群,灾变类虚构作品长期以来都与圣经里的形象有着微妙的关联。《高巢》与《搁浅》均化用了诺亚方舟的故事,其中不乏藏身于密闭空间而幸免于难的家族社群,同时也含蓄地提出了如下的问题:在一个没有橡树或者鸽子的世界里,以这种方式存活的意义何在?
在2019年的小说《枪岛》(Gun Island)里,高希运用了神话与神秘主义等元素,还有历史上的语言、动物与人群在全球范围内的运动,就自己提出的尖锐问题给出答复。小说的高潮是一场鲸鱼和海豚的大举迁徙,这一不太可能发生的离奇事件同时也是一种可观察的物理现象。这部小说在其核心处重现了弗洛伊德所定义的“诡异(uncanny)”,即一种抹除想象与现实之区分后产生的效应。
阿拉姆也诉诸诡异元素来切入《把世界抛在身后》的超现实表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一群降落在后院游泳池里的火烈鸟。 “它们既滑稽又令人不安,”这位小说家说道, “它们是一抹似乎不应该出现在自然界里的色彩,但又确凿地存在着。它们也肯定不该在美国东北部亮相,这就好比在伦敦市中心遇见斑马一样。在我看来,这有些小小的神秘色彩,类似宙斯化身为天鹅降临世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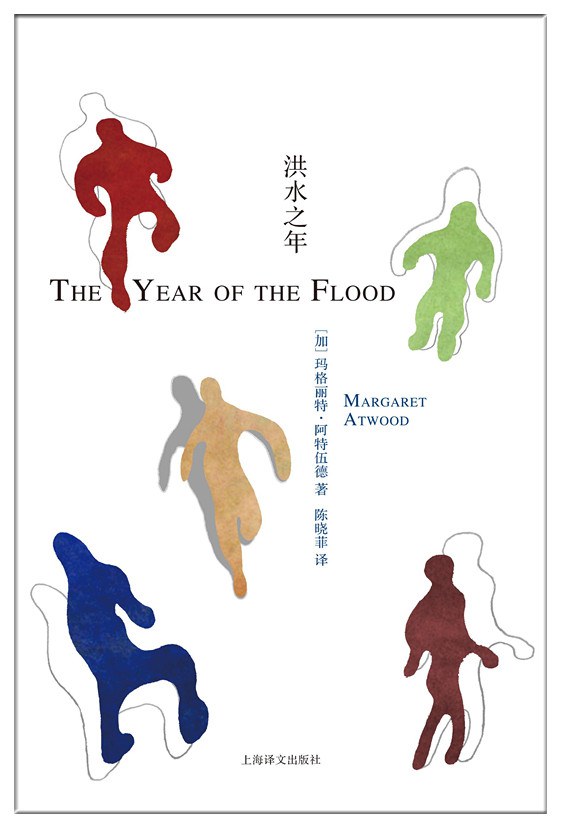
[加拿大]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 陈晓菲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3
火烈鸟的到访还带有一种古怪的惊悚感。“我认为,我们对新闻里的各种恐怖与奇特的瞬间已经司空见惯,而我们必须把这些元素设想为诡异之事物,因为它们包含了一些我们现时尚且无法理解的东西,”阿拉姆说。他引用了一幅颇具冲击性的画面:在岸边搁浅的移民小艇旁溺毙的小孩。“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人,直面这些瞬间是令人心碎的,同时也是我们的羞耻。但在这当中也有一些让人死活捉摸不透的要素:一个小孩莫名其妙地躺在海岸边,给人的感觉很像某种出自民间传说的桥段。”
与《枪岛》相似,《把世界抛在身后》也是一部有意而为的混合式小说——部分是社会喜剧,部分是推理性的恐怖故事。混合性(hybridity)的要义在于处置一项核心冲突,即我们之所是(社会性的存在者,处在由诸多为人所熟知的仪式建构起来的生活中)与我们面临的挑战(用格林格拉斯的话说,灭绝将十分彻底,以至于“没有教堂大厅里的追悼会。没有人能谱写歌谣。不会留下任何东西”)。
澳大利亚作家夏洛特·麦康纳吉(Charlotte McConaghy)的《最后的迁徙》(The Last Migration)游走于魔幻、假想与人居环境之间,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远航故事,藉此追踪了世界上最后一批飞越公海的候鸟,盼望着它们能揭开最后一群鱼类的下落。书中的叙事者弗兰妮(Franny)对她追踪的三只搭载示踪设备的北极燕鸥里的一只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已经把她的一切都设想成自己的,因为她已经钻进了我的胸腔,在我的胸中安了家,”她说道,而现实则是这只鸟不过是声纳面板上的一个点,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
杰夫·范德梅尔(Jeff VanderMeer)在《蜂鸟蝾螈》(Hummingbird Salamander)同样拥抱了某种混合性,一反他平常在推测性小说里围绕某个失踪的生态恐怖分子来展开紧张激烈的惊悚情节的惯例。“在思考环境问题时使用‘我们’这个词,会抹杀掉所有不同版本的‘我们’,”逃亡中的西尔维那(Silvina)如是说,“许多原住民就不是这样想的,反文化者也并不总是这样想。足以解决我们问题的哲学、知识和政策已经存在了。”
其它一些作家则以完全拒斥按部就班来应对叙事上的挑战,如珍妮·奥菲尔(Jenny Officll)在她文风泼辣的小说《天气》(Weather)里就做得非常出色,它由多少具有随机性的段落构成。各种与大灾变有关的格言拷问着叙事者、图书管理员莉琪的良知(“起先他们盯上了珊瑚,但我却没有开口,因为我不是珊瑚……”),她的“猿猴大脑”担心在一个没有牙医的世界里自己的牙将会怎样,而她社会化了的部分则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把唇膏涂到了牙齿上。
探索以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沮丧及混乱状态的,不只有气候变迁类虚构小说。在莎拉·莫斯 (Sarah Moss) 的《夏之水》(Summerwater)里,度假者们设法在不合季节的豪雨中尽情享受,全然忽视了只存在于各章节前言里的自然世界:濒临灭绝的蜜蜂,闭门不出的蚂蚁。在露西·艾尔曼(Lucy Ellmann)的《鸭子,纽伯里波特》(Ducks, Newburyport)里, 一只母狮试图保护其幼崽的安全,这条叙事线索处在主角的意识流之外,主角本人花了1030页的篇幅来铺陈她的生活琐事。

[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著 何娟/孙伟峰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 2021-1
莫斯和艾尔曼以不同的方式触及了意识的唯我论(solipsism)或者说自我中心(self-centredness)这一特征,它使我们在一开始就落入境地,此状况在我们所讲述的有关我们自身的故事里进一步定型和发展。二人笔下的角色都属于波兰小说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在其颇具启迪性的诺奖演说里谈及的“复调第一人称叙事(the polyphonic first-person narrative)”的囚徒,这种人透过故事讲述者的自我这副有色眼镜来看待万事万物。
托卡尔丘克的环保计划体现在生态侦探小说《糜骨之壤》里,她呼吁回归寓言的视角,以及发展一种她所谓的“更加克制的叙事者(tender narrator)”,即无所不知、方方面面都洞察无遗的叙事者的弱化版本。至于这么做会有怎样的后果,她表示自己还不知道,因为这种叙事者还没被发明出来。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摒弃传统的入流与不入流(high- and lowbrow)小说之分,以碎片为依托。“如此一来,”她表示,文学就可以“解放读者的潜能,令他们能把碎片统一为单一的构想,在事件的微粒里发现整片星空”。
但只要我们还在构想及讲述故事,我们就并非必然要毁灭。几十年来,阿特伍德的小说屡屡为暂且还不可见但已然降临的事物敲响警钟。“没有什么不可逃避的未来,正如没有什么不可逃避的历史的正确一边。没有什么不可逃避的毁灭之路,也没有什么不可逃避的奥兹(Oz,著名故事片《绿野仙踪》里的虚构国度——译注)之路,”她说,“但各种行动都有其后果,并非所有后果都能被预见到。黑暗乃巫师之道,对于小说家亦然。”
(翻译:林达)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