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微博上的一波讨论是围绕着“年轻人做自媒体靠不靠谱”展开的。自媒体在此处既是一种宽泛的职业范围,又暗含着非固定工作、(可能)不靠谱工作、以在网络上生产内容换取影响力为生的种种特质。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王炎也观察到了身边青年人的这种生活状态——他们职业不固定、没有稳定的同事圈子和上下级关系,他们一人身兼多职被称为“斜杠青年”,他们队伍日益壮大挑战着传统的劳动关系和工作伦理。
王炎在阅读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教授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的著作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的时候意识到,面对今天全世界范围内新兴的“职业”(或者人的新的生存状态),经典的无产阶级是否还存在、经典的阶级理论是否还有效,已是一个问题。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是否仍可以有效解释新的劳动关系?当我们仍试图用阶级话语剖解当下的物质焦虑,其中的文化错位是怎样发生的?这些斜杠青年和自由职业者,究竟是个人主义膨胀、社会责任淡薄的不安定因素,还是代表着互联网时代的终极方向、而知识界仍未提出有效成熟的理论工具去理解他们,甚至干脆视而不见抱残守缺?
《“阶级”之后,我们如何理解网络时代的职业与身份?》
撰文 | 王炎
以前我们以职业辨别人设,因为上世纪的职业是清楚的,很多人一生只从事一个职业,有稳定的同事和同行圈子,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如今,不少青年人以不从事固定职业而获得新身份——自由职业者或曰斜杠青年,也即下文提到的无固定工作者。
在前现代传统社会里,人以血缘、门第高低来决定社会地位,等级森严,难以逾越。20世纪则挣脱了封建秩序,人以劳动定义其主体,所有人在社会生产和分配的链条上获得社会身份,职业和工种成了现代人的社会标识。不仅如此,日常生活也把不同职业划入特定的社会空间,工人在厂区家属宿舍居住,干部在机关大院生活,相互间有趋同的生活节奏和内容,下班去同一家影院,子女上同一所学校。师傅带徒弟,老人教新人,传、帮、带滋养的工作伦理,维系彼此的信任与忠诚。

正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阶级”才有实在的社会基础,而不仅是占有财富的多寡。当然,现代社会仍残留着传统偏见,婚姻要门当户对,交友须身份对等,劳心者鄙视劳力者,等级观念仍禁锢着社会意识与行为规范。
01 阶级意识消失,19世纪的幽灵在互联网时代徘徊
到了21世纪,择业与劳动的内涵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无固定工作者人数大增。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教授盖伊·斯坦丁造了一个词“precariat”,即precarious(不稳定的)加上proletariat(无产者),合成“不稳定的无产者”。他用这一新造词形容西方社会中没有社会保障的临时工——他们既不属于工人阶级,没有长期劳动合同与工会的保护,又无社会保险,移民临时工甚至没有完整的公民权。

斯坦丁对这群人予极大的同情,他无情地揭露了全球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榨。但阅读过程中,我的脑子里却不断产生疑问:经典的无产阶级还存在吗?所谓的阶级意识在21世纪真能形成?人并不总因为贫困而与其他贫者共情而结成联盟。马克思笔下的阶级,不仅描述人的经济状况,更重要的是劳动群体的团结与行动。这需要相类似的工作环境、共同的生活方式、紧密的社会联系,先锋队才有可能把工人动员起来,爆发巨大的能量,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
而今天,无论劳动者收入水平的高低上下,大家一样水米无干,各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可能有相似的贫困,却没有共同的目标。斯坦丁呼唤precariat从“自在”(in itself)阶段发展至“自为”(for itself)的阶段,即启蒙“不稳定的无产者”,产生鲜明的无产阶级意识,打造团结一心的阶级,与全球数字资本主义斗争。这种想法有点确时代错位,罔顾现实已沧海桑田,似19世纪的幽灵从坟墓里游荡到21世纪,诈尸还魂在数字网络的虚拟世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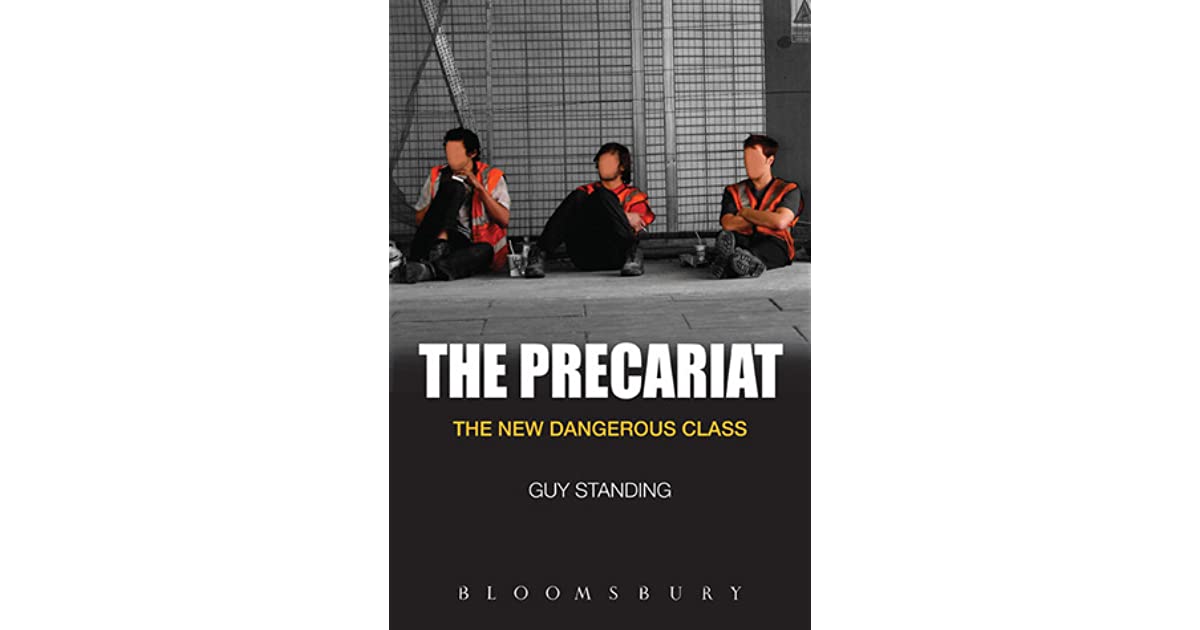
盖伊·斯坦丁 著
在中国语境中,“斜杠”确乎与precariat有相似的困境,却难照搬这一概念。目之所及,一些“斜杠”出身名牌大学,甚至怀揣美国常青藤名校学历,还有的在全球知名大企业工作过,甚至端着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的铁饭碗,却毅然辞职,加入自由职业队伍。显然他们不是被剥夺与被迫害者,而更似为“自由”而牺牲“稳定”的人。
或有人认为他们是家庭条件太好不知珍惜,也有人说等年龄大些他们或会后悔。本文所关心者,是随着大都市自由职业队伍的壮大,身份文化、社会观念、以及人际关系等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当下舆论总聚焦社会“刚需”,如住房、升学、房贷、就业等才是硬道理,而身份意识、大众文化之类都太虚无缥缈。实际上,刚需的背后有文化观念支撑,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陷入某种观念而不能自拔,所以才会一窝蜂地追逐雷同的热点。千军外马过独木桥,必定让人焦虑,而表达焦虑时,要么请来19世纪经典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不及物地天花乱坠一番;要么把一切问题简单归于物质匮乏,妒富愧贫。历史在前行,经典理论不是百年不变的真理,要考察新世纪与旧世纪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其中最大的变量又是什么。
02 是浅薄还是深远?无固定工作者如何改变这个世界
以自由职业者为例,他们既没有长期的雇用合同,又缺乏“三险一金”,没有固定的老板和工作场所,常以承接项目或工单提供服务,雇用关系随“分包”完成而结束。但他们收入不一定低,生活也不一定差,有些甚至可算富有。以有无长期保障来衡量其阶层高低,显然不再无效。
但“问题”的确存在。由于一切都是临时的,无固定工作者的忠诚感较弱,因缺少行业依托或共同体支持,集体性的社会记忆和社会归属感往往比较淡漠。于是,他们更可能个人主义膨胀,漠视社会责任与道德约束,行为机会主义。以20世纪的观念看待,这股力量看似社会不安定因素,却可能是互联网时代的大趋势——离心化和原子化不断加剧。
随着电脑技术的迅猛发展,因特网已成为连接全社会的结构性纽带,职业、单位、机构、组织已不能再担当社会机体的核心部件。网络时代的“e经济”最大特点便是雇用关系松散,劳资双方都倾向选择流动性的最大化。传统的长期固定雇佣关系,很难适应脑力劳动对共享与自由的要求,因此,自由的非固定工作将逐渐成为知识经济的主体而非另类。
当然,鼓吹技术浪漫主义或乐观的历史进步主义难免片面,我们必须得承认,新型的雇佣关系已经带来各种社会问题。首先,自由职业的工作环境更为孤立、务实和功利,“4A”情绪——愤怒(anger)、失范(anomie)、焦虑(anxiety)和孤独(alienation)——更加常见。其次,自由职业者看似自由,但往往工作过劳、自我消耗、生活散漫,缺乏长远目标,不热心系统性与持续性的社会图景。
与之对应的,其网上表达也缺乏耐心思考渐进性的、系统性的政治议题,受一人一地的视野局限和情绪影响,更倾向于追逐政治标签(hashtag)而非制度建设的长期理想的实现。事实上,西方21世纪前二十年的社会运动已经将这些症候袒露无遗:“占领华尔街”、“黑命攸关”(#BlackLiveMatter)等等起初似火山爆发,很快便强弩之末,始乱终弃,草草收场——运动与其说推动制度变革,不如说追求曝光率。

以20世纪社会革命的标准来看,如此运动不免显得苍白无力,意义寥寥,但这个社交媒体渗透生活方方面面的时代已与往昔大有不同。由街头抗议而形成的网上热搜,可能比立法或改制更为影响深远。一旦人们的观念被运动的文化冲击力所影响,行为和社会关系随之改变。大众社会的文化共识,在互联网连接的社会里,可能比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变革更为有效。
03 自由职业已非另类,知识界不该抱残守缺
一些操心的父母弄不清子代的职业,担心其未来的生计,或是因为他们年龄大了,跟不上时代步伐。但知识界依然抱残守缺,在社会分析时仍视自由职业者为另类,打入另册或忽略不计,慵懒于思想的舒服区,坚持以经典政治经济学考察正式职业,要么阶级分析,要么解码意识形态,根本无从解释21世纪的社会现状。对于知识界来说,是否有责任和有必要意识到,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与阶级意识等概念已经与时代渐行渐远了呢?
身份的不确定,与网络技术的特征如去中心、去等级化、生产者与用户角色互换等,同出一辙,“斜杠”乃技术革命的副产品。在虚拟网络世界里,大脑直接回应舆情的感官刺激,而孤独沉思或冥想便成了稀缺之物;个体经验与个性知识,都抵不过网民意见的狂轰滥炸。职业既不能定义人格,财产也不能决定立场。网民更多以趣味分群,才有了小粉红、追星族、追剧族、豆瓣成员、“后浪”一族、动漫一族、耽美一族等等。人们从趣味、美食、甚至时尚获得多样身份,职业、阶级和门第等硬通货反而降格为亚文化。
所以,知识界不可能继续沿用上世纪的学术资源来阐释今天的身份政治,思想必须突破传统定式,创新理论,才是当下学界最紧迫的课题。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