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人们在谈论文学时,只谈论故事情节就够了吗?那么讨论文学与讨论同事朋友的八卦有何不同?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出于对文学分析的关切,写下了《文学的读法》,以开头、人物、叙事、诠释和价值几部分内容展现阅读文学的方法。
伊格尔顿承认文学有助于人们丰富体验,也看到阅读变相补偿了现实中的不足。他举例道,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有时会被推荐给工人阶级阅读,好让他们获得现实中不可得的体验,“比如策马纵犬狩猎,比如嫁给子爵为妻。”
“叙事”一节的分析相当有趣,他引用亨利·詹姆斯对现实主义小说的结尾的讽刺——众多小说仿佛在结尾处分配奖品:丈夫、太太、婴儿、百万资产、欢乐的话语——讲述这类小说的结局在于安抚读者,是对于严酷现实的纠正,属于一种“诗性的正义”。在现实中,这样的理想结局往往是少见的,莎士比亚一些喜剧的结局已经存在类似的反讽,《仲夏夜之梦》谈到性吸引力时,对什么是“般配”提出了质疑;夏洛蒂·勃朗特的《维莱特》为读者准备了两个不同的结局,一个是喜剧的,另一个是悲剧的,似乎在告诉读者,如果你想要一个完满的结局,这里给你,但别以为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而比起单单满足现实中无法满足的愿望,这样的结局也满足了我们对终结的渴望。伊格尔顿解释道,令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的,正是这种对终结的渴望,也是这种渴望让读者不断呼喊出“最后会怎样”,无论是阅读惊悚、推理还是哥特恐怖故事,都是出于这种冲动,而这也是后来弗洛伊德所命名的“死亡冲动”。
至于人物,从司汤达、巴尔扎克到托尔斯泰的伟大成就,就是刻画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笔下的人物往往陷于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网中不得脱身,是远强于自身的社会历史力量产物,然而他们并没有这些力量玩弄于股掌之间,从来没有坐以待毙安于命运。这样的小说模式与之后的现代主义小说有所不同,现代主义小说的人物往往呈现出单一而孤立的意识,人物的身份也常常陷入危机当中,乔伊斯《尤利西斯》的主角在都柏林街头漫无目的地游荡;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中,人的意识会渗入周遭环境、渗入他人意识,人物的面貌往往面目难辨,一个人的情感如振动波般从一人传递到另一人。
他还将哈利·波特的形象与狄更斯的小说人物进行对比指出,同为孤儿,《远大前程》的匹普、《雾都孤儿》的奥利弗和哈利·波特在出生、境遇和前途方面有着相似之处,并对《哈利·波特》这部当代流行文学作品作出诠释:主角的姓名长度彰显着他们的家庭背景,魔法师精英对麻瓜同类的敌意里有着政治隐喻。《哈利·波特》系列值得这样解读吗?伊格尔顿写道,这涉及到文学的价值问题,不入流的作品也能让我们收获快乐,就像大家都在机场书店读那些情节紧凑的小说,文学教授也许也会在被子里打着手电读冒险故事,但话说回来,喜欢吃什么可能是口味问题,但具体到文学作品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比如比较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约翰·格雷沙姆,真正懂行的人肯定能分出好坏。

《文学的读法》日前由后浪推出新版(上一版为河南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文学阅读指南》),现从中摘录部分关于狄更斯与哈利·波特对比的章节,与读者共读。

[英]特里·伊格尔顿 吴文权译
后浪 /海峡文艺出版社2021年
英国文学最钟爱的孤儿
匹普与奥利弗均是父母双亡。因此,他们属于从汤姆·琼斯到哈利·波特的卓越谱系,涵盖了孤儿、准孤儿、受监护人、弃儿、私生子、可怜的继子以及疑似给人调了包的孩子。这类人物在英国文学中屡见不鲜。失恃失怙者大受作家青睐,有着几个原因。
其一,他们不名一文,常常遭人轻贱,全靠自己在这世上打拼,这便能激起读者的同情与赞赏。我们理解他们的孤寂与焦虑,同时钦佩他们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孤儿往往感到脆弱且遭遇不公,而这种感觉恰能用来象征性地评价整个社会。狄更斯的晚期作品让人觉得,社会制度放弃对公民的责任,令所有人都成为孤儿。社会就是个假父亲,从不履行父亲的义务,反而让所有男女替他承担责任。
再者,小说,尤其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对艰苦奋斗靠一己之力摆脱穷困发家致富的人很是着迷。这简直就是美国梦的预演。无父无母的确令他们前行的道路更为平坦。盖因少了家世的拖累,他们就不至为亲情所牵绊,可以放手一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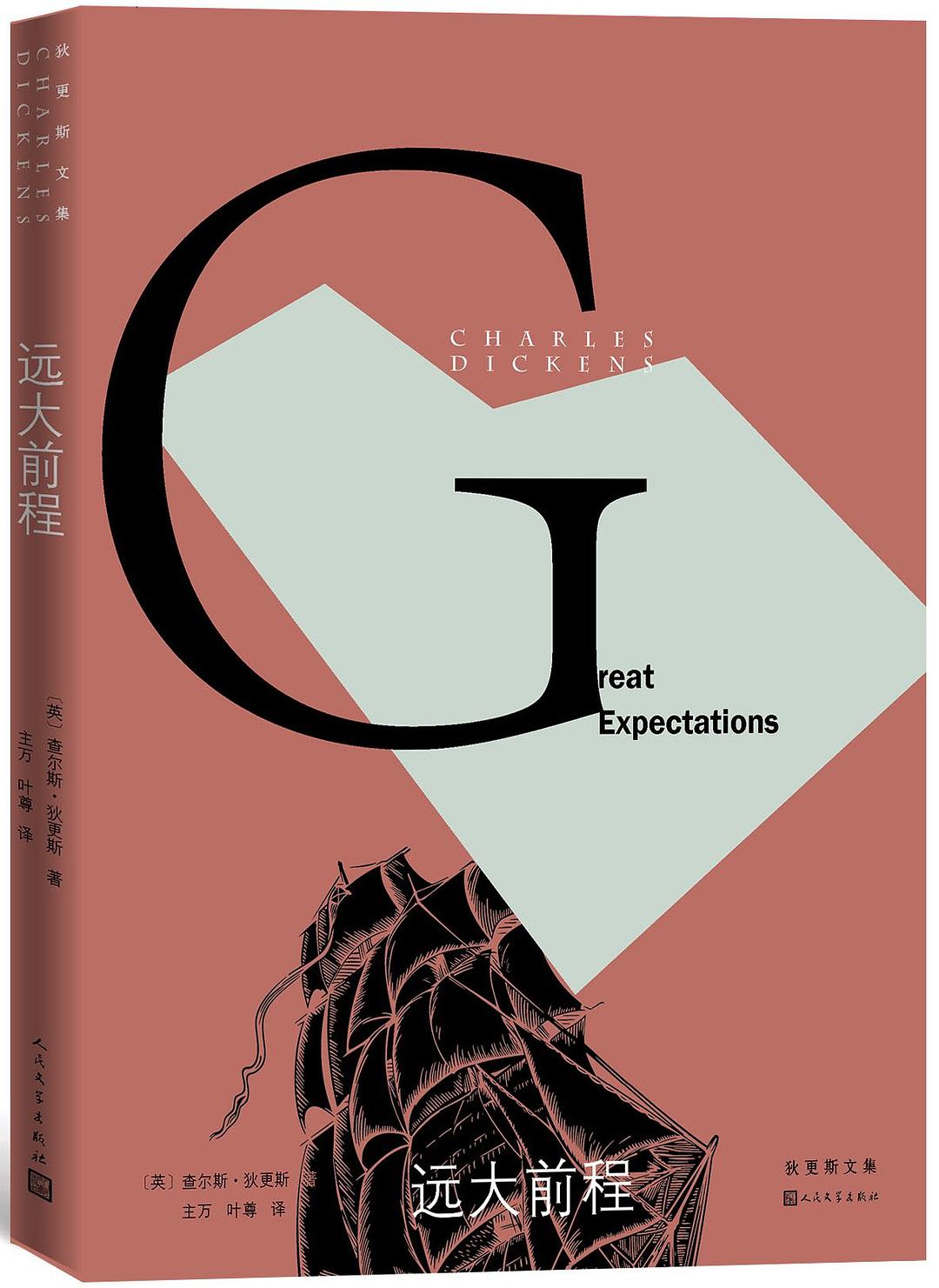
[英] 狄更斯 著 主万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
孤儿是反常的人物,与收留他们的家庭若即若离。他们与环境有些格格不入。孤儿是零余之人,不得其所,是家庭这副扑克里的小丑。正是这种断离状态驱动着故事的发展,所以说,孤儿是可堪一用的叙事手段。如果我们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准知道到了小说的尾声,他们就会否极泰来,但也会好奇,这样的结局何以得来,一路上人物们又会经历怎样有趣的冒险。所以,读者既感到笃定,又觉得没底,这种矛盾心态最是撩人。恐怖影片虽然阴森可怖,令观者心神不宁,但因为知道是假的,也就不至于胆战心惊。
当下,英国文学最钟爱的孤儿非哈利·波特莫属。哈利早年寄人篱下,跟可憎的德斯利一家生活,这与小男孩儿匹普以及寄居里德家的小姑娘简·爱的经历差相仿佛。然而,在哈利身上,弗洛伊德所谓“家世妄想综合征”居然并非妄想。他的家世可比德斯利一家要显赫得多。事实上,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首次踏入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时,他发现自己早已是闻名遐迩。哈利出身巫师名门,不仅比德斯利一家高贵(那是自然!),且足以睥睨所有麻瓜(非魔法师的凡人)。他的父母皆为法术高超的巫师,且声名显赫,备受爱戴。与《远大前程》相反,这个幻想毕竟是货真价实的。和匹普不同,哈利无需变成特别的人。他本身就是个特别的人。实际上,哈利身上无疑有着弥赛亚(救世主)的影子,即便是一心向上爬的匹普也不敢有此非分之想。就像贾格斯找到匹普,告知他即将一步登天的喜讯,头发蓬乱的巨人海格也从天而降,向哈利透露了他的真实家世与身份,引他走向已经规划好的非凡未来。由于哈利生性谦逊,并无野心,所以比倨傲自得的匹普更惹人喜爱。他的好运是盛在盘子里呈上的,没有花他半点气力。
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之间
哈利摊上个糟糕的替代父亲,即粗野蛮横的德斯利先生,所幸他遇到一众慈爱的替代父亲,从邓布利多、海格到小天狼星布莱克,足以弥补前者造成的不幸。德斯利家是他现实中的家,可那根本算不得家;霍格沃茨是个梦幻的家,却是他真正的归属。邓布利多告诉他,有的事情虽然发生在头脑中,但并不一定就是假象。幻想与日常现实在作品中汇流,令它盘桓在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之间。
在这部小说描绘的现实世界中,匪夷所思的事情明目张胆地发生着。读者必须在这个系列小说中发现自己熟知的现实,方能在魔法将之幻化时获得快感。读者大多是没有地位或权威的孩子,因此,目睹别的孩子拥有巨大的法力,无疑会让他们大呼过瘾。由此看来,即便几乎每页上熟稔的现实,都与奇异的魔幻并置,带来不和谐的感觉,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的结合,对这部小说依旧至关重要。人物施展法术时,穿着蓝色牛仔裤。笤帚落地,会激起泥土与卵石。食死徒与穆丽尔姨妈并肩而立。不真实的生物进出真实的大门。有一次,哈利用魔棒清洁烤炉时弄脏了手帕。擦炉子为何不直接用魔棒呢?
魔法若能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故事便没有存在的必要。我们已经看到,故事想要立起来,其人物必定要遭遇不幸,获得启示,或者时来运转。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中,这些际遇不可能源自魔法与现实的激烈冲突,因为魔法会赢得不费吹灰之力,哪里还会有惊险的故事可讲。所以,它们必须来自魔法世界内部的分裂,来自正邪两派巫师的斗争。魔法力堪称双刃剑,可行善,亦可作恶。唯有如此,故事情节才能顺利展开。但这也意味着,善与恶也许同宗同源,并非表面上那般势不两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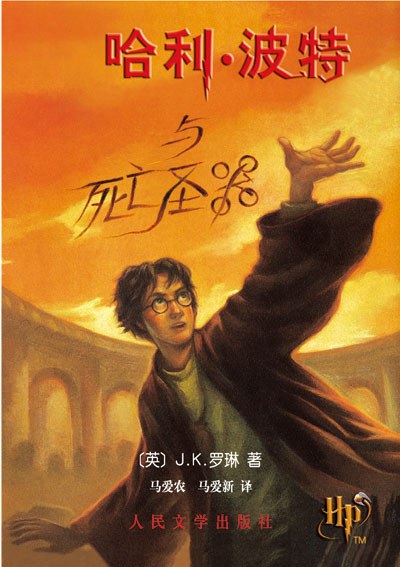
[英] J. K. 罗琳 著 马爱农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年
《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中“圣器”(Hallows)的本意是“圣化或神化”,因此,看到它与“死亡”(deathly)紧紧绑在一起,我们心中便涌起了不安。它让人想到,“神圣”(sacred)原本既有“被保佑”,也有“受诅咒”的意思。我们还看到,这一系列小说既让幻想与现实对峙,又呈现了二者的交融。同样,它们坚信,光明力量与黑暗势力不共戴天,无私的哈利与恶毒的伏地魔总要拼个你死我活;然而与此同时,却时时刻刻质疑这种对立,总也不肯罢休。
从很多方面看,这一点都清晰可见。一则,邓布利多这类慈父也会渐渐显出恶意。就像《远大前程》中的马格韦契,邓布利多亦暗中布局,以期拯救哈利;不过,读者时不时会对他的本意打个问号,正如马格韦契对匹普的规划也曾引起疑虑。最终我们看到,他站在天使一边,但行止亦有亏缺,这使得善恶间看似清晰的界限变得模糊。西佛勒斯·斯内普的所作所为亦是这般含混难辨。此外,伏地魔不仅仅是哈利的仇敌,也是其精神之父与邪恶自我。二者的鏖战颇似《星球大战》中天行者卢克与达斯·维德的争斗,乃至两个恶棍名字的首字母都一模一样。
诚然,与达斯·维德与卢克不同,伏地魔和哈利不是亲父子。然而,哈利体内长着伏地魔的关键部分,就像所有人都带有父母的基因。竭力摧毁黑暗魔王的同时,哈利也在与自己拼斗。真正的敌人总是来自内心。哈利虽然憎恨这个暴君,却也无奈地与他维持着亲密关系。“真恨他能进入我的内心,”哈利愤愤不平地说,“不过我会利用好这点。”哈利与伏地魔在某种意义上实乃同一人。只不过,哈利能抓住进入这个恶棍内心的机会,一举将其击败。
哈利的亲生父母给予他生命与慈爱,而作为父亲形象的伏地魔却异常残忍、极端跋扈。他代表的父亲是令人生畏的法律或超我;在弗洛伊德看来,这是一种内在于自我的力量,而非外在的权威。弗洛伊德认为,父亲形象的黑暗面与伤害、阉割的威胁有关。若说哈利额头上的伤疤通过某种心灵感应将他与伏地魔联系起来,也便可以说,我们这些人都带着具有类似关联的心理伤疤。伏地魔切望独占哈利,因此,哈利便成为光明与黑暗力量角逐的战场。事实上,这部小说与悲剧仅一步之遥。就像许多寻求救赎的角色,哈利必须以自己的死换取他者的生。唯有一死,方能彻底消灭伏地魔。不过儿童故事有着大团圆的传统,以免心灵创伤让小孩子睡觉时瑟瑟发抖,所以小说祭起了各式法宝,使哈利免遭死亡的厄运。全书的结束语“一切都很好”道出了所有喜剧末尾的潜台词。
魔法师对麻瓜的敌意
在这些故事里,文学批评者还能发现什么吗?首先,这里面有政治维度。一群法西斯精英般的魔法师对拥有麻瓜血统的同类充满敌意,与开明的巫师们展开了斗争。这便提出了某些重要问题。如何能做到既不感觉高人一等,又能变得“与众不同”?少数派与精英分子有何差别?有可能像巫师对麻瓜那样,既区别于大众,又与之保持某种团结吗?这里有一个隐而未发的问题,涉及孩子与成人的关系;书中魔法师/麻瓜的关系正是对此的影射。
孩子代表着某种谜题,他们与成人类似,但绝不相同。他们就像霍格沃茨的居民,虽然与成人世界有交集,但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要对他们进行公正的评价,则需承认他们与成人的差别,但也必须把握尺度,不能将他们视作邪恶的“他者”。维多利亚时代某些福音派教徒就犯了此类错误,认为自己的子女桀骜不驯、难获重生。一些现代恐怖影片中也存在同样的观念。孩子的“他性”让人联想到异类与邪灵,《外星人ET》与《驱魔人》就是很好的例证。传统中罪孽深重的孩子,如今变得鬼气森森。弗洛伊德认为,既陌生又熟悉的事物是“离奇”的。然而,若稍不留神孩子们就会喷出五颜六色的呕吐物这一看法是错误的,那么同样错误的,是像童年之独立地位获得承认之前那样,将孩子视作小大人。(英国文学书写童年始自布莱克与华兹华斯。)同样,应当承认少数族裔的特殊性,但也不能痴迷于其“他性”,反而置大量的共性于不顾。 这个系列小说值得关注的还有主要人物姓名里的音节数。

在英格兰,上层阶级的姓名往往要长于劳动阶级的名字。丰富的音节象征着另一类富足。叫作菲奥娜·福蒂斯丘 - 阿巴思诺特 - 斯迈思的人不可能出身于利物浦的穷街陋巷,而叫乔·多伊尔的却很有可能。赫敏·格兰杰(Hermione Granger)的名字是三个主角中最讲究的;“赫敏”在英国上中产圈子里比较常见,“格兰杰”让人想到乡间大宅 。这个名字包含不少于六个音节。(一些美国人将“Hermione”读错,只读了三个音节。)哈利·波特(Harry Potter)是典型的中产阶级主角,他的名字包含四个音节,平衡且齐整,不夸张也不小气。罗恩·韦斯莱(Ron Weasley)的名字就显得寒酸了,只有三个音节。他的姓氏让人想到“黄鼠狼”(weasel),这个词的引申义为鬼祟的骗子手。黄鼠狼不是什么威武的野兽,所以正好拿来给罗恩这样出身低微的人物取名。
我们大概也注意到,大量如Voldemort(伏地魔)般以V开头的词汇都具有负面意义:villain(恶棍),vice(邪恶),vulture(秃鹫/趁火打劫者),vandal(肆意破坏公物者),venomous(有毒的)……V字手势具有侮辱性,象征着阉割。伏地魔(Voldemort)在法语中意为“逃离死亡”,但也许别有意指,因为 vole(田鼠)也不是什么像样的野兽。这个名字或许也在暗示“墓穴”(vault)与“霉菌” (mould)。
有的批评家认为,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不值得探讨。在他们眼中,这些书哪算真正的文学。什么是好的文学,什么是坏的文学,让我们接下来看。
书摘部分节选自《文学的读法》一书,经后浪授权发布,部分内容有删节,按语写作:董子琪,标题为自拟。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