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发展中国家的作家如果入籍西方国家,常常被贴上标签,其作品如果不是反映原籍国家、民族的风俗样貌,而是描写西方世界,就会被指摘为与西方霸权话语共谋,失去独立性,乃至同流合污。本文通过对英籍印裔作家维克拉姆·塞思的小说《琴侣》的分析,提醒读者及批评家注意力应该放在作品本身上,充分读解作者呈现出的情思与感怀。
《不是错乱,而是错读》
文 | 张磊(《读书》2022年2期新刊)
在《英国跨文化小说中的身份错乱》一书中,作者们对奈保尔、拉什迪、毛翔青这三位英国著名亚裔小说家的社会政治立场倾向提出了质疑与批评,并鲜明地指出:他们的不少作品都在极大程度上与西方霸权话语保持一致,二者形成了一种共生共谋,甚至可以说是同流合污的关系。换句话说,他们并未把自己有意识地打造成真正有进步思想的后殖民作家,而是从心理上把自己白人化,极力迎合所在社会的白人受众,因此出现了严重的身份错乱/位。
无独有偶,类似的质疑亦曾经指向另一位亚裔作家——维克拉姆·塞思,尤其是他那部被《每日电讯报》誉为史上用英语创作的最佳音乐小说、写尽当代古典音乐职业演奏家公共与私人生活百味的《琴侣》。譬如,印度作家、记者阿米塔瓦·库马尔虽然表面上声称自己无意做任何价值判断,却又情不自禁地强调这部小说全部的人物形象都是白人,没有一点咖喱味。表面上,他似乎理解曾经在中国、美国、印度、英国、德国四处行走的塞思自我塑造的世界公民身份,但又不时提醒读者所谓本真身份的问题。其实他在《民族报》上发表的书评,标题《没有西塔琴的印度音乐》就已经表露了他真实的立场和态度,即使全书没有一处提到印度音乐,他仍然要将“印度”二字与其联系在一起,哪怕是以不在场的方式在场。

与库马尔温和的颇有微词相比,布鲁斯·金对这部小说则做出了毫不遮掩的批评。在他看来,它完全脱离了目标,不符合现在的读者对后殖民作品样貌的期待。罗希尼·摩卡西-普尼卡更进一步,干脆认定这部以西方古典音乐、古典音乐职业演奏家为主题的作品是在彻头彻尾地鼓吹欧洲中心论,作家近乎没有道德地、完全地抹除了自己的印度人身份。安贾娜·沙玛的评论文章甚至直接用了质问式的标题——《这难道是部英国人写的小说吗?》。
不论是温和的质疑,还是严厉的批评,这些批评家们近乎不约而同地创造了某种具有强制性的假设——如果具有少数族裔(如印度裔)身份的作家不极力将某种族裔性(印度性)与自己的作品明确无误地联系在一起,就无法有效地证明其创作的合理性,就有可能会出现“身份错乱”。
事实上,塞思曾是被竞相追捧的文坛新秀,在前作《如意郎君》中,他曾经以一千三百多页的篇幅洋洋洒洒地展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印度社会的全景。贯穿于其中的拉格与加扎勒音乐,也为小说塑造了极好的、充满着异域风情的东方音景。这部当代少有的鸿篇巨制不仅确立了塞思的地位,也赢得了批评界与读者的一致好评。塞思如果按照这一范式继续创作下去,就不会引发如此大的争议,也一定会继续创造作家、批评家、普通读者皆大欢喜的局面。他为何要打破这一范式呢?
在笔者看来,除去创作自由、不愿意亦不允许自我重复,塞思打破这一范式的最大动力在于:继从外部(印度、非西方),亦是典型的后殖民视角展现别种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差异式抵抗之后,他希望从西方文化的内部对其进行改造与重构。而作为其代表与坐标的西方古典音乐,便成为他这一创造性尝试的重要对象。换句话说,塞思非但不是倒退到与欧洲主流、中心文化合谋的保守立场,而是更加决绝、激进地更进一步。如果批评家或一般读者只是从背景与场域、角色构成、题材这些方面去做表层解读的话,无疑是没有读懂或读透那些隐藏在文本字里行间的重要讯息,形成了误读、错读,亦是辜负了塞思的深刻用心。

一
塞思所做的第一重改造,是试图去除西方古典音乐(尤其是古典主义时期与浪漫主义时期的古典音乐)长期以来被贴上的某些固定标签。众所周知,古典音乐常常被认为代表着中产阶级与贵族阶级的社会地位与审美品位,那些在经济、政治上处于下等阶层的群体往往被认为不适合,也不能真正欣赏这种“高雅”的艺术形式,更无法负担长期专业的音乐训练。就欧洲而言,古典音乐学习、演奏的重镇当然是伦敦、维也纳、威尼斯等大城市。从一开始,《琴侣》的男主人公迈克尔便饱受这一标签的困扰,一度形成了强烈的自卑情结。他出生于曼彻斯特郡罗奇代尔市,远离英国的文化中心伦敦。他也没有专业音乐教育的家庭背景,父母非但不鼓励,甚至还常常打击他的音乐热情,连他用来演奏的小提琴都是从一位贵妇那里近乎卑微地借来的。可以说,男主人公既不占天时、地利,亦不占人和。然而,正如《霍华德庄园》中同样出身卑微【】却有极好乐感、从生到死始终保持尊严的伦纳德·巴斯特一样,迈克尔也始终坚信“唯有联结”的道理。小说题词部分引用的约翰·但恩诗歌,几乎是他呼之欲出的心声——“既非噪声,亦非无声”的“平等之音”与“平等交融、平等身份”遥相呼应。
正因如此,迈克尔养成了一种特殊的能力——善于发现那些鲜为人知,却有着很高艺术表现力的音乐作品。他在小说第一章里下意识哼唱的小曲(后来也反复出现多次),便是舒伯特晚期创作的一首不甚有名的艺术歌曲:“我看见一个人眼睛向上凝视,双手痛苦地紧握。我看见他的脸时为之战栗。月光暴露了我自己。”舒伯特作品中的忧郁、痛苦、恐惧、焦虑,似乎让他产生了强烈共鸣,成为他内心复杂情绪外化的重要方式。而通过哼唱这样的作品,迈克尔无疑在为这些常常被视作阴暗、负能量的声音正名,为自己在包括伦敦在内的各种不适之地的格格不入找到了理由。

除了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小说中用最大篇幅描述的贝多芬C小调弦乐五重奏(作品第104号)更是成为迈克尔追求音乐平等的重要动因。自从学生维尔日妮跟他提及这部神秘的作品之后,他便在伦敦的各公共音乐图书馆与音像店里近乎疯狂地寻找它。遍寻未果之后,他竟然“意外”地在自己家乡曼彻斯特的亨利·沃森音乐图书馆找到了这部作品的一套分谱,是这家图书馆许久之前便收藏的珍品。并且,它还有一九一六年八月十日由奥伊伦堡公司生产的微型乐谱。曾被认为是古典音乐“当然”中心的大城市伦敦,此时竟敌不过曼彻斯特一家小小的图书馆,不论眼光、品位,抑或是远见,都输得彻彻底底,颇具反讽意味。所谓的中心论、先进论、高贵论、高级论、优越论在这里被强烈地动摇、打破。
随后,在更为艰难地寻找这部作品极为有限的唱片录音时,迈克尔对音乐平等坚定的信仰再次得到了强化与确认。在一个贝多芬过度录音的时代,这首小众的作品几乎无人问津。伦敦、维也纳、威尼斯等地的著名重奏乐团竟然没有一个曾经录制过这部作品。而真正有心、用心录制这部作品的,竟然是捷克的苏克四重奏团(外加一个中提琴手),并且早在一九七七年便由捷克本土的超级响度公司发行。这个重奏团的理想,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努力推出一些不太流行、没有理由被人们忽略而事实上又已经被忽略的作品。这几乎与迈克尔的理念如出一辙,也就不难理解他心情无比激动,打算一定要带着满满的仪式感聆听这张唱片。不仅如此,迈克尔还发现,这一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演奏家约瑟夫·苏克是作曲家苏克的曾孙,而作曲家苏克本人跟他一样,也是下层民众之子,这让他更是百感交集。

当迈克尔在自己的房间里播放这张唱片时,立即感受到贝多芬这部作品的巨大魅力——它是“如此地熟悉,如此地令人爱不释手,如此地别出心裁,既令人不安,又令人陶醉”。他迅速沉浸在这个他“无所不知却又一无所知的世界里”。这里看似矛盾而又复杂的情感表达,确实耐人寻味。一方面,他在这音乐中找到的是一种久违的熟悉感、归属感,似乎这音乐里说的就是他自己那虽然充满酸楚,却仍然值得纪念与珍惜的过去。另一方面,他听到的也是他正在努力形塑的现在。他知道这现在的种种不确定,亦知道他的过去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他的现在。然而,这种不安、一无所知,让他感受到的并不仅仅是消极意义上的痛苦与不适,还带来了强烈快感的陶醉与沉浸。与其说这是艺术家疯癫与精神分裂的表征,不如说是他在音乐这种充满着强烈滑动性的能指中发现了超越固化意义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不“安”本身便是对既有认知模式的一种打破,而一无所知才能刷新与重启认知。这首作品从沉寂到被发现、从乐谱到唱片录音、从播放到倾听的过程,几乎是迈克尔古典音乐去阶层化、去等级化的平等化实践的完整再现。
二
塞思所做的第二重改造,亦是终极改造,便是打破古典音乐界对听觉能力的强制性规约。对于音乐家来说,听觉能力,即对接收到的声音进行综合分析、理解、记忆,是一项必备,也是要求极高的能力。那些不论是天生还是后天的失聪者,常常被认为在这项能力上具有不争的缺失性,近乎当然地被排除在音乐演奏或创作的世界之外。即使失聪者真的有机会进入这一领域,他们也往往面临被边缘化,被嫌弃、看轻的境遇,会被认为不够正常、低人一等,没有资格去和其他音乐家合作,完全是“拖后腿”的角色。

在小说中,迈克尔曾经的爱人、钢琴家茱莉娅不幸失聪。她曾经在一封长信里向迈克尔详细交代自己逐渐失聪、被抛进聋哑世界的过程,她叙述的语气并不算沉重,但仍然难以掩盖她内心的忧伤。双耳不能再听到曾是自己生命之源的音乐,自己的演奏生涯也可能戛然而止,对音乐家来说,这是毁灭性的打击。更悲凉的是,音乐圈人情浇薄,一些曾经的好友对失去利用价值的她甚至吝啬到连同情的姿态也没有,让她心寒不已。
事实上,失聪与听觉能力的缺失并不当然地画上等号。不论是历史还是现今,都有不少失聪音乐家在以自己的方式强力地扭转这一偏见,并向世人证明:与常规的听觉方式相比,通过仔细感受声音的振动,同样可以完美地“聆听”,肉耳的听觉变弱或消失之际,便是心耳的听觉开始之时。譬如,贝多芬晚年的那些最伟大的作品,大都是他失聪后所创作的。而他感受音乐的方式被称为“骨传导”——一种让外部声音的振动直接由头骨、颌骨传入内耳刺激听觉神经,从而产生听觉的声音传播方式。同样,自十二岁起便失去听觉的英国女性打击乐演奏家依芙琳·葛兰妮,在演奏中依靠内心的节拍与周围物体的振动,成功地创造出极具震撼力的音响语言,重新定义了打击乐的演奏形式。
与贝多芬、葛兰妮颇为相似,从一开始,茱莉娅即使内心再痛苦,也没有放弃自己或音乐,体现了强大的意志力。她积极地参加预防话语疗法课程,数小时地练习唇语与手势语。她也颇为配合地戴上了助听器,以帮助她听到大概。她还经常做各种各样的听力测试,譬如在左耳边清脆地拍两下,又在右耳边连拍两下。除此之外,在演奏室内乐时,她懂得了如何从灵动的手指、姿势的变动、弓的回旋来判断何时演奏,以何种节拍跟进。尤其是那些有重低音声部的室内乐(譬如她与迈克尔所在的马焦雷团合作的舒伯特的《鳟鱼》),更是让她可以充分依靠传来的振动感来准确判断自己回应的方式与时间。对乐谱全力做到烂熟于心,不断唤起自己之前曾经演奏同样作品的记忆,也成为她大量精力投入之所在。

不过,除了种种超常的努力,茱莉娅这个人物令人叹服,也是最特别之处,在于她同迈克尔提到的一个全新的音乐观点——“作为一名失聪的音乐家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乍听起来,这多少有些故弄玄虚,甚至有些自欺欺人。然而,当读者与茱莉娅一起严肃地思考这句话时,便可逐渐体会其背后的深意。这个优势当然不是她半开玩笑说的那些所谓的好处——住酒店时,可以欣赏窗外的霓虹灯街景,却不必担忧街上嘈杂的噪声会影响睡眠;弹琴时不会被观众席上此起彼伏的咳嗽声惊醒;没有手机铃声,没有观众看完节目单后,折眼镜的噼啪声……卖了一大堆关子、绕了一大圈之后,茱莉娅终于将这个优势和盘托出——可以“尽力使自己有点创意”。当演奏家有常规的听觉能力时,往往会特别依赖既有的录音,去听听别人,尤其是所谓的权威如何演奏作品。在实际演奏时,演奏家们也往往会尽量避免各种风险与争议,而选择中规中矩,亦是安全的演奏方式。这无疑与真正的创造性相背离。吊诡的是,当茱莉娅失去常规的听觉时,反而能够自然地摆脱种种规约、权威的束缚,按照自己的意志与理解去演奏作品。譬如,在乐团排练《鳟鱼》最后一个乐章的第一主题时,迈克尔和海顿分别演奏了一个两小节的乐句。然而,让他们颇为惊讶的是,茱莉娅回应起来就像这是一个四小节的乐句并持续减弱一般。她并不是听错了音符,而是提供了一种更加符合乐句发展的解读方式。在短暂的争议后,乐团成员一致认为,茱莉娅的这种方式是更值得采用的,因为这样一来,到那些重音及后面的切分音时,对比的效果会更好。这时候,迈克尔甚至可以略带欣慰地看待自己旧爱的失聪——如果她能够清楚听到其他人的演奏,倒可能没有这么好的创意了。
不论是对古典音乐的去标签化,还是从肉耳听觉到心耳听觉的转向,塞思确实在小说中完成了从西方文化内部对其进行改造与重构的重要尝试。当其他少数族裔作家纷纷选择以典型的后殖民文化抵抗姿态来书写自己的身份时,他却无惧可能的误解与争议,勇敢地选择了一种非典型,亦是创造性的方式。作为一个有良知与责任感的作家,他从来都没有什么身份错乱。他始终都知道自己是谁,自己要做什么。对他所谓错乱的错读,不仅是对他创作用心的辜负,也更深刻地证明了简单粗暴、妄断式思维的危害。作家复杂而又微妙的立意,作家在言辞表达中努力传达的微妙情绪、情感、关系,值得批评家与读者以更为微妙的阅读和解读方式加以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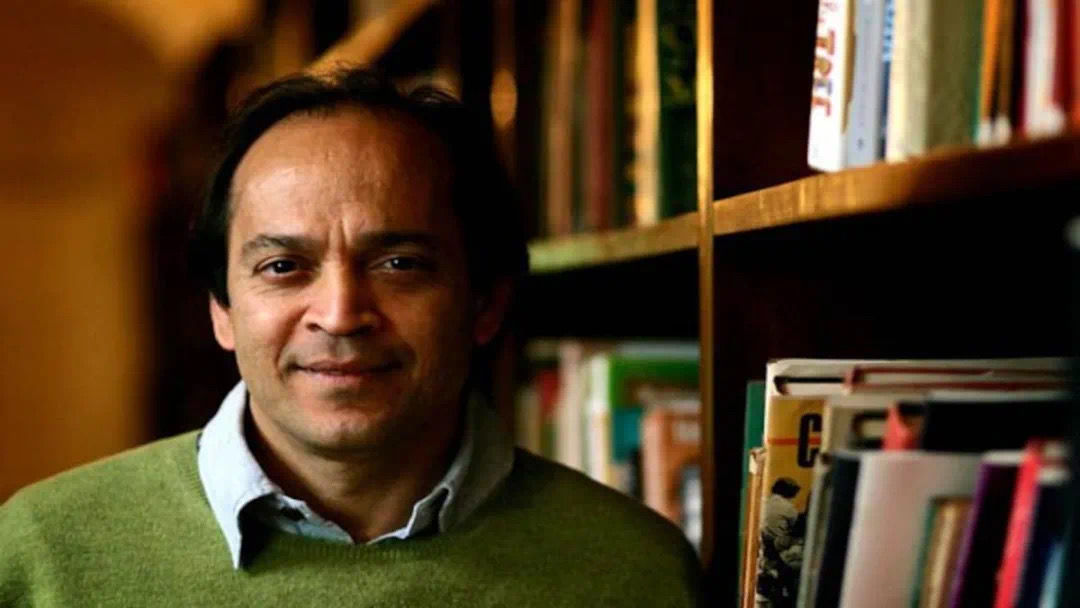
来源:读书杂志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