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总是乐于模糊虚构与非虚构题材之间的界线,所写的小说读起来更像是历史学著作或文学批评。他的新书《伊丽莎白·芬奇》(Elizabeth Finch)已经艰深难解到了对读者极不友好的地步,书的体量并不算大,却还是在一篇短论上花费了50页,讨论了有关罗马皇帝叛教者尤里安(Julian the Apostate)的一系列历史学观点。这位皇帝企图摒弃基督教,在罗马恢复异教崇拜,但未获成功。
短论的作者就是这本书的叙事者尼尔,他是一位离过两次婚的肥皂剧演员,后来又改行搞蘑菇养殖,写书的目的是为了纪念伊丽莎白·芬奇(Elizabeth Finch),此前他在伦敦上了一年的夜校,期间曾修读过这位讲师的“文化与文明”课程。他从来没交过期末论文,只是请伊丽莎白——她心高气傲并且爱摆架子,令学生议论纷纷——出去吃午饭。一场为期二十年的例行公事就此开始,尼尔每年都会请伊丽莎白吃两次饭,直到她去世,她在临终之际把自己的论文留给了我们的叙事者,其中包括一篇有关尤里安的文章的笔记。
随着尼尔开始着手完成论文,一条提到《金色传奇》(The Golden Legend,作者为十三世纪末意大利热那亚大主教、多明我会修道士雅各布斯·德·沃拉吉尼,为中世纪奇迹与殉道者故事的集大成之作——译注)的早期注释或会引起尚无准备的读者的注意。同样值得留意的还有伊丽莎白的兄弟所说的话,“红光满面且略有发福”的他对尼尔表示,自己“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文艺男青年。虽然我也喜欢写得好的猎奇志怪类故事”。这是书中的若干条暗示之一,透露出巴恩斯自己也没有做文艺男的想法:正如尼尔也坦白称“我心里住着的那个八卦爱好者也在好奇伊丽莎白是否留下了什么掏心掏肺的自白式日记……我这些俗气的想象和她教过的那些资质平平的学生不过半斤八两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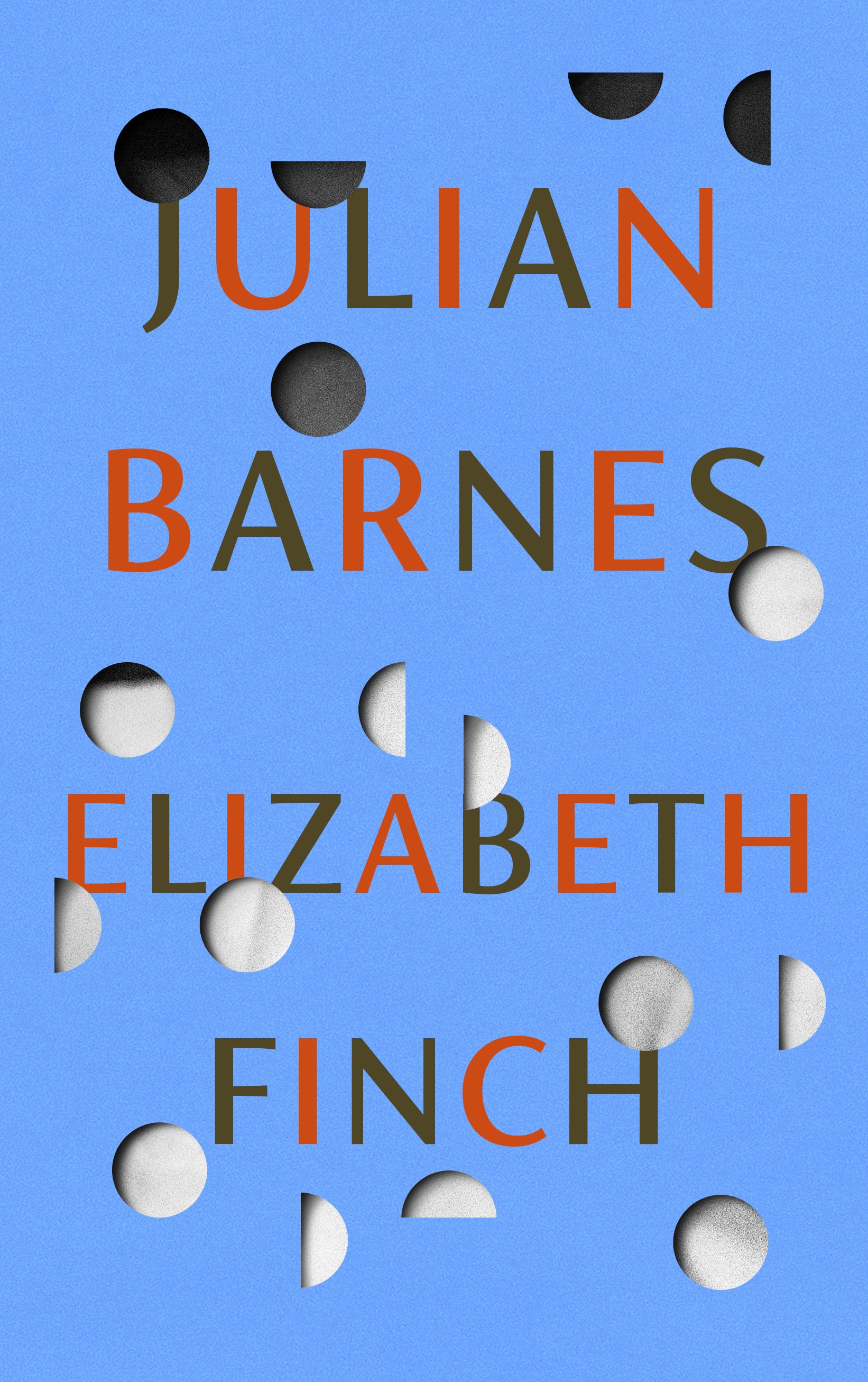
这部小说以持续不断的警示扰乱了读者对于重要性之高低的感知——有关伊丽莎白的情感生活或是尼尔的离异经历——使叙事变成了一连串的错误开端。典型的情形是,巴恩斯在句子开头使用“就我的情况而言”这一短语,只是为了让读者不要对号入座想到自己(“但我的情况与此无关”)。
这种阅读体验就好比是接了一个陌生来电却发现对方一直不说话,但这不等于书中就全无有趣之处了。在一位女同学说出“生活……并不等于叙事”这句话之后,尼尔告诉我们,他喜欢“比我更聪慧或者更清醒”的女人,而下一分钟他又在问女同学是否和别的女人一起睡过,随后还亲自上阵撩拨对方。麻烦在于,这种喜剧桥段有其附带损害,令我们无从判断尼尔是否还能成为整体主旨的可靠导引者,考虑到伊丽莎白的表现与她竭力营造的“完美的智慧传人”形象也颇有出入(“生活既是必要的又是不可避免的?”“宪政民主是我们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不坏的制度?”),前述的疑虑更是有增无减。
在某个章节里,尼尔在火车上阅读米歇尔·布托尔(Michel Butor)1957年的小说《变》,而这本小说里的叙述者也在火车上,读的正是叛教者尤里安的故事。布托尔狡猾地拒绝在叙事者与主题之间建立起读者所预期的关联,使尼尔愈发不耐烦,这恰好呼应了我们自己的挫败感。换言之,巴恩斯以清晰得不能再清晰的方式表明了他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如果你读得再仔细一点,不难发现伊丽莎白身上有那么一点巴恩斯的朋友安妮塔·布鲁克纳(Anita Brookner)的影子,后者于2016年去世,巴恩斯借伊丽莎白向她致敬这一点意味着尼尔在论及伊丽莎白时会高度严肃(“我的嘴里从来不会冒出‘安妮塔,你觉得爱尔兰在六国锦标赛里有多大机会?’这种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小说中的戏谑成分就更丰富了:尼尔对于为伊丽莎白立传这一“粗陋想法”的不屑,也许就调侃了巴恩斯的另一位朋友赫敏·李(Hermione Lee),她目前致力于研究布鲁克纳的生活,而巴恩斯经常在上面发文的《伦敦书评》编辑或许也会喜欢尼尔对该刊之风评的总结,即“左翼分子、颠覆者、伪知识分子、世界主义者、叛乱分子、骗子和倒皇派害虫的巢穴”。
最后,我(指本文作者Anthony Cummins,自由撰稿人)不禁想知道,巴恩斯是否也在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的自传体小说《内部消息》(Inside Story)那里得到了那么些不大光彩的“灵感”,因为我在读巴恩斯新书的时候,高度在意他是否在其中加入了与自己在艾米斯回忆录《经历》里的出场——艾米斯在其中回顾了90年代中期两人反目成仇的苦涩往事——相类似的桥段。新书里的叙事以尤里安为中心,同样受一名女性的神秘魅力左右,尽管魅力是智性的而非感性的。这样的谋篇布局,相当于把一部影射小说(roman à clef,法语词,直译即为“带着钥匙的小说”,需要读者加以解码——译注)的钥匙严严实实地藏到了后门的花盆底下,较少高调招摇成分。以上无疑都是纯粹的推测,但巴恩斯也足够聪明,以至于算准了读者在面对这部极其晦涩的小说时多半还是会强迫自己在里面找出乐子来的。
(翻译:林达)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