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的最新长篇小说——他到目前为止创作的第一部、可能也将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是以一场发生在农村的传统葬礼开始的:村霸宏阳因饮酒过度死于梦中。他的家人为完成他生前夙愿,为他施行土葬。谁曾想到出殡时,被当地官员撬棺,人们才发现,原来宏阳曾短暂“复活”过。这个故事来源于阿乙的一位作家朋友方慧闲谈时讲到的一则逸闻,“一个掌控小镇上一切的人物,最后被活埋了。她讲的时候我就很激动,当时马上就觉得这个人物走到眼前了。”以此为起点,阿乙逐渐勾勒出这个长篇小说的框架:以葬礼为贯穿线索,以宏阳亲人的口述和回忆为主,既刻画了一个村霸的性格,也立体呈现了一个家族的发展变化。与此同时,小说中还穿插了一个关于飞眼和勾捏杀人、逃离的中篇小说,自成体系。这个中篇带着一种漫游式的英雄主义色彩,通过阿乙的刻画,连环杀人者像是某种艺术家,专心致志地雕琢自己的犯罪作品。在阿乙看来,他写的人物没有善恶之分,他们最大的恶可能在于他们没有善恶。
阿乙的小说很多取材于犯罪故事,这和他早年的经历相关,他上过警校,当过警察,享受侦破案情洞察人性带来的快感。即便在成为一个作家后,他仍然关注社会新闻,喜欢看一个名叫《庭审记录》的节目。他不喜欢读小情小爱小伤感,认为书写20岁之前的那些初恋故事永远无法留名历史。他坦言也许是自己在情感方面“比较无能”,无法体会细微的感情,所以“非要在打打杀杀中看到人性”。
在阿乙眼中,小说创作的目的是什么?作为一位很容易被标签化为犯罪小说家的写作者,他如何应对“写作天花板”的问题,又如何避免自我重复?作为如今“70后”作家的中坚力量,他如何看待中国作家的代际划分与成长,又如何看待他所擅长的乡村和小镇题材?针对上述问题,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日前采访了阿乙。

1、当代社会是一个互讹型社会
界面文化:为什么选择以一个葬礼贯穿全书?

阿乙:这些年我频繁参加了一些葬礼,印象很深的是城乡葬礼的差异,这一点对很多人都会产生冲击。社会新闻里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很多人在土葬改成火葬的截止日期之前死掉。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每到鬼节或亲人忌日,人们在城市的红绿灯边上或十字路口烧纸,可到处都是水泥,鬼魂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以前在农村,鬼魂可以飘在树枝上,可以在天空中振翅飞翔。在城市里面人死了之后很凄凉,没什么意思。
界面文化:你在其他采访里谈到,这个小说最初的灵感来源于朋友讲过的一件异闻:在安徽某农村,有一个人喝酒过量而死,村民把他埋了。但政府不允许土葬,于是开棺掘墓,发现这个人曾经“醒”来,痛苦地求生过。为了刨棺材板,两手骨头都“越过”皮肉露了出来。但在结尾部分,其实你并没有把这层意思直接呈现给读者,这是为什么?
阿乙:整体来说,以前我喜欢追求情节,现在情节已不是最重要的部分,我甚至把情节都斩了。一开始听说这个故事,我觉得太惊人了,但是写到最后,又觉得没必要再把这个结尾写出来。整体来说我并不是试图讲一个惊悚故事,还是想写一个人,一个市场经济背景下唯利是图、没有任何信仰,既不对孔子负责,也不对耶稣负责,也不对共产主义负责的一个无君无父的农民,他只对自己的利益负责。这就是宏阳,他没有道德,也没有不道德的地方,一切的考量让人觉得高深莫测,可想通之后发现他唯一的一点就是自私自利。他自私到什么程度呢?他发现攒了这么多钱,没有可以移交的人,因为世界上没有可信任的人。所以他最后勉为其难,办了两份存折,一份给他跟班的,另一个份给他最痛恨的老婆。这实际上写得很彻底——世界上没有任何可以交托的人。
这样一个人就是这个时代中国人的写照,不知道一生活着为了什么,活着就是为了自己。我在医院碰到不少这样的人,他们的思维很奇怪,但又很合理。医生给他们打针,他们就会很本能地认为医生把他们当做试验品了。难道到医院打针还要医生给他们掏钱?我又想到前几天看的新闻,子女跑到医院里问医生,为什么要救他们的父母。一开始会觉得愤怒,但用市场经济来解释就会觉得很正常。这一代人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以前认为这是新闻,但其实这是普遍现象,这是一个互讹型社会。
2、被市场经济浸润的农民与曾经的农民截然不同
界面文化:所以在你看来,小说的目的是对于人的刻画?
阿乙:一个小说就是一个巨大的词条,用一个词条来定义这个人,一个人最后就是一个十几万字的词条。换个角度看,清朝的人或是23世纪的人,可以通过我的小说,看到这个时代的人是如何思考的。我写作就是带着这个目的。
我写完之后想过一个问题,我写的农村和“50后”、“60后”写的农村有着巨大的区别。他们写的农村其实是一个前社会主义农村时代,写的是社会主义的前农民,那时候的农民还有一些固定的标签在身上——忠厚、弱势,情感容易理解;而我写的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后农民,是市场经济浸润的农民,市场经济把他们的思维改造了,他们以利益为中心,以现实利益来考量,这一批人实际上和以前的农民截然不同,信仰和思想都改变了。

阿乙 著
译林出版社 2018年1月
界面文化:在你看来,“50后”、“60后”作家笔下的农村,这么多年来、甚至是在市场经济进入后都没有变化吗?
阿乙:“50后”和“60后”的童年是前社会主义时代的,他们是在共产主义的影响下成长的。对每个人影响最深的其实是童年和少年时代,这一阶段是写作的营养或理解世界的关键时刻和关键经验,所以他们的经验还是停留在那。余华的农民形象就是福贵,就是忍受忍耐,这是一个很悠长的中国农民的缩影,活着的目的就是活着,没有别的目的。
但是我的经验不同,我幼年和少年是在80、90年代,20世纪最后20年是我的关键经验,正赶上中国改革开放和汪洋大海般的市场经济,很多东西都在交易。
界面文化:在这个长篇中还穿插了一个中篇小说,其实单独拿出来看也是自成体系的,那为什么选择把它放在这个小说内部?
阿乙:最开始我只想写一小段,后来发现这个人物自己在膨胀,好像他自己也想说话,在里头觉得不满足,要求作者不能草率地把他写完。我对此很挣扎,挣扎了十来天,到底是写大还是写小。写大结构可能会变形,所以天天都在取舍。
那时候我去天坛公园散步,看到很多树都长着树瘤。苍茫古树如果修剪得很好、长得很笔直,就没什么意思;如果一棵树长得很古老,树身褐色,树皮干裂,长一个树瘤,在秋天傍晚看到这种景色,会觉得挺合理的。我就在想,小说也是这样,如果一个地方结构变形了,就像另外长了一个树瘤,也不会影响什么。所以它自己想撑开,就索性让它撑开。因为别的地方没有撑开的欲望,只有这个地方有。
当时我还立下一个决心,既然已经当做树瘤来写,那么前后的风格就完全要断裂开,要强调对立性和不协调性,就放弃了长句子的写法,恢复到了我过去在《下面,我该干些什么》里用过的方式,奇快无比。所以这里有两种阅读体验:一种是前面那种,非常晦涩,缓慢,比较痛苦;而到这一部分,像是坐上了冲锋舟,直线往下。这一块的阅读非常快,字体也换了,就是为了彼此割裂开,形成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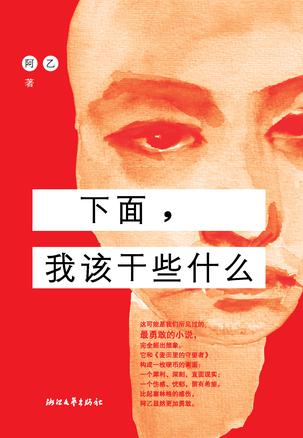
阿乙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2年2月
3、“我的作品非要通过打打杀杀才能够看到人性”
界面文化:夹在长篇中的这个中篇小说是个英雄主义的故事,是漫游式的,同时主人公飞眼也是一个杀人犯。
阿乙:实际上最后我想讲一个事情,即使是飞眼这样一个人物也有高贵的地方,这种高贵被宏阳无情地出卖了。我想写一种状态下的人——他们在这个社会上没有根、没有家、没有故乡,随机漂泊,杀人是他们存在的一种方式。这里面根本没有善恶,文学里没有太多的善恶,他们最大的恶就是没有善恶。到最后就是受一种庞大的习惯力量驱使,哪怕做一个事情的成本太高,但他们已经习惯了,也就直接做了。
界面文化:你的很多写作题材还是关于乡村、关于小镇,关于警校的经历。
阿乙:我出身比较低微,从乡村到城镇一路都经历过。我在农村出生,在城镇长大,后来在大城市生活。可能也是创作需要,我的经历反过来帮助了我的创作,好像上帝安排了这一切,让我从这些地方都走一遍。
但20岁之前生活的环境是一生很难改变的经验。26岁开始我就基本上在大城市了,但始终没有那种刻骨的体验。只有最开始的地方是印象最深的,我把它当成家乡。我从2004年到北京,至今有十几年了,完全没有发自内心的归属感,写作也不会以此为背景,我从来不觉得北京在小说里可以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场景。甚至可以说,一个地方只有在离开之后,我才会把它当做场景——我对小城是这样,郑州也是这样——只有离开了,才成为可能场景。
界面文化:你的小说很多题材来源于一些犯罪故事或者逸闻,比如这本的棺材中的“人死复生”,为何选择这个路径?
阿乙:这是自然而然的。我喜欢法庭小说和犯罪小说,看电影也是如此,我过去做警察就喜欢侦破,对任何事情都刨根问底。我不喜欢情感片,要是让我看一个给老人关怀送终的情感片,我会本能地排斥拒绝。我就喜欢看《老无所依》《逃出绝命镇》这种片子。对名著也是这样,看《荷马史诗》我就很开心,如果是《理智与情感》的话,仅仅因为这个标题我就不会读了,一看就是讲小情小爱的,我到现在都没读过。我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司汤达的《红与黑》,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罪案法庭小说。我自己的写作方向也是如此。
界面文化:阎连科在不久前的一个演讲中提到“苦咖啡文学”,认为近几十年在中国流行的西方经典文学的特点是写作的人物从社会历史转向家庭,没有宏大历史中的苦难,只有微小人群中的小伤感、小温暖、小挫伤、小确幸。你是否认同这一观点?
阿乙:他虽然说得不太讨喜,但感觉上是对的。直觉上我和他比较一致,因为我不太喜欢小情调文学,也可能是因为这方面我比较无能,细微的情感不是每个人都能体验到。所以我的作品非要通过打打杀杀才能够看到人性,但生活中那些小的细节看人性我可能看得不太够。
界面文化:你在写作取材时,一般会通过哪些渠道来获得素材?
阿乙:前些年有报纸的时候我还会系统看报纸,以前看《新京报》《京华时报》会经常看中国新闻里的罪案。后来我喜欢看《庭审现场》(注:CCTV12的一个电视节目),但还没养成习惯。现在的《庭审现场》太狗血了,我最近没有系统地看。
我以前有个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是看了《新京报》的一个报道之后才写的。那个时候报纸上的法案新闻会比较慎重,现在网上的社会新闻都是福尔马林液体泡过的新闻、奇怪的新闻、没有价值的社会新闻。我喜欢的社会新闻是带着油墨香的,是那种让人啧啧称其的同时也让中产阶级读者发出唏嘘感叹的社会新闻。
界面文化:为何对犯罪题材情有独钟?
阿乙:犯罪是一个人类精神活动的凝聚点,戏剧性最强。通过一个犯罪事件,一个人的人性是最极端化的。我在派出所工作也是这样的,派出所就像一个戏剧舞台。派出所把社会上大部分正常健康的人“淘汰”出去,来派出所的人要么是受害者,要么是凶手,天生具有情节,人性里可能还有一些不正常的东西。小说也是这样,我写犯罪,能够看到人性。莎士比亚的作品有些是弑父案,有些是国王被害,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写二十岁之前的故事的作品很少在世界名著中留下踪影,不是因为初恋不好写不宝贵,而是因为初恋体现不了多少人性。

4、作协不是主流,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场域才是主流
界面文化:我们经常能看到的对你作品的评价是“很阿乙”,但也有一些评价认为,你“死死地顶着自己的天花板了,多次重复以前的内容,”你自己有这种感觉吗?
阿乙:只是有局部的。重复是因为在某一个细节方面,我总试图用最好的方式。可能我过去在某个动作或情节上形成了一个惯性思维,下次一闪念,觉得虽然用过了,但是无法克服诱惑,因为它是最好的,所以会重复再用一次。人在有最优选项的时候都是无法去选择一个次优项的,即便次优的选项十分新鲜,而最优的已经被重复了好几次。
这是写作的考虑,而批评的角度并非如此,批评的角度是觉得写法重复了就是有天花板。整体来说,“天花板”这个说法不是很公平,因为我写作一直以来都在变化,不会停在某个地方,我认为停在某个地方被读者超越是很耻辱的事情。我想甩脱读者,不想被读者甩脱。我喜欢变化,除了对犯罪题材念念不忘之外,我的写法以及很多东西都在变化,写法、结构、用词全部在变,没有一个地方不在变,只是这种变化有时候看起来不是那么显著。一开始的《灰故事》都是畅快的故事,之后偏晦涩,现在又开始变得不那么晦涩。我最近在实验一些新的东西。如果我不写犯罪题材了,我也会写侦破人心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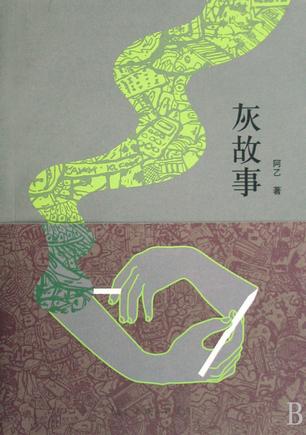
阿乙 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08年8月
界面文化:我们去年的“野生作家”系列访谈采访了很多非体制内的作家,你是否认为加入体制会限制表达的自由?
阿乙:我认为不必要把作协和非作协看得很重,对写作之外的事情,我或可或不可都行,抱着一种很随和的态度。我不是很认可体制、非体制这种标签,唯一的标准是能否把作品写出来,所有的环境都可以理解为有利的环境,也可以理解为不利的环境。成本最低的方式就是我所说的,不要去管外面的事情,也不要管自己是野生还是非野生。
不一定在体制内就是主流,非体制内就是非主流。但是一个写作者一定要把自己纳入文学史的主流,写作的时候一定要有雄心,是在接大师的班而不是旁门左道。有些作者把自己当做革命派,天天想走捷径标新立异,做一个批判者。可当务之急是把自己的代表作写出来。如果还没写出来,就为这一天而奋斗。
实际上文学就是一种继承,从远古时代的巨大主流——柏拉图、荷马、屈原——一路流下来,我们只有加入主流文学去继承、去训练,这种训练甚至要长达十年,才能说在里面取得一点点的成就,哪怕粉身碎骨,也始终要把自己纳入主流的竞争中去。
界面文化:你所说的主流,指的具体是什么?
阿乙:主流不是指作协,作协不是主流,主流是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场域,巴尔扎克、余华、苏童、格非这些都是主流。要让自己身处正统的文学领域里,而不是天天发明什么主义,也不要天天做很大的冒险。先锋也是主流,它不是原子弹炸出来的东西,它是西方和拉美本土化相结合并发生化学反应而产生的事物。主流就是大学文学课本里所传承的一种写作方式,可以做实验,但没必要自封一种新的流派。
5、“谁年富力强,谁就在纯文学的关注中心”
界面文化:“70后”作家这个群体其实是一个诡异的存在,是在“80后”的后面才真正出来的,直到现在,人们也很少会说“70后”作家,“70后”作家似乎也没有形成足够的话语权,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阿乙:“80后”是由作为第三方的他者来催熟、来摘果子的时候给他们加上的标签。也不能说书商不道德,但他们确实对这一批作家有所利用,过早地提出了“80后”的这个概念,推出了一些作家。当然,这对有些作家是有好处的,但我认为也把一些有天赋的人给耽误了。
实际上按照写作的潮流来看,“60后”过后就是“70后”,“70后”在这些年才慢慢起来。看现在的文学榜单,如果50后、60后们的作品不是茅盾文学奖级别的,那他们的反响也特别小。这差不多就要换代了,要到70后了。70后作家盛可以、任晓雯、路内,他们推出一个作品的时候,往往当年的榜单是有反应的。而等我们70后作家慢慢换不动的时候,像王威廉、双雪涛这样的80后作家的作品肯定就会接上来。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跟催熟的80后是没有关系的。时间往前走,每个阶段突出的都是年富力强者,谁年富力强,谁就在纯文学的关注中心。
我记得当时对70后也有过强行摘果子的行为,就叫“美女作家"。也是昙花一现,就是出版界为了一个噱头,强行挂上一个概念,把一些有天赋的作家囊括其中,制造一个泡沫。现在70后作家应该是主流力量,今年市面上活跃的有鲁敏,还有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是新浪十大好书第一名,还有徐则臣,甚至我认为梁鸿都是70后,她今年写了《梁光正的光》。再看60后,活跃的还是几位中坚力量,毕飞宇、格非、余华、苏童、李敬泽,周边那些作家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弱势了。如果写不出永恒的东西,那么他们所写的题材就已经让读者接受不了了。我记得有一个学历很高的读者,他说他看纯文学,看他们写的还是村里那些事,怎么看得下去呢?这是60后最擅长的写作对象。但是写村里的事情,要有办法写成永恒。无论是写18、19还是21世纪,把它用永恒的口吻去写,才会有生命力。
界面文化:永恒是什么意思?
阿乙:永恒是有悲剧意味的,有人类的普遍情感在里面。这种普遍情感在《麦克白》、在《李尔王》或者是在《奥德修斯》《伊利亚特》中,都呈现出来了,现代人也能感受得到,这就是永恒的。不永恒的就是时髦的。我举一个例子,有个很好的作家,他写了一个《愤怒的小鸟》,当时看觉得很新鲜,但是这个小说写完了这个游戏就没了,现在还有谁记得“愤怒的小鸟”?所谓反映时代只是反映一个时髦的事物,那么它就是不永恒的,是跟永恒为敌的。永恒不是空间上的,而是时间上的、纵向的那种情感,是贯穿几个世纪的,从爷爷到孙子都能感同身受的,但从亚洲到非洲都感同身受的,不一定是永恒的。文学的魅力就是这样,莎士比亚统治几个世纪,流行歌手统治几周,区别就在这里。
界面文化:你的小说是永恒的吗?
阿乙:我的野心是这样的,否则我不会动手写,就是带着这种期望,我才动手写小说。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