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在如今已被视作长篇经典之作《尘埃落定》完成的7年之后,作家阿来又推出了《空山》三部曲。如果说《尘埃落定》是聚焦藏区土司制度的兴衰变化,那么《空山》则关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史无前例的政治和经济实验。同样是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和《空山》三部曲的结构截然不同——前者是一部传统的长河小说(多卷集长篇小说),以几个人物作为线索,透过他们之眼讲述几十年的起伏变化;后者则用六部相互独立的小说展示了机村——一个藏族村落中无甚关联、但实际上都随着社会大流飘荡转变的众多个体命运。2018年,《空山》在完成15年后再版,此次,它被冠以了《机村史诗》之名。
虽然最早是以诗人身份在文学界崭露头角,随后通过发表在《四川文学》上的短篇小说走上了小说创作的道路,但时至今日,阿来最为人熟知的仍然是他的长篇作品。当被问及在中国大陆文坛是否存在长篇小说迷思——黄锦树在近日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谈到了台湾文坛对于长篇的迷恋——时,阿来否定了这种看法。他列举了一批与自己同时代的作家,诸如莫言、贾平凹、苏童、余华,并强调“我们每个人都写过很多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他又补充道:“小说不在于先划定自己,而是依据我们拿到的材料,看我们表达的对象需要什么体量。”
虽然长期与“藏族作家”这个身份紧紧捆绑,然而对于文学的民族视角问题,他的态度异常坚定:他反对那种对于藏区文化异域风情式的想象,也反对将藏族村落塑造成异族文化样本的猎奇方式。可能正是阿来自身的奋斗经历——“出生于一个偏远的村庄……后来拜教育之赐离开了乡村”,再后来成为作家——以及他亲眼目睹的藏区乡村的发展与进步,让他笃信竞争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同时也笃信所有文化都要发展、要进步、要努力现代化否则就要被淘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阿来眼中,如今社会进化论的最顶端是英美文化,后面的文化要么努力追赶英美文化,要么就被淘汰。
也正因如此,阿来认为,在中国语境下谈论“文化霸权”以及时下大热的“后殖民理论”是十分不恰当的。一方面,他以东印度公司早期殖民印度作为例证,来阐释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我们确实要研究历史,而不是依靠几个流行的概念”;而另一方面,阿来认为,在如今这个殖民国家形态已经瓦解的世界,所谓“文化霸权”已经不存在了,开放市场和自由竞争已经取代了殖民时期的强制性力量。“中国的导演美国人不知道,为什么美国的斯皮尔伯格中国人就知道,难道他派军队强制中国人了吗?”阿来如此反问。
1、谈史诗:书写宏大壮阔历史进程的当代小说亦是“史诗”
界面文化:《机村史诗》其实是再版书,之前叫《空山》,为什么改名?

阿来:之前《机村史诗》是副标题,《空山》是大标题。《空山》这个标题挺好的,但这六本书的现实性其实很强。而我们中国人说汉语总有些文化影响在里头,一说“空山”大家总想起王维的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可王维不是一个特别关注现实的人,他强调禅意。所以,这个名字可能对读者形成一种误导,读者期待读到王维那样的作品,有一种那样的想象,后来就干脆把原来的副标题用作了书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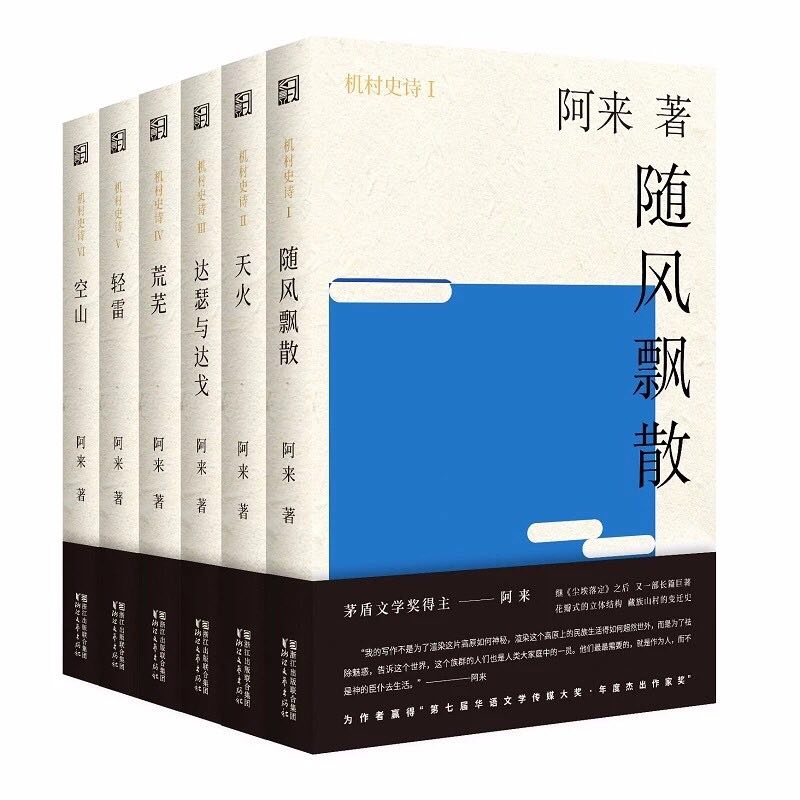
阿来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1月
界面文化:在本书最后一篇《一部村落史,几句题外话》的结尾处,你提到了哈罗德·布鲁姆对于“史诗”的定义,对你来说,在中国的语境下该如何理解史诗?如今还存在史诗吗?
阿来:我比较同意布鲁姆的说法。他写过一本叫《史诗》,在书中评价了二十多部作品,既包括过去最规范的、我们最熟悉的史诗作品《伊利亚特》《奥德赛》,也有后来但丁的《神曲》等诗歌题材的作品。《史诗》同时也收录了一些现代当代小说,比如梅尔维尔的《白鲸记》、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布鲁姆对于“史诗”的定义已经把当代小说囊括进去了,所以他其实借用了“史诗”这个名词;当代小说如果写出了历史进程中的某种宏大、壮阔以及对人性的深入,也可以被称为“史诗”。
因此,今天我们在谈汉语文学的时候,也会说很多当代比较好的作品有史诗性,或者说是一部史诗。史诗的意义在发生转化,当代文学中说的“史诗”和古典文学中说的“史诗”是两个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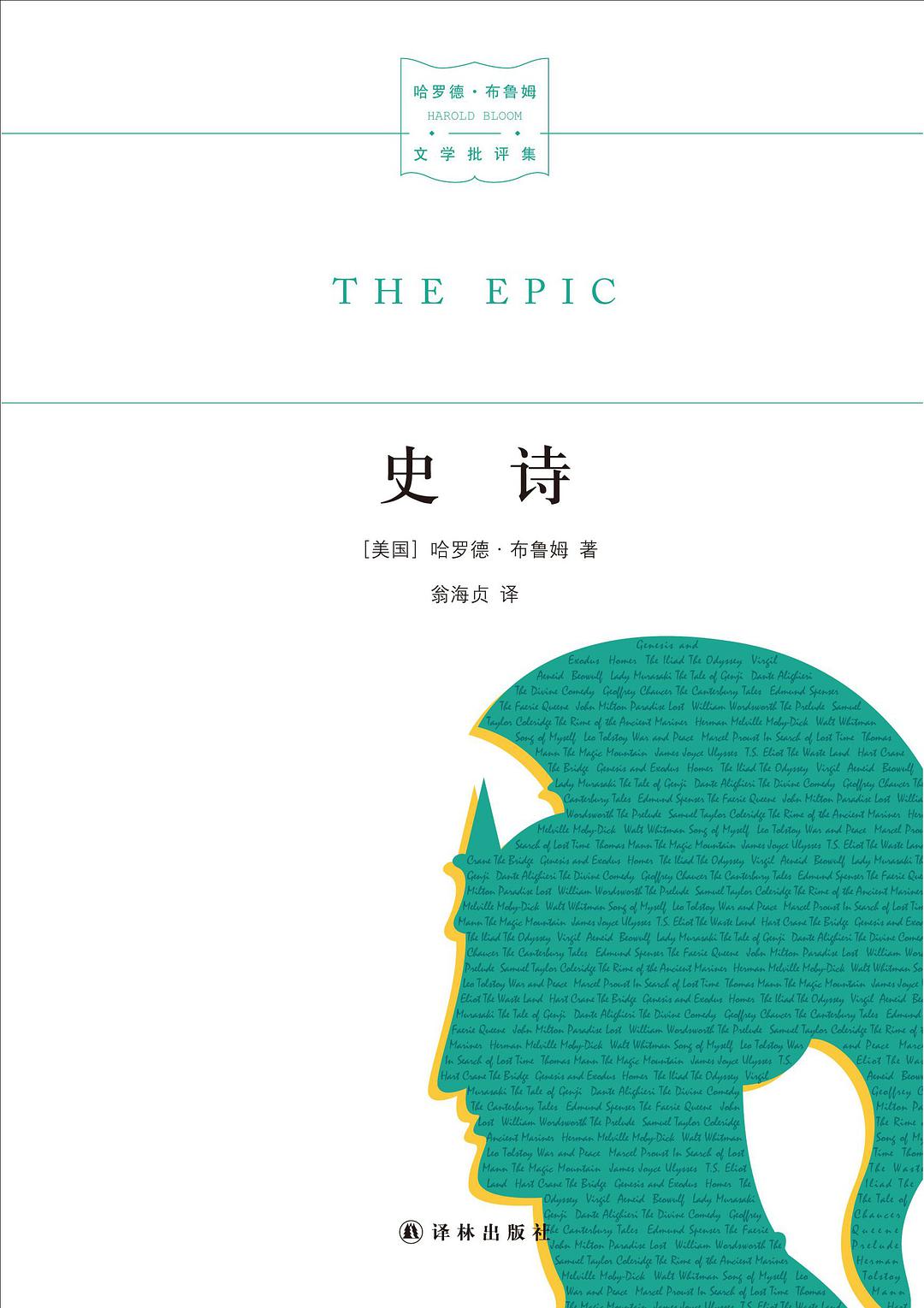
[美]哈罗德·布鲁姆 著 翁海贞 译
译林出版社 2016年5月
回到《机村史诗》,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中国文学当中还没有聚焦新中国前五十年农村变迁史的作品。上世纪五十年——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在南方其实是一九五零年——到九十年代及新千年的到来,是今天中国一切变化的基础,中国从过去一个农耕农业国家变迁成为现在这样,这种历史本身就构成了史诗的文化性。
界面文化:马来西亚作家黄锦树日前在接受界面文化的采访时谈到,目前台湾文坛有一种长篇迷思,包括很多文学奖的评选机制也会偏向长篇,导致很多作家把自己的作品刻意拉长。你觉得在大陆文坛有这个问题吗?
阿来:我的每一篇小说都非常精炼。《机村史诗》虽然讲了六个大故事,有六个单元,但每一个单元就十多万字,不超过二十万字。有些时候可能东南亚作家有点害怕大的东西,如果说我们有对长篇的迷思,也许他们反过来也有一种对于长的误解。长篇需要更好的把握,不是为大而大。
我觉得大陆不存在长篇迷思。不是说我们只能写长篇,我自己以及和我同时代的小说写作者都写过很多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莫言、贾平凹、苏童、余华没有一个人是专攻一种类型的,没有人说自己一辈子只写长篇或短篇。小说不在于先划定自己,而是依据我们拿到的材料,看我们表达的对象需要什么体量。
短篇小说形式感更强,语言的感觉和修辞发挥得更充分;但长篇有生活洪流一样的、比较粗放的力量。粗细是相对的,各有各的力量,各有各的审美风格。我们做一个小溪一个池塘,就会做得精巧;但如果是一条大河,追求的就是另外的风格。我只写一两个人的一天、一个闪念、情感当中的一个动荡,一个短篇当然够了;但是当我要写五十年,五十年当中上百个人物在大的舞台上交替出现,那五千字确实没法写,写一个梗概都不够。所以,艺术就是当大则大、当小则小。

界面文化:那跳出你自己的创作,你认为,在中国目前文学奖的评选机制中会有对于长篇的青睐吗?
阿来:没有。我们没有一个奖项是把长中短篇放在一起的,长篇就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有专门的短篇、中篇和长篇。这些不同体量是不能放在一起的,比如让一个短篇和一个长篇作比较——论修辞的精巧、形式的完美,可能短篇小说更好;但如果比内容的丰富性、深刻性,以及表达世界的宏观性,那一个短篇再怎么努力、再怎么以小见大,也没有办法和长篇比。所以这两个本来就不是可以放在一起等量齐观的东西。
界面文化:说到文学奖,2014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采取了实名投票制,你的入围作品《瞻对》当年曾被视为获奖热门,但在终选环节以零票落选。这件事你怎么看?
阿来:这是有人操作的。因为我的作品在之前一轮还有很高的票数,最后一轮就变成零票。他们的借口就跟刚我们讨论长篇中篇类似,他们就回到一个体裁问题——这个到底是不是报告文学——在这种东西上做文章。但文学是生长的,每个文体都是不断延展的,有生命力的东西就是不断突破你对它的命名,它要能够成长;如果它可以被控制下来,就不再成长了。
2、谈民族视角:“一个国家要凝聚起来,要强调公民身份而非民族身份”
界面文化:你在《一部村落史,几句题外话》中也提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问题,你认为机村虽然是一个藏族乡村,但不是一个异文化样本,人们应该以乡村和城市的视角、而非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的划分来看待如今发展的问题。为什么你认为应该采用去民族化视角?
阿来:《机村史诗》的故事虽然发生在藏族,但里面提到的改变是中国所有农村共同经历的——比如土地改革、后来的合作化、人民公社、政治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之后不搞政治了,开始转向经济;再后来就是商品化大潮的冲击,农村里呆不住,大部分人就离开乡村。所有中国乡村那五十年的经历——除了地域不同,带点儿文化和民族特性以外——实际上经历的变迁步伐是一样的,都是统一的国家政策下共有的经历。
界面文化:书中也经常提到神灵或者超自然现象,在有些地方你会用“封建迷信”这个表述。
阿来:这不是我的表述,这是时代话语。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不光共产党不信(迷信),群众也不能信。但是过去的人,尤其是中国乡村的人,总会信点什么。无非是有些信仰慎重一点,有些不太慎重。比如汉族很多信仰就不太慎重,只是一个简单的报应观。藏族人的信仰可能更纯粹,就像西方人信仰他们的宗教一样,是对神性的一种绝对崇拜,并且把这种崇拜渗透到了对于自然的崇拜当中。过去乡村鬼鬼神神的事情很多,这都是乡村文化的一部分。不然中国文学史怎么会出《聊斋志异》呢?
界面文化:《机村史诗》讲述的是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乡村的变化,那么在九十年代之后至今的这段时期,您又观察到了乡村的何种新变化?
阿来:整体是向好的。八十年代以前,我们国家希望用强制政治手段完成社会变化,比如成立人民公社等等,后来政策被证明是失败的,所以就退回去。八十年代开始经济放开,农村处于底端,因为农产品不由农民定价,都是国家定价。那个时候农民的最后一条路就是离开土地,进城从事最低贱的工作。这在《机村史诗》小说结束的时候都还是这种情况,而且农村里存在着大量资源破坏、环境破坏问题,“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农民都是这样,没文化。
新千年以来,尤其是这十多年,情况在慢慢变好。农民开始得到一些帮助,比如开始有医疗保险,有的地方甚至有养老保险了;政府也开始往农村投入,帮他们建设新农村,帮助他们改善居住条件;对困难一点的地方,有目前全国都在做的任务很重的精准扶贫。而且这些变化并非局部发生,而是整体在改变。现在的新农村建设让我觉得很欣慰,当然有的地方做的好,有的比较形式主义,可总体至少在社会造成了这样一个倾向。过去我们完全把农民当成下等中国人,现在虽然社会不公平还存在,但是起码在朝着公平努力。这个社会就这样慢慢前进,胜利者要照顾弱势群体,但也不能完全取消竞争。过去计划经济就是完全取消竞争,人在这个机制里就完全懈怠了,所以竞争是有必要的,但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竞争中要照顾那些不够强大的。
界面文化:一方面,你强调去藏族或者藏文化的中国经验写作,但另一方面,你身上一直贴着的藏族作家标签,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困扰吗?
阿来:不困扰我,但我认为老根据这个标准区分不好。世界上一些更先进的国家比如美国,都是多民族国家,但他们很少强调民族身份。一个国家要凝聚起来,更多要强调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中国人现在较少强调这个身份,经常强调民族身份。古人说“和而不同”,“和”就是消除身份,抹掉差异,可一旦强调每个人的民族身份,就是在强调差异,而不是缩小差异。
界面文化:但比如在澳大利亚,内部会非常强调原住民和非原住民。
阿来:澳洲的情况我也知道,我和他们很多作家都是朋友。今年我还去给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作家亚力克西斯·赖特当嘉宾。政府对原住民有赎罪的心态,当年殖民者在未经原住民同意的情况下占领了土地,所以现在政府认为应该对原住民好一点,给他们补偿。这是国家整体政策层面的问题。
界面文化:以赖特为例,她特别强调原住民自己的传统和文化,包括口传历史,因为她担心这个文化传统可能会消失。
阿来:说是说,你要看她的作品。她的作品是关于原住民的,但如果她完全写成原住民的形式,你能看懂吗?她还是采用了英文小说通常的写法来写。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主张,在我看来,那些神话传说自然而然就有,你自然而然把它写出来就行了,没有那么多要保存的。原住民还有一个问题,他们连文字都没有,要保存其实是不可能的,说说而已。人类社会在进步发展,发展就是大家找共同的东西。
赖特本身采用了当代英文小说的写法,而且驾驭得非常好,尤其是《卡彭塔利亚湾》,放在当代英语小说中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只是在策略上,她需要强调原住民身份和文化。可澳洲原住民和中国少数民族情况毕竟不同,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同,社会才反过来愿意包容他们、补偿他们。每个国家的历史形成完全不同,在这个前提下,中国文化当中要储藏什么、宣扬什么,不能照搬澳洲的经验。

3、谈进化:“一个文化如果无法和现代性达成一致,就会被抛弃”
界面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否担心藏族文化会被汉文化同化?
阿来:我不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竞争的世界,达尔文就发现了这一点。竞争既发生在生物个体之间,比如人跟人之间、山里的动物植物之间,也发生在文化和文化之间——要不被淘汰,要不自己现代化。自我更新很重要,所有文化都需要把自己变得适应今天的社会。就是两个关键词——科学和民主,只要包含了这两个东西,这个文化就还有活力,还能继续成长。文化跟现代性达成一致,如果没有达成一致,就会被这个社会抛弃。藏族文化当然也有这些选择,我们要做的不是让它不变,而是像很多好的文化曾经历过的那样不断革新自己。中国重新开始崛起强大,最基础的东西就是新文化运动,就是语言和文字的革新,是从文言文变成白话文的革新。
界面文化:我很好奇你怎么看待人类学里带有反思现代化意味的、对于藏族或者藏文化的研究?
阿来:人类学从诞生那一天起,不是从纽约从巴黎开始做研究的,而是跑到最偏远的地方去取文化样本。列维·斯特劳斯是这样,我读过他几乎全部的著作。美国的玛格丽特·米德写《萨摩亚人的成年》,是专门跑到太平洋最封闭的岛屿上进行研究。他们是在寻找原始样本,如果他们只是为了维护原始样本,那么这个工作就没有什么意义。他们还是强调差异,永远要把差异保持下来,而且希望它们一成不变。人类学家去观察几天,又回纽约了,又去声色犬马了,他们告诉自己的研究对象你们就刀耕火种很好啊,不要改变。下次再看到这群人,发现他们不再钻木取火而开始用打火机了,人类学家就觉得:“天老爷,这还得了。”原来他们袒露上身两个乳房,像木瓜一样晃晃荡荡,下次一来发现怎么穿T恤了,这不对啊——但他们自己一直穿得很好。所以我觉得,人类学当中有一个偏向不好——研究者在进步,而让研究对象不要进步。这就相当于在地球上建立一些活形态的博物馆,以活形态的人来表演古代和原始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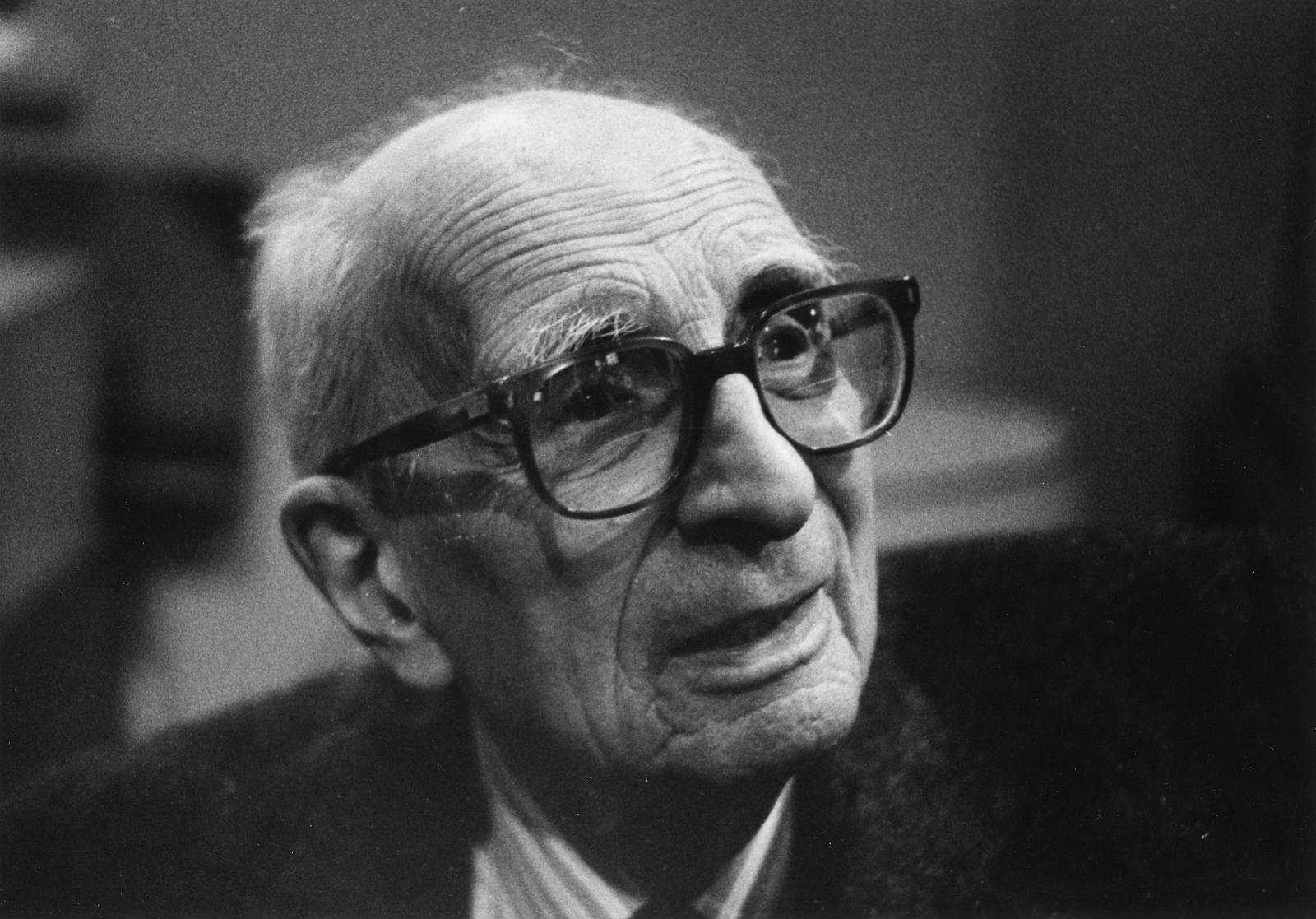
界面文化:所以在你的预设里,所有的民族和文化都是想进步的?
阿来:不可能不进步,只是没有能力,没有遇到机遇。任何一个文化都是进化的结果,跟猿猴、原始人比都在进步。所有文化现在都在从事生产,都有社会组织,只不过是从事生产的手段和工具有区别、社会组织好不好有区别。所以每个文化都在进步,只是速度快慢的问题,有的是龟兔赛跑中的兔子,有的是乌龟而已。
界面文化:那进化链的最顶端是什么文化?
阿来:现在谁走在前面,就是哪种文化的样子,今天就是英美文化的样子。
界面文化:你是百分百的进化论信奉者?
阿来:我反正不想回去当猴子,反对进化就是愿意回去当猴子。进化产生了一个优美的结果,就是让我们变成了今天这样——不是山里的猴子,也不是原始人、山顶洞人,整天光着屁股在山上拿个石头寻找猎物,茹毛饮血。进化是必然的,只不过今天的进化论会带有一丝同情,已经处在顶端的对于那些跟不上趟的多一点同情、多一点帮助,刚才澳洲原住民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现在进化论对自己的调整就是,不能通吃,还得留点空间给别人,让人家也来分享。这个是今天的进化论和上世纪进化论的不同之处。上世纪进化论没有同情,没有对失败者的怜悯和照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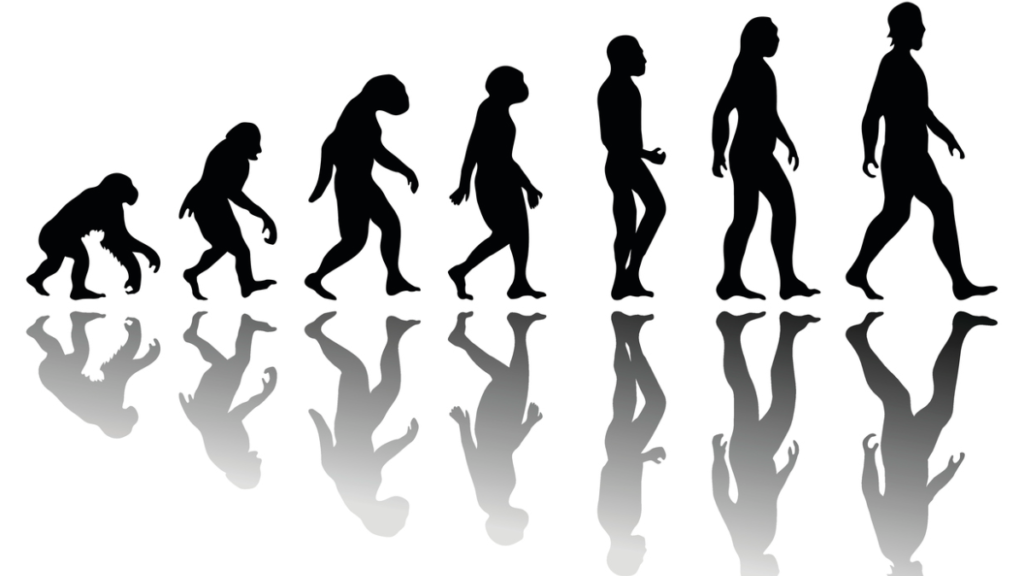
界面文化:所以你用汉语写作也是对进化论的一种实践?
阿来: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几种共同语言,不要用“汉语”这个词,我建议用“中文”,否则我会觉得你是一个汉族沙文主义者,这门语言文字是中国人共同使用的,并且在国际上有个更好的称谓。还有东南亚的一些作家,他们已经不是中国人了,因此说“中文”都不对,而应该用“华语”这个词。
过去的学者比我们伟大,陈寅恪先生说华夷之辨不是民族,不是种族,是文化。文化最大的原因是语言,是使用何种表达工具。文化涉及传播,我们希望更多人分享文化。使用小语种的结果是分享的人少了,使用大语种的结果是分享的人多了。中文是国家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几十个民族使用的共同语言,在西方叫官方语言,多民族国家会规定官方语言,下来可以讲各自的语言。中国、美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如果不规定官方语言,各说各话,大家就不能坐在一起,坐在一起就是哑巴。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可以保持对原来小语种的忠诚,但比如我今天坐在这,跟你说藏语的话,这个沟通就失效了。语言创造出来是让人沟通的,不是让人表达民族身份的。所以我还是觉得,我赞同叫“中文”或者“华语”,这是一个更具开放性的姿态,我们准备接纳更多人来使用这个语言。
4、谈文化霸权:“在处理当下方面,中国确实没有很好的作品”
界面文化:但这里面会有一个文化霸权的问题,当然在你看来可能就是进化论的结果?
阿来:首先要注意,我们中国人在使用一些过时的文化概念。文化霸权来自后殖民理论,但凡人类历史上有一个理论出现,都是迎合一种政治运动。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欧美国家衰落——它们不是第一次衰落——失去它们的殖民地。但印度人发现,虽然赶跑了英国人,他们还得讲英语,因为印度各个民族之间语言不通,所以到今天印度官方语言还是英语。英国人在印度时候那个叫文化霸权,今天英国人走了,就不存在文化霸权,是印度自己的语言没有强大到这个程度。所以文化霸权几乎是一个有点过时的概念。我们中国在用一些西方的过时的理论,二战前后是反殖民主义,但现在已经没有殖民主义国家了,至少国家形态不存在了,所以今天再用这套理论和话语就不对了。
第二点,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跟英国人占领印度几百年是不一样的。而且更荒唐的是,最早控制印度的还不是英国国家,东印度公司组织了二十万人军队就把印度占领了;最后一百年东印度公司不行了,国家才从东印度公司手里接手印度。所以我们确实要研究历史,而不是依靠几个流行的概念。这些概念听上去很好,但是真正实行起来非常恐怖。

界面文化:你刚提到“文化霸权”这个概念是过时的,因为这些国家现在已经不再被殖民了,也提到了研究历史的重要性,可当谈到这些曾经的殖民地的时候,这其中涉及的历史因素以及历史对当下的影响就是不重要的吗?在当下去看这些曾经的殖民地的时候可以直接把历史因素抽离吗?
阿来:你觉得美国有文化霸权,但是反过来想,要是真正反思的话,你把自己的文化变成霸权文化不就可以了。要是中国的电影好看,人们不就不去看美国电影了吗?霸权是中国送给美国的(说法),美国说“我不要啊”,我们的电影到中国来也参加自由竞争,我们并没有派警察或海军陆战队说“我们美国电影你们必须看啊”。这是自愿发生的,不能说别人还在行使霸权。
霸权分为自然形成的霸权和强制形成的霸权,二者不一样。殖民时期是一方不干另一方就打,今天很少这样,都是参与竞争,市场开放。为什么美国人不听毛阿敏和王菲,而中国人就知道鲍勃·迪伦呢?中国的导演美国人不知道,为什么美国的斯皮尔伯格中国人就知道,难道他派军队强制中国人了吗?而且我们国家也在层层壁垒保护,让美国电影少进来一点,中国多放点儿自己的烂片。这里面有文化霸权,但是文化霸权后面的生成机制变了。过去是不接受他们来中国做生意就开打,比如鸦片战争,但现在没有了,现在就是谈判。殖民时代是不情愿,不情愿就要挨打,今天是心甘情愿的,哈这个哈那个,都是自愿发生的。不要说美国了,韩国我们都哈。
界面文化:那在文学上呢,我们现在读英美文学是因为它们比我们好?
阿来:我们古典的诗歌和散文确实创造了一些独特经验,但是在处理当下方面,中国确实没有很好的作品。西方社会已经走到前面了,而我们中国正在经历西方曾经经历的阶段,我们现在写到的这些,比如农村经验,英国两百多年前工业革命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小说家了。比如哈代《德伯家的苔丝》讲的就是姑娘在农村待不下去了、进城当保姆当佣人被主人强奸的故事,这背后也涉及乡村转型。所以英国是先发国家,我们是后发国家。我们自己叫做发展中国家,世界上有另一个词叫后发展国家。
界面文化:如果我们是在写别人已经写过的东西,那中国作家和中国作品的独特性在哪里?
阿来:中国也有演变的特殊性,但是相对来说,先锋性在西方。西方先面临问题,就先表达,我们不可能超前。因为他们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中国还在清代中期,那个时候写什么呢?那是写《红楼梦》的时代。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必须承认,文明是有几个级差的,中国目前算是跟得比较紧的,有跟得慢的或是完全跟不上的,甚至放弃不跟了的。
界面文化:完全放弃的有哪些?
阿来:比如澳洲原住民,人口都不够,那就放弃了,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放弃了,有一点东西就要求政府保护。
界面文化:所以在你看来,首先是自由竞争,如果无法参与竞争,就通过政府和制度保护?
阿来:也不光是制度,在社会上还有一些基金会、NGO组织也会做这些事情。只是在中国这些都刚刚起步,这些社会组织不发达,因此我们总觉得所有事情都是政府在做。第二,我们大企业也没有养成做社会贡献的习惯。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