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阿巴拉契亚参观芭芭拉·金索沃(Barbara Kingsolver)的农场,感觉就像是来到了神奇的荫凉之地。在我们驾车经过弗吉尼亚州阿宾登(Abingdon)附近的城镇时,金索沃指着一些颜色鲜丽的木屋对我们讲解道:这座客栈建于1779年,那边的巴特剧院(The Barter theatre)在大萧条时期就有了,当时演员们通过演出换取食物,“拿火腿换哈姆雷特”。紧接着,我们就看到了她那又大又舒适、饰有沉重木梁的农舍,钢琴上摆着巴托克(Bartók)和萨蒂(Satie)的乐谱(金索沃凭音乐奖学金进了大学,还加入了各种乐队)。
在她询问我对咖啡的喜爱程度时,她的边境牧羊犬一直跟着她。“我来自南方,”她笑着说,“我想让你开心。”如果这一切听起来如同田园诗一般美好的话,你要知道,金索沃本人可不是甜言蜜语那一类型的。她温暖又爽脆,这个地方对她而言,让她得以安全地审视外部世界许多值得警惕的现象。她的新书《无所庇护》(Unsheltered),是对此前出版的作品——诸如《空隙》(The Lacuna)和《毒木圣经》——的一次回归,风格宏大、富有野心。小说尽管描绘了一幅人们生机勃勃居于其中的景象,作者的观点却颇为苦涩。世界濒临崩溃,主人公薇拉·诺克斯(Willa Knox)来自新泽西州的瓦恩兰(Vineland),这本是一个乌托邦社区,却遭逢了一系列变故。诺克斯被杂志社解雇,还承受着丧亲之痛、惨重的学费债务、医疗支出和蒸发一空的投资,一切都在解体。
在忙着不让房子倒塌的同时,诺克斯对1870年代生活在这片社区的人们产生了兴趣,他们组成了小说的第二部分。撒切尔·格林伍德(Thatcher Greenwood),一位热衷达尔文思想的科学老师最近同野心勃勃的罗斯结婚了,二人的婚姻并不稳定,对达尔文思想的狂热又使得格林伍德承受着被解雇的风险。他们也和诺克斯一起,居住在同一幢建筑里,“整个房子像是在和自己闹矛盾一样,”地基打得十分糟糕。格林伍德和历史人物玛丽·特里特(Mary Treat)成了朋友,后者曾和查尔斯·达尔文、阿萨·格雷通信。特里特的时间都花在了科学实验上,诸如把蜘蛛放进罐子里、让食肉性植物啮啃她的手指好几个小时——金索沃还给我看了她花园里的一些食肉植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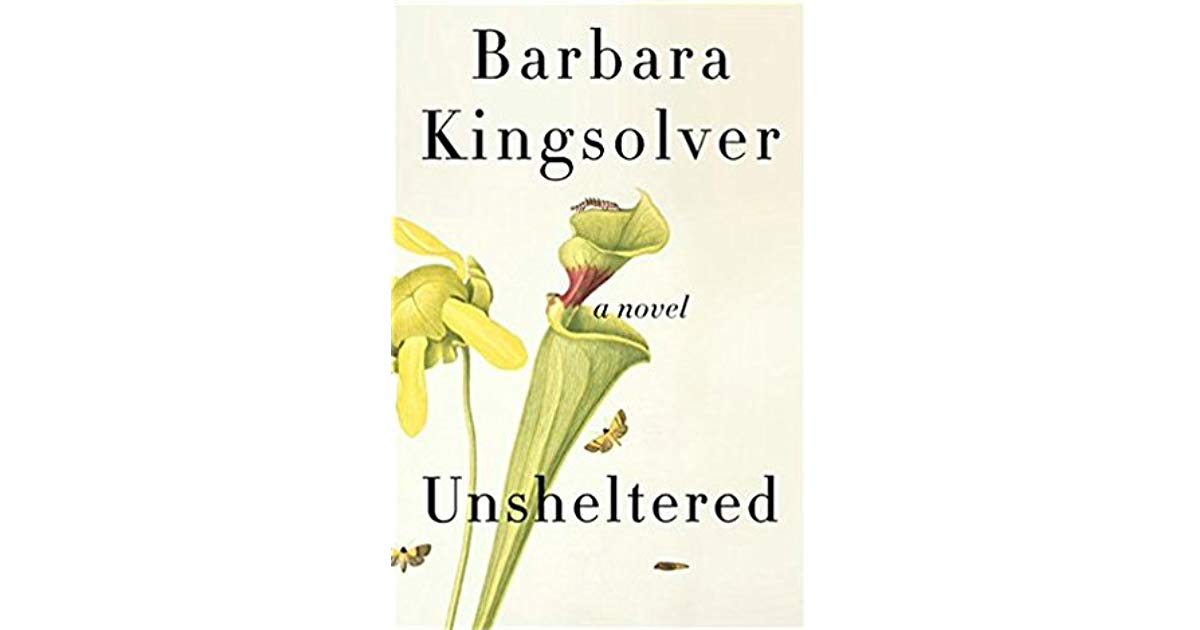
她认为“回到历史中,人们会对自己的存在有一种绝对的错位感,这样的时刻是有用的”。在决心“我要写美国小说”之前,她曾考虑过要以达尔文本人作为素材。“多么好的一个人啊!”她说道,“幸亏当时没有互联网,人们太讨厌他了。连埃米莉·狄金森都讨厌他,而她几乎不讨厌人的。”“很难去理解他的思想有多危险,”她这样评价达尔文,因为他告诉人们世界实际上并不掌控在我们手中。她期待能在小说《无所庇护》中探讨“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这个问题,“如果人们觉得自己是活在世界末日里,他们会怎么做?因为这正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一点应该没有人反对。许多人甚至在10年前就这样说了,但现在他们是真的在发问‘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就像1871年的人们一样,小说中生活在2016年的这群人也挣扎着意识到,他们对生活的预想和期望,包括他们对自然和经济规律的理解,都已经不再适用。曾经所相信的——“冰就是冰,海里总是会有更多的鱼,”增长和消费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努力工作是会有回报的,每一代人得到的比上一代人多——这些信念已然土崩瓦解。金索沃说,不管是现在还是罗马帝国灭亡之际,“在每一个时代行将结束之时,人们会越来越紧地依附于他们所知的这个世界。”这就好像“把一群老鼠放在盒子里一样”,金索沃比喻道。这也很正常,当物质的世界摇摇欲坠,人们会去寻求旧的观念做庇护。“我们要么做出选择,要么让那些在半个世纪以前,即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形成什么是好的、如何解决问题这样一些观念的人们来引领我们向前。看看是谁在带着我们前进吧,他们可都西装革履,不再年轻。”对这一点,金索沃并不奇怪。
小说中那些虚构家庭所经历的每一次经济灾难,金索沃说,都在她认识的人身上发生过。“末日已到达其核心,”她相信这会让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社会运作的方式。在美国,直到最近,“还有足够多的人相信我们值得所拥有的一切,”并由此滋生了“可怕的美国式疾病”——责备受害者。

《无所庇护》显然是一本探讨自我依赖与相互依赖之间张力关系的书。“这是辩证的,”她说道,“在我写的每一件事的中心,最基本的冲突是个人表达的欲望、成为一个有能力照顾自己的人,与所依赖的社区以及社区中不被我们注意或者承认的种种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在她攻读生态学和生物进化学博士学位时,这个想法就已经产生了。当时,她的研究方向是遗传学的利他主义,但是这一主题在经历了一次“信仰危机”之后被抛弃了。“我躺在床上,在脑海中数着会有多少人读这篇文章,我得到的数字是11。”这不仅仅是智力上的一种兴趣,“在许多将生命致力于服务的人身上,我看到的是不开心,是受挫,是痛苦,真是这么回事。我母亲那一代人并不怎么开心,我猜这也是为什后来他们有那么多人服用镇定剂!我不想要那样一种人生。”
但金索沃不是那种容易迷失的人。她的第一本小说《豌豆树》(The Bean Trees)是在夜间完成的,当时她还怀着大女儿卡米尔,白天她是一名记者。她注意到自己的失眠在某种程度上也帮了她很大的忙:“每个人醒着的时间都相对固定,除了我。”到了预产日期,卡米拉还没有出生时,医生建议她引产。但是金索沃拒绝了,她利用这一段多出来的时间完成了《豌豆树》的创作。后来,卡米拉和莉莉(莉莉是她第二段婚姻中的孩子)都知道了,不能在她工作的时候打扰她。“在两种情况下你们可以敲门,”她记得曾经这样告诉孩子们,“动脉出血和房子着火。”尽管里面有玩笑话的成分,但是“两个孩子非常尊重这一点,她们知道妈妈正在做着很重要的事情”。她从没想过要结婚,或者依靠一个男人,她觉得“自己不是那种在家里做饭,价值得不到认可的人”,金索沃说,“我渴望我的人生由我自己来定义,我也明白没人真的能彻底做到这一点,没人是完全意义上的自我。这其中的道理就在于,任何事都没法孤立存在。”

就在这时,金索沃的丈夫斯蒂芬·霍普(Steven Hopp)从阿宾登给我们带来了午饭。他在附近的埃默里-亨利学院教书。当金索沃发现窗户上有一只撞过来的死鸟时,他马上识别出这死去的鸟是一只黄莺。他们1993年相遇,那时,她从亚利桑那州的图森过来,参加为期两周的临时性作家指导工作。作为单身母亲,她当时的情况“十分困窘”。在他的野生动物保护课上,她做了讲座,“大概是讲得太好了,好到他想要娶我。”尽管对婚姻疑虑重重,并且离过一次婚,他们还是保持了联系。当“电话费超过贷款后”,两个人开始一起生活,最后在弗吉尼亚的农场定居。
金索沃虽是在肯塔基长大,在阿宾登却被当作是本地人一样对待。她家中好几代人都曾在这里生活,她的曾祖父还在这里为人接生,长达数十年。“我就是典型的乡下人,看起来我们各不相同,这是其中一种样子,”她说道。她也抱怨,自己不能够以牺牲邻居利益为代价,去观看那些晚间政治喜剧。即便是那些“从善意出发的朋友们”,对她居住的地方,观点也不能免去偏颇。她也理解,为什么中部地区对“持代表城市的、开明的文化观点的人怀有鄙夷,这是真实存在的。既苛刻,也在不断恶化”。这也是为什么19世纪诱发了她无穷的想象力,当时,“我们也刚刚经历断裂内部,国家一分为二,就像现在一样两极分化。随之而来的还有相似的地理区域划分,这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对立主要是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对立,直到现在,曾经断裂的也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金索沃喜欢挑战艰巨、“不舒服”的主题,比如说,写美国对刚果做了什么,并将这一主题用她能找到的最耐人阅读的方式创作出来,这样一来,全世界的读者、读书俱乐部的成员们都能在她提出尖锐的问题中享受阅读本身了。“我所处的位置非同寻常,”她说道,“因为我是以一位文学作者的身份写作的,每一个句子、图像、隐喻和主题,我都必须力臻完美。但与此同时,我还要让人们能够理解我笔下所写,这大概是我生长于斯的缘故吧。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会送孩子们去公立学校读书,我想让她们和普通人一样,不想让她们产生任何优越感。因此,我是真的希望所有能阅读的人都能读懂我的小说,我也想让人们有继续读下去的愿望。”新闻工作者常常惊讶于她的作品有如此大的雄心,他们总是要问这样的问题:“你能这样写?”她发现:“男人不会被问这样的问题。”尽管如此,她还是给出了答案。她从没上过任何写作班,“在八九十年代,我没有去拿什么艺术硕士学位。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声称冲突必须在婚姻里发生,或者至多是在杂货店里。我不知道那是我应当做到的,所以也就没有去做”。
要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美学问题。“这个国家长期以来对探讨真实问题的艺术都怀有敌意。我可以写父亲如何酗酒,却不能说致使他酗酒的经济因素。”《空隙》的背景是麦卡锡执政下的美国,讲述了墨西哥画家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的故事。通过这本书,金索沃“尝试回答是什么致使这个国家的人对探讨问题的艺术如此警惕。要看清楚自己生活在怎样的鱼缸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她发起的贝尔维德文学奖(Bellwether prize)旨在奖励记录社会变迁的作品,这是金索沃对该问题的另一种回应方式。过去二十年来,每隔一年,贝尔维德奖就会推出一位新的作家。她注意到,事情开始有了变化,小说是这样,外面的世界也是这样。以美国为例,“30岁以下的人们,有一些将自己定位为社会主义者,或者至少是非资本家,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在他们看来,无限增长是科学幻想,人们不能哪天就跳到火星上去,在那里开始建造城市。”尽管如此,她也说,“抚养两个女儿,眼看她们遭遇和我一样的性别歧视,遇到同样的性骚扰,这是一件十分令人沮丧的事情。”甚至年轻女性在婚后随夫姓这件事也让她困扰,她想不通,“抹除自己”怎么就这么流行。
不管怎么说,金索沃仍然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这是因为,在她看来,乐观是唯一可操作、唯一对得起自己良心的选择。在完成《无所庇护》一书的草稿后,金索沃前往澳大利亚观看大堡礁,在向我讲述的过程中,她迅速纠正了我关于暗礁悲惨命运的说法。“那些关于礁类死亡的报道太夸张了,”她说,并且清晰地向我解释了为什么那些珊瑚能在那样特定的微气候中存活、自愈和适应。
“你所听到的都是关于死亡的消息,你并没有听到有什么活了下来,”金索沃说,“如果你认为它已经死了,一切都太晚了,那么你就不会再受到困扰。我甚至认为,人们会倾向于思考‘一切都太晚了’,那样的话,他们就不用再努力去做什么了。”就好像是不经意间在告诉我,她的小说里世界会以那样缓慢而痛苦的方式坠落,为什么是一种对今日危机的回应。她说:“你只有爱某样东西,才会将自己置于麻烦的境地,只是为了去完成它。”
(翻译:朱瑾东)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