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依旧困扰着世界经济和我们的政治生活。它也扰乱了我们对全球一体化叙事的理解。直到最近,“走向全球”都仍是一个颇具天下大同色彩的故事:世界一体紧密互联,技术治理同舟共济。如今,它完全变了个样:当今的故事充斥着崩溃、灭绝和毁灭。它们成了本土主义者的操作手册,这群人坚信相互依赖必将引发大灾难。
我们的宏大叙事一度是谨慎周到的,现在则有些非此即彼,在兴高采烈和烦躁不安之间剧烈摇摆。对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每一个希望故事而言,衰落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的;到了19世纪,自由主义者不得不跟保守主义者以及宣扬末世预言的激进派展开对抗。其中一些人视危机为机遇。在卡尔·马克思的影响之下,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也提出要变废为宝。摧毁业已腐朽的旧制度之后,富有创造力的新事物必将诞生。后来,出生于德国的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hman)又认为,失衡状态(disequilibria)乃是孕育着新思想的温床。1981年,他提出危机分为两类:一类只是令社会解体,另一类则迫使社会成员绞尽脑汁构想出路,他称后一种为“综合性危机”(integrative crisis),人们将会团结起来谋划全新的前进道路。
见证过一战灾难以及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兴起的熊彼特和赫希曼有一种特别的写作风格。且不论1930年代的恐怖和黑暗,二战也同样激起了一种希望:危机终将平复,社会迟早能摆脱混乱局面。人们可以管理好经济,避免周期性的毁灭。二战结束后,胜利者们发起了一场全球性的狂欢(spree)。他们大举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派遣顾问和投资者,鼓吹资本主义现代化。作为这一高歌猛进的时代氛围的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Walt W Rostow)在1960年曾说过。“利滚利的大好局面带来了福气和诸多的选择。”所谓的“第三世界”受众们一般都会对罗斯托的说法表示不满,但他们和罗斯托有一共同点,那就是相信未来尽在自己掌控之中。
即便年景不好,全球一体化的鼓吹者也必须想出一系列新故事来回应其挑战者。当西方资本主义在1970年代频频陷入困境,充满阳光的战后故事变得阴沉了起来。集体行动的问题、社会的僵化与搭便车者令忧心忡忡的科学家们烦恼不已。不过仍有一些人视此为机遇时刻。这种情形至少局部上符合赫希曼所谓的综合性危机。对发展中世界来说,这是一个纠正历史错误、构思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大好时机。一度沉闷的局面也催生了协作管理和跨文化的交流。虽然对市场进行规制的理念遭到边缘化,但政府确实试图在其它某些领域约束过热的竞争。环保主义者们对资源耗竭和人口过剩作出了相当悲观的预测,他们在1972年于斯德哥尔摩召开的首届地球峰会(Earth Summit)上倡导生态保育和共同愿景。我们及时地就控制氟氯烃(chlorofluorocarbon)用量达成了共识。围绕核问题展开的对话永远都是最高规格的,它使世界成为了一个军备控制体系。渐渐地,我们进一步就控制碳排放签署了相关条约。与人道主义、军备控制以及生态相关的诸多协定目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它们的根基是否牢固,取决于下述的故事能否确立其正当性:面临高度不确定的世界局势,我们依旧要推进一体化。
1989年结束的冷战令人们讲述全球一体化故事的习惯发生了深远变化。在没有来自东方的竞争或南方的挑战的情况下,进步的宏大叙事坍缩成了一出独角戏。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构想让位于“华盛顿共识”;社会主义的一体化构想亦失去了它一贯的诉求。美国政治科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一文里捕捉到了时代精神的脉搏——不过所有人都忘了这一题目是以问号结束的。柏林墙的倒塌和新自由主义的胜利造就了一个新故事,面对人称“达沃斯人”(Davos)的全球精英主导的世界,它推崇市场的纯粹性、富有远见的企业家和小生意的解放力量。在《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一书中,美国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对自由贸易、开放式交流以及全球供应链的利好大加赞赏,不乏溢美之词。正如许多评论人士的乐观表态所言:只此一途,别无他法。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的《向前一步》或许是这种“我全都要”(have-it-all)式风格的绝唱,书中精心编织的故事以她在谷歌和Facebook担任高管的经历为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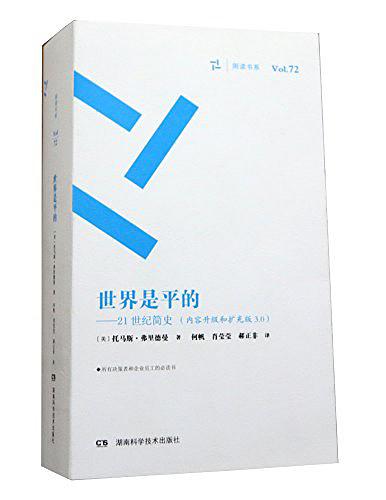
托马斯·弗里德曼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04
一些挑战者对“世界是平的”这一叙事表示了异议。下述的人群对这种叙事就不感冒:恰帕斯州的农民、“西雅图战役”中的抗议者,以及在气候变迁的政府间座谈小组背后辛勤工作的科学家们,都在为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而斗争,这些故事指向流离失所、不公以及日益严重的碳排放问题。但“世界是平的”叙事的力量异常强大,它几乎完全窒息了反对声音。

直到金融危机降临、冰川碎裂的奇景出现以及“阿拉伯之春”以极度扭曲的结果收场之后,这种凯旋主义(triumphalist)情绪才遭到挫败。转眼间,兴高采烈的氛围就变成了一曲烦躁不安的大合唱。
如今,哪怕是那些最为精巧的故事也开始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有分道扬镳的危险了。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便将不平等与低增长的弊端摆上了台面。它还有一更为广泛的主张:从历史的角度看,1930年至1975年的高增长率乃是异常现象(aberration)。透过这项分析,我们应当看到当今的低增长、经济停滞和不平等在历史上乃是司空见惯的事,需要解释的反而是1945年以后的几十年何以如此繁荣。英国历史学家亚当·托泽(Adam Tooze)2018年出版的《崩溃:十年金融危机如何改变世界》(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一书也给人留下了一种沉沦的印象:2008年的危机如今还远远谈不上结束!与此相反,它令这个世界愈发债台高筑,且经济权力也更趋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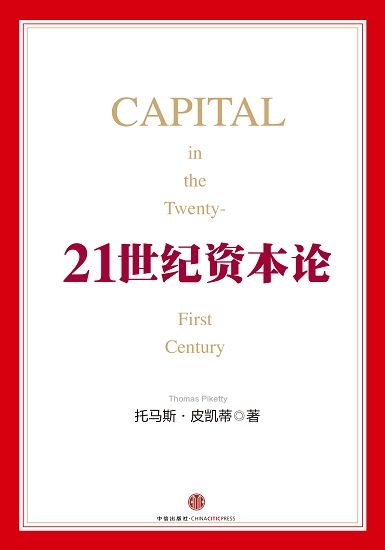
托马斯·皮凯蒂 著 巴曙松 等译
中信出版社 2014-09
皮凯蒂和托泽并不打算解释人类究竟是如何登上这趟开往毁灭的班车的。相反,他们的贡献在于对当前的新常态进行了提炼和浓缩:其中灾难成了新的缺省设定,不平等和迟缓的增速也成了新规则。皮凯蒂著作的最后一部分详细探讨了一些切实可行的、针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修正措施。尽管进步主义目前的真空态势导致世界各国政府落到了右派本土主义者手中,但皮凯蒂对改革前景的讨论却没能引起多少回应。如果说,熊彼特指出了危机也是运动和进步的契机,那么托泽则讲述了一个建制派拒绝从其一手造成的危机中吸取教训的故事。就金融危机的恶果而言,真正的失败在于:其始作俑者根本看不到,由自己一手炮制的、所谓不受监管的“金钱人”(Homo pecuniaria)的英雄般故事,才是应当为危机承担主要责任的——但到头来被迫为此买单的却是旁观者和纳税人。
末日叙事的受益者是愤怒不已的本土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约拿·戈德伯格(Jonah Goldberg)和尤瓦尔·莱文(Yuval Levin)等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圣贤”们则是其精神支柱,而后面这两人又颇为推崇那个老生常谈的衰落故事:一曲“西方”文明的挽歌。《纽约时报》的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为美国无可避免的破败深感痛惜。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巴西总统雅伊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和匈牙利总理维克托·奥尔班(Viktor Orbán)来说,只有唯一的、严酷而自私的选择:要么是全球性的大灾难,要么得到拯救,他们自诩负有特别的使命,声称可以带领我们走出由全球盗贼统治(plutocrat)一手造成的末世局面。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仍在为了究竟该责备谁而争吵不休——这就进一步强化了我们身处危机这一共识。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务必要看破大灾变修辞的一项伎俩。种种毁灭类故事皆依赖于把张力(tension)说成是不兼容的(incompatibility)。所谓张力,是指两种力量发生了争执——譬如热与冷、价格稳定与就业,以及帮助陌生人与支援邻居。虽然两者方向不同,但却是可以共存的。早期的宏大叙事曾经以张力和不稳定的妥协来解释选择。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争论主要聚焦于发展中世界能否既取得进步,又保持自己作为更广泛的全球经济体的一员。十年后,张力变成了如何共同管理好面临威胁的全球共有物(global commons,指大气、海洋、两极地区、外层空间及互联网——译注)。
今天,大灾变的合唱又把一些差异说成是无药可救且不相兼容的,视其为零和的(zero-sum)抉择。要么全球主义,要么“本国优先”;要么拼就业,要么拼气候;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其思考模型极为简陋:之前的领导人都是头脑糊涂、举棋不定、软弱妥协且态度暧昧的。在竭力回避作出艰难决定时,他们也将整个国家带向灾难的边缘。
悲观主义当然有助于退治1989年后的凯旋主义热潮。皮凯蒂和托泽正确地指出了不平等的结构性特征,说明了大灾变的始作俑者何以又成为了它的受益者。但我们也需要看到,贯穿于整个意识形态光谱的大灾变共识——但这种共识如今正滑向一个更加阴暗、更具敌意的极端——对强人政治也有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且压制了那些对本国优先论仍有疑惑的人。
对“世界是平的”叙事抱有怀旧情绪,企图透过把技术当成灵丹妙药并恢复市场原教旨主义来寻求庇护的做法,无益于寻求解决之道。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回到“向前一步”的童话中,以临机应变的灵活之道来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借此来平复心境。若要从崩溃和灭绝中吸取教训,要防止其故态复萌,我们就必须重建自己驾驭及讲述复杂故事的能力,思考张力而非不兼容性,容纳选择与替代,接受含混性、模糊性与不稳定性,并学会摆脱对深渊的错误确信(false certainties of the abyss)。假如我们做不到这些,芸芸众生或将难逃一劫。
(翻译:林达)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