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出版于1987年的《美国精神的封闭》抨击了高等教育的本质,其核心论点是反对文化相对主义。“有一件事是一个教授可以绝对确信的,”他写道,“几乎每个来到大学的学生都相信或自称相信真理是相对的。”布卢姆坚称,受1960年代的文化影响,经过小学及中学教育阶段的持续灌输,美国精英大学的学生变得倾向于信奉一种并不可靠的东西,那就是在普遍的自然权利和追求良善生活上持有开放态度。“如果对目标或公共善的愿景没有共识,”他发问,“社会契约还可能存在吗?”
布卢姆的文风精英派头十足,但这本书却很普及:它出人意料地成为了里根时期后半段销量最高的学术书籍。布卢姆提出,大学在高学历精英的把控下正在误人子弟、摧毁人们所珍视的社会习俗并腐蚀社会团结的根基。布卢姆大力抨击的、号称无处不在的“文化相对主义”,如今仍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件烦心事。

[美]艾伦·布卢姆 著 战旭英 译 冯克利 校
译林出版社 2011-3
时评界健笔迪内希·德·索萨(Dinesh D'Souza)——此人几乎可以从任何地方找到支持自己世界观的证据——则于1995年著书提出,文化多元主义要为种族主义的延续负责,其理由是它让人们不敢对非裔美国人的文化提出必要的批评。虽然“文化相对主义”这个术语某种程度上已经淡出了公共话语,但右翼对多元文化主义和移民的攻击里仍隐含有类似的批评。在2019年7月的“全国保守主义大会”上出尽风头的法学教授爱米·瓦克斯(Amy Wax)曾表示“不是所有文化都一律平等”并声称“我不惮于使用‘优越(superior)’这个词。人人都想去欧洲白人占主导的国家”。
“文化相对主义”的理念和“政治正确”类似,是一种用以抨击一般意义上的自由派精英的大棒,人文学科教授尤其受其针对。一种说法是,这一危险的理念使得这群人要为诸多社会病负责(病症的数目甚至超过了这群本来就为数不多的人的影响能力)。新近推出《高空之神》(Gods of the Upper Air)一书的查尔斯·金(Charles King)无疑也称得上是教授。在国际事务与政府这个学科里,他的位置略显含混,介于人文和社科之间,以至于我实在不清楚他是否也应该被算进需要为把道德搞得千疮百孔负责的文化相对主义——就像饥饿的毛毛虫在周六所做的那样(《好饿的毛毛虫》是美国著名儿童漫画,其中的毛毛虫以钻洞的方式进食,它周六的食量尤其大,钻的洞也异常多——译注)影响着我们的本科生——负责的那群人里。但《高空之神》是一部群体传记、一部造就了“文化相对主义”的人类学家的智识史,该书某种意义上也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原则提出了辩护。在眼下的环境里,这种努力尤其值得赞赏的地方在于,它使得文化相对主义从其论敌的沙袋这个位置上解脱了出来。该书揭示了文化相对主义诞生的语境——那是人文学科研究的一个特殊时刻,其时代背景是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殖民主义和伪科学种族主义,不幸的是最后这点与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还有一些交集。
文化相对主义的先行者们致力于对抗多个世纪以来的种族主义观念的偏见。18、19世纪的种族理论家提出,人类分为一系列截然不同的种族群体,分别体现着文明的不同阶段。这些范畴构成了一种等级制,令欧洲人及其殖民者感到自己比起在环游世界过程中遇见的其他人类而言是更强大、更成功的。在殖民主义、奴隶制以及对移民的限制为自身寻求辩护之际,种族理论家恰好提供了相应的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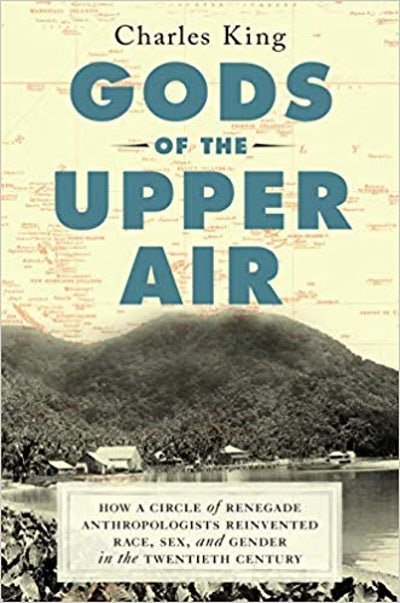
这种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理论建构基于荒唐的逻辑。例如,德国解剖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布鲁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在1775年提出,世界上的人们分为五大种族。在“衣索比亚人”、“亚美利加人”、“蒙古利亚人”和“马来人”之外,布鲁门巴赫的原创性贡献,是给了皮色白亮的欧洲居民“高加索人”这个名字。一个表面上的理由是,布鲁门巴赫接触到了一批私人收藏的骷髅,对其中一名来自高加索山的格鲁吉亚少女的头骨特别中意。鉴于该地距许多学者认定的伊甸园所在地也相当近,布鲁门巴赫据此认为,拥有惊人美貌的“高加索人”出自上帝的精心设计,而别的种族由于离创造的源头较远,不过是人类的较低级形式。

一个多世纪以后的1916年,美国优生学家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出版了《伟大种族的逝去》(The Passing ofthe Great Race)一书,主张改进人类的最好方法就是鼓励培育最为正面的人类特性:精力、创造性、智能以及敢于冒险。格兰特相信,这些品质最突出地体现在北欧人身上——且构成了支持种族主义以及限制南欧移民的根据,在他看来,出于“利他主义价值观”而接受这些移民无异于“将整个国家拖向种族的深渊”。
作为文化相对主义先行者的人类学家们踏入的正是这片深水区。这一群体通常被称作“波亚士主义者”(Boasians),此称谓源自弗兰茨·波亚士(Franz Boas),他们挑战了许多在当时广为接受的种族观念。学生们称生于普鲁士的波亚士为“弗兰茨爸爸”。他于1881年拿到了物理学博士学位,成绩一般般,由于不喜欢这个学科而试图寻求新的挑战。波亚士几乎是听着北极探险的故事长大的,他去了加拿大的巴芬岛,和因纽特人同住。其间,他亲眼目睹了因纽特人是如何采集食物、与配偶和孩童共处、玩游戏乃至于患病的。
令他意外的是,这些人并不是在时间之外的,而是有着私人历史的个体。一名叫西格纳(Signa)的男子是其研究的主要合作者之一,他出生在别处,幼时搬到了科克尔腾村(Kerkerten)。当时该地爆发了白喉病,但波亚士这位“医生先生”却没有帮上什么忙,令当地人深感不满。波亚士意识到了自己知识的局限性,明白了因纽特儿童所受的教育是与其生活方式一脉相承、相互匹配的。最重要的是,他开始视自己的研究对象为真实而完整的人。“我经常扪心自问,我们的‘好社会’比起那些‘野蛮人’来说究竟有哪些优点,我越了解他们的习俗,就越觉得我们没有理由以轻蔑的眼光看待他们,”他写道,“我们不应该对他们的习俗和迷信指指点点,因为‘教养良好’的我们相对而言可能还不如他们。”
然而,波亚士的学术生涯却远远谈不上一帆风顺。他先为1893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工作了一阵子(会上展出的既有费里斯摩天轮,也有来自中途岛及其周边的活生生的土著人),设计了一间人类学展馆。参观者可以现场测量自己的头骨尺寸,体验一下当时颇为流行的颅相学。然而,馆里的测量结果却没能符合颅相学家们的预期:结果表明,美国的黑白混血儿的高度和白人一样;北美印第安人的指纹各具特色;同一社群里的人在头型上极具多元性,甚至于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波亚士据此得出结论,文化偏见让科学家们犯下了错误,乃至于采纳了一些与可观察的数据并不相符的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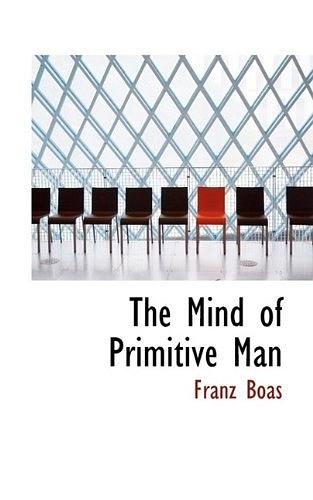
1897年,波亚士终于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正式教员,工资由一名富翁担保。他在1911年的成名之作《原始人的心智》(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里提出,人类历史并不体现为各种族之间的宏大竞争。甚至于当今的种族都不是稳定的,因此它也无法以一种能够清晰定义的方式存在于过去。种族和文明水平也没有关系——假如种族观念本身都不可靠,这种说法还站得住脚吗?此外,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有多个不同的“种族”都曾比欧洲人更为先进。换言之,关键在于历史。
依照金的说法,波亚士“呼吁美国人和西欧人放下对自身之伟大的执念”。许多人干脆无视他的观点,另一些人则有了威胁感。哥伦比亚大学领导层取消了他的本科生课程,以防学生受到此激进思想的影响。不过,波亚士的入门讲座仍然广受欢迎,尤其受女性青睐。尽管她们仍需与学术机构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作斗争,但波亚士的许多高徒如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艾拉·卡拉·德洛利亚(Ella Cara Deloria)和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都追随了波亚士的道路,力图创作出更广泛、更重要的作品,令人类学成为一种鼓励人们反思自身及其社会的途径。
作为一个相对小众的共同体,追随波亚士的人类学家们似乎也预表了“个人的即是政治的”这一后来的理念。《高空之神》里也写到了三角恋乃至于更具雄心的多角恋,其开头就谈到了米德和本尼迪克特的同性恋情。读者是否喜欢这种写法或许是个口味的问题——我就比较青睐短小精悍的、对已出版著作的总结——但亲密关系确实为故事增添了色彩,且对所完成的工作本身而言也是重要的。例如,本尼迪克特在研究墨西哥的祖尼人(Zuñi)时就注意到了跨性别现象(gender-crossing)——即男性采纳女性的着装和社会角色——并意识到依照自己社会的标准而言是“异类”的做法,在别的社会里可能是正常的,哪怕还不是稀松平常。文化相对主义者要挑战的不仅是种族,也还有诸如性别这样的社会范畴。

[美]玛格丽特·米德 著 周晓虹/李姚军/刘婧 译
商务印书馆 2010-10
在米德这一边,其成名作《萨摩亚人的成年》试图表明,青年人的焦虑并不是自然的。在马努斯岛(Island of Manus)上,米德花了九个月时间,过了一段迥然不同于以往的生活并观察到:它并不强调依恋(attachment),因此也较少产生妒忌。米德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和女人和女孩同住的,据此她得出结论,认为萨摩亚青年较少焦虑的原因在于当地的性生活总体上也是平和的。感情出轨有可能会被发现以及惩治,但也易于得到谅解。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社会里的每个人都彬彬有礼,而只是因为这个社会本身就不同于西方。
《萨摩亚人的成年》与许多有波亚士风格的作品相似,在许多方面关涉到作者自身及其所处的社会,其开端和结尾都对美国进行了反思。“我们的小孩要面对一大堆道德标准,”米德提出,“但萨摩亚人的小孩不会有这些两难。性是一件自然、愉快的事。性自由遭到滥用的可能方式仅有一种,那就是对社会地位的考量。”关键不在于萨摩亚社会更优越,它只是不同而已。“体面、谦和、得当的举止以及对一定伦理标准的持守,都是普遍的,但这几样东西的具体内容则不是普遍的,”波亚士在书的前言里如是说,“我们将许多东西归诸人性,不过是对自身文明所受限制的反应而已。”
波亚士的追随者也犯过一些错误。其研究合作者的说法有时是彼此矛盾的,而人类学家也难免有过度概括之嫌。米德对萨摩亚青年性行为的解读就被批评为太过宽泛。波亚士的追随者同样也会受偏见的影响。波亚士自己就曾认为非裔美国人有某些缺陷,他的学生佐拉·尼尔·赫斯顿对此提出了反对:她对佛罗里达州黑人社群的研究(该研究构成了她后来的经典小说《凝望上帝》的蓝本)因其承认研究对象与角色具有完全的人性而受到肯定。但即便如此,她也留意到,自己的研究经常被认为是在谈论“黑人”(Negroes)的特殊性和病理性,而诸如萨摩亚人这样更加边远且号称更“原始”的人群则被视为是全人类的某种反面教材。

她们的著作销路很好,并逐渐开始对大众意识发挥影响。在物质至上的1920年代,一些人开始认为所谓的原始文化其实拥有现代社会所缺乏的一些智慧。当时兴起了一股刻意让美国白人青年模仿“印第安”习俗的复古风潮,包括野外露营、成立男子童军(Boy Scouts)和篝火女孩(Camp Fire Girls)等,而体育队伍也开始热衷于使用美洲原住民的吉祥物,这一切令波亚士的学生、祖先是扬克顿达科塔族的艾拉·卡拉·德洛利亚十分惊愕。“西方人的征服才刚过去几十年,就出现了一种新常态,美国白人父母纷纷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把自家孩子打扮成了那些其先祖曾绞尽脑汁加以抹除的人。”金写道。
1961年《萨摩亚人的成年》再版时,米德在前言里澄清称,她并不主张“回归原始状态”。她还补充道,自己并不想生活在萨摩亚:“我想在纽约生活并且把我在萨摩亚学到的东西整理出版。”文化相对主义这一术语最初于1934年出现在本尼迪克特《文化的模式》一书里,被视作一种思考世界的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有不同的解决人之为人的问题的渠道,如本尼迪克特所言,人类学家“必须避免去权衡谁高谁低”。具备接纳他人视角的能力,乃是一项专业责任。
金在《高空之神》一书的开端处表示,自己的书“不是要教人宽容”。这本书里确实也没有课后专题节目的耳提面命。但其中的主人公和英雄是一体的,无论其有多少瑕疵,且他们也再三呼吁宽容:接受人类的差异,对不同生活方式的研究令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在人类可能性的范围内,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或者恐同都不是人类本性的要求。“文化相对主义是一种关于人类社会的理论,但同时也是人生的用户指南,”金总结道,“它旨在让我们的道德感受力更加鲜活,而不是要破坏它。”
对波亚士的追随者而言,文化相对主义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对良善生活的追求。通过澄清人之为人的多种方式,以及不将凌驾于他人的优越性视为理所当然,本尼迪克特希望世人可以这样达到“更现实的社会信念”。尽管其研究也会犯错,但坚信世界应当建立在事实和观察而非文化偏见的基础上的,也正是这群波亚士的同道。最核心的理念是——或许可以公平地将之归于大部分的人文学科教授——拒斥种族中心主义,承认一切人本质上都具有人性。它重视谦卑、反思而非傲慢。颇为讽刺的是,如今的文化相对主义辩护者很少,批评者却很多,最反对它的人恰恰是最需要了解它的核心洞见的人。
(翻译:林达)
来源:新共和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