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去摔跤。血、汗和战斗,那才是我。”我回头看着七岁的女儿,当时我们正准备离开有着各种丛林游戏的游乐场。“是什么让你想起这个的?”我追问道。我的孩子从未表现出对血和汗水的迷恋,战斗在她以往的解读中是一种动口不动手的行为。我们走进一家生鲜超市,女儿跳上一个带轮子的购物车,这样就可以把抬起腿滑行,她反问道:“这是因为——为什么男孩子……像男孩子?是什么让他们成为那个样子的?”
当时,我刚刚看完兰迪·赫特·爱泼斯坦(Randi Hutter Epstein)的《唤醒:荷尔蒙的历史以及它们是如何控制一切的》(Aroused: A History of Hormones and How They Control Just About Everything)。这是一本由诺顿(Norton)出版社发行的平装书,通俗易懂且引人入胜。于是,在超市挑选李子的老太太听到一位母亲向女儿解释说:“好吧,那是雄性激素的原因。当胚胎是XY时,它就会对母体供应的血液中的激素做出反应,告诉它应该长出睾丸和阴茎——晚餐你想吃红薯吗?——后来,其他的激素也开始发挥作用。”
我直到很晚才接触到荷尔蒙这个概念。今天早些时候,我面前是堆积如山的文件和笔记,洗过的衣服摊在沙发上还没叠。我想在午餐时吃一磅奶酪,有些事情我刚想起来就马上忘记了,然后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简单地说,我有经前综合症(Premenstrual syndrome,PMS)。我开始计算日子,等待月经来临时那种几近疯狂的快感:哇,终于解放了!哇,我又精力充沛了!阴霾一扫而光,我又变得思路清晰。我再次专注于各种事情——日程表、电视剧情节、做家务的顺序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于荷尔蒙的变化。两个星期后,我的丈夫和孩子将惊叹于我如何用吸尘器将客厅的地毯吸得一尘不染,将浴缸擦得闪闪发光,并且按照作者的字母顺序和主题,将书整理得井井有条。这是排卵期。然后,我将再次陷入经前综合症。荷尔蒙,它们似乎控制着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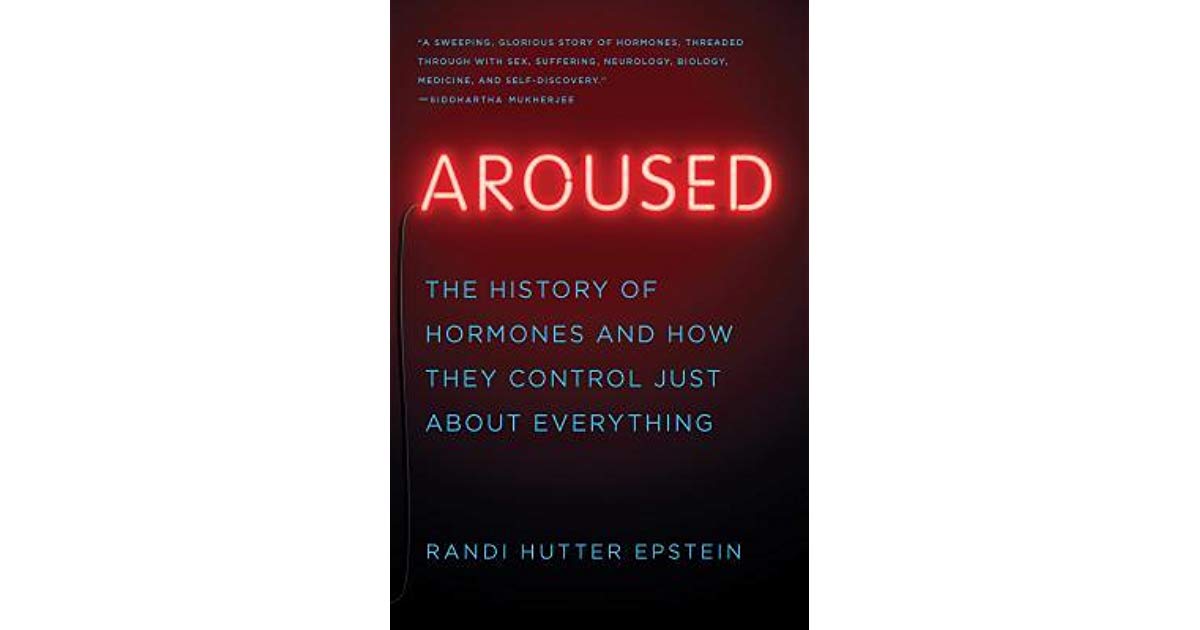
这本书的故事始于1900年前后的世纪之交,当时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发现了荷尔蒙以及它们与神经递质的区别:如果将我们的神经系统比喻为互相连接的高速公路,那么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就是爱泼斯坦称作的“你的无线网络”。这本书真正成功的地方,是对社会规范和性别政治如何与科学新发现互相作用做出了尖锐的调查。路易斯·伯曼(Louis Berman)博士在1920年代提出了一个新领域,他称之为"心理-内分泌学”(Psycho-Endocrinology)。之后,他写了一本名为《决定人格的腺体》(The Glands Regulating Personality)的书,他在书中指出,“月经周期不规律的女性”会更具侵略性、强势,甚至更具进取心和开拓意识——简而言之,(她们)的卵巢已经男性化了。“想想吧:如果一个女人每个月都像上了发条一样流血不止,怎么还能有进取心!”
历史上有许多与荷尔蒙相关的让人哭笑不得的案例。例如,1924年,来自波士顿精神病医院(确有此医院)的两位医生哈罗德·赫伯特(Harold Hulbert)和卡尔·鲍曼(Karl Bowman)被召去对两名青少年——纳森·里波路(Nathan Leopold)和理查德·娄伯(Richard Loeb)——进行体检。这两名青少年正在因外界所称的“世纪犯罪”而接受审判,他们绑架、虐待并谋杀了一名14岁的男孩。该案件除了道德堕落之外,并没有明显的动机。但由于案件所处的时代,恰好也是内分泌学说甚嚣尘上的时期,所以震惊的公众和一个名为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的辩护律师试图在这一新领域寻求答案。体检共进行了8天,很多记者蹲守在监狱外。最后,赫伯特医生宣布娄伯患有”腺综合症“,而里波路则存在松果体钙化症状,这导致了他性欲过剩。他们采用的主要检查工具是代谢测量仪和X光机。法官最后裁定,内分泌专家的判断并不能改变判决结果,谋杀就是谋杀,犯罪分子不能从生物化学方面寻求赦免。
这仍是一个让我们的社会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否可以原谅精神病患者的某些行为?是否犯罪行为或多或少可以理解?许多专家讨论了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泰德·邦迪(Ted Bundy)的性格——他是一个典型的精神病患者吗?——并且觉得他们找到了一个关键问题。但确实如此吗?它到底仅仅是语义学的问题,还是有关于科学、治疗和惩罚的重要问题?当然,有趣的地方在于,荷尔蒙的发现如何引发了这一轮辩论?

爱泼斯坦书中最吸引人的一个章节是关于一个1956年出生的名叫布莱恩·沙利文(Brian Sullivan)的婴儿的故事。这个婴儿在最早的医院记录中被称为“雌雄同体”,他似乎同时拥有阴茎和阴道。在他18个月大的时候,医生进行了一次探索性手术,按照当今的标准来看,这个手术非常激进。医生通过手术发现孩子腹腔内有阴道、子宫和卵巢。在没有征求布莱恩父母意见的情况下,医生直接切除了孩子的阴茎,并嘱咐父母将其按照女孩来抚养。布莱恩变成了邦妮(Bonnie),“她”的衣柜,甚至整个房间的颜色都换成了传统的“女孩的粉色”。而邦妮很快就停止说话了。正如爱泼斯坦提醒我们的那样,对于出生时有非典型生殖器的人来说,那是一段黑暗的时期。当时,人们对于天生的性别认同背后的复杂过程知之甚少。实际上,发现孩子体内有子宫并不意味着也发现了孩子的性别认同。后来,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怀孕期间,如果雌激素或睾酮进入血流中,可能会部分影响性别表征。因此,无论是什么影响了布莱恩的生殖器发育,这种物质也可能影响到了他或她的自我性别认同。邦妮的人生在8岁时再次被医学所改变,当时她通过手术切除了腹部的生殖器组织。她被告知手术是为了治疗她的“胃痛”,尽管她并没觉得自己胃疼。1964年,邦妮被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收治入院,在那里,摄影师拍摄了她赤裸的身体,她还忍受了术前骨盆检查。“检查者将手指伸进她的阴道和肛门,她为此感到耻辱,觉得自己像个怪胎。”很多年后,爱泼斯坦见到了邦妮,她当时叫做“博”(Bo)。很多年之后,博终于看到了自己的病历,发现自己在忍受了虐待后,被粗野地标记为“雌雄同体”。再后来,她创立了“北美双性人社团”,希望与遭受类似虐待和野蛮干预、并因此陷入孤独和困惑的人建立联系。她还想告诉医生,该如何更好地治疗双性人儿童。很快,她的信箱里塞满了来自孤独和沮丧的双性人的信件。一个支持网络由此开始发展起来。
这本书也展示了激素和外科治疗如何强化了二元性别系统。 但是,“这些数据实际上显示出了更加复杂的人性。” 克莉丝汀·乔根森(Christine Jorgensen)在1926年出生时还是乔治·乔根森(George Jorgensen)。26岁时,乔根森在手术和荷尔蒙的帮助下,从男性变性为女性。《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在1956年报道了这个故事,不久之后,实施手术的丹麦医生收到了大量的(变性)帮助请求。美国人则涌向专注于性别和性行为的内分泌学家哈利·本杰明(Harry Benjamin)博士寻求帮助,正是本杰明提出胎儿大脑对性别的天生认同依赖于母亲子宫内的荷尔蒙,他还进一步写了《变性现象》(The Transsexual Phenomenon)一书(变性人是一个已经过时的词,后来被“跨性别者”一词所取代)。本杰明将寻求手术的患者介绍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性别认同诊所。爱泼斯坦很好地驾驭了这个主题,将重点放在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上。“一个人的变性认同原因可能与另一个人的并不一样。”她写道。

最后,这本书指出,虽然我们对荷尔蒙有了更多了解,但绝对不是全部。庸医、骗子、粗心大意的研究人员,以及希望从新发现中获得快速回报的人纷纷登场。在几乎每一个章节中,爱泼斯坦都强调,关于维持人体运行的最新科学信息很容易被商业利用。荷尔蒙尤其是薄弱环节,因为它们几乎可以调节人体的每个主要过程:从生长到新陈代谢、从睡眠周期到性生活、从养育孩子到免疫系统、从压力到哺乳……从1920年代的“复活性输精管切除术”和“肾上腺素栓剂”,到当今将催产素补充剂作为性兴奋和催情增强剂出售(尽管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荷尔蒙可以通过舌下给药的方式代谢,且荷尔蒙的精确功能也尚不明确),但商业公司仍急不可待地想将新科学研究转换为不义之财,就像我们容易受到善意医生的伤害一样,我们也很难抗拒对治疗和治愈的渴望。
这本书警告说,荷尔蒙就像无尽海洋中的一小滴水,以复杂的方式与神经细胞和人体内的其他化学物质相互作用。我们不仅需要了解更多的知识,还需要对这些知识进行精确的测试。我们可能已经远离了那些黑暗的日子:当“肥胖的新娘”布兰奇·格雷(Blanche Grey)被放在纽约Dime博物馆(注:美国十九世纪末在纽约下层社会非常流行的一家收费低廉的娱乐场所)展览——她可能存在某种类型的甲状腺或垂体功能障碍;或是博·劳伦特(Bo Laurent)所经历的被迫接受阴茎切除的日子,但当今社会仍在努力接受性别多样化这样一个现实。我80岁的父亲说,自己对理解不同的性取向或变性身份没有任何困难,但“非二元性别”(指那些超越传统意义上的二元划分,不单纯属于男性或女性的自我性别认同)实在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与此同时,在我女儿所生长的这个时代,人们可以用自己感觉最合适的代词来指代自己,所以我女儿可能会惊讶地知道,人们曾经为了适应性别划分来调整自己的性别。我和女儿正在读《银河的裂缝》,这是《时间的皱纹》的续集,作者马德琳·英格(Madeleine L'Engle)介绍了一种更先进的物种,它们通过“kything”相互交流,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另一个同类的内心世界。这让我觉得这是对人类性别认同扩展定义的恰当比喻,因为科学可以赶上人的体验。在最好情况下,生物科学可以使我们加深理解,并相互帮助,将我们的差异视为桥梁,而不是障碍。
书里又谈到了更年期。 去年12月,《纽约》杂志的一期封面文章惊呼“更年期精神病”。 《四十五岁,女性和幻听》(45, female, and hearing voices)这篇文章研究了绝经期间荷尔蒙的波动——特别是雌激素下降——和迟发性精神分裂症之间的联系。作者承认,自己最初不愿意接手这个主题(她不想被指责助推了疯狂的更年期女性的形象)。
但是,她解释说,很明显女性再次成为研究不足的对象:激素如何影响女性的思想和身体很少被人理解,因为很少有人研究。我已经44岁了,虽然尚未进入更年期,但也开始注意到微小的变化。我每个月都还来月经,但我觉得自己的情绪有点不那么稳定,有点难以预测。我注意到自己越来越烦躁不安,每天需要进行高强度的体育锻炼才能平静下来,并集中精力。我注意到自己的经前综合症症状减轻了,但在其他时间,那些忧郁情绪和情绪爆发又会出现。当然,我对更年期和精神分裂症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感到震惊和着迷。我想,肯定发生了什么,请让他们找到原因。最近,一篇关于认知衰退和更年期的文章在Facebook上广为传播,我赶紧记下了文章的要点,希望能够收集到一些技巧,以减少患上由性别决定的痴呆症的几率。我还把作家达西·斯坦克(Darcey Steinke)关于她自己更年期经验的新书《盘点日记》(Flash Count Diary)加入了立刻阅读清单。
在关于更年期的章节中,爱泼斯坦的机智得到了充分展现:“有些女性会越过整个过程:她们停经了,仅此而已。没有不规律的体温波动,没有情绪波动,没有脑雾(注:指大脑难以形成清晰思维和记忆的现象),性欲一如既往的强烈。对于那些女人来说,我们这些其他人一定看起来像脾气古怪的婊子。”
我知道我的大脑受荷尔蒙的影响有多深,不仅仅是因为每月身体的剧烈变化和症状,还因为我经历了如此痛苦的孕期,那些记忆永远不会离开我的脑海。怀孕只有六个星期的时候,我就会在太阳落山时哭泣。到了八、九个星期,我的子宫开始收缩,让我喘不过气来,还出现了让人疼痛难忍的皮疹。
孕期的很多时间里,我都在严重抑郁中度过。而且我知道,即使在看到漂亮的孩子之后,我也不愿再经历怀孕了。所以,我预计自己会成为那群脾气古怪的婊子中的一员。
我也想获得与更年期相关的知识。问题是各种数据存在冲突。雌激素的下降是否会使女性更容易患心脏病、中风、痴呆、骨质疏松症,还是情况更加复杂?爱泼斯坦透露,研究显示,长期激素替代疗法没有任何益处,也就是说,这些类型的疾病没有减少。然而,她确实提供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为缓解更年期症状而进行为期数年的激素治疗不太可能对你造成伤害。
我们不得不依靠目前已有的研究摸索前进。如果这点不令人欣慰的话,爱泼斯坦对这个主题的文章肯定对我们有帮助。我感觉像有一位朋友指引我穿过我自己身体内的可怕水域。与此同时,我得让女儿了解雌激素。我当然希望,她能感谢自己体内大量存储着的神秘且至关重要的荷尔蒙。
本文作者Leslie Kendall Dye是一名自由撰稿人,也从事演艺事业,曾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上发表文章。
(翻译:王涛)
来源:洛杉矶书评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