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夏天,我从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一所公立高中毕业,前往东北部的耶鲁大学就读。然后我花了将近15年的时间在不同的大学学习——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最后又回到了耶鲁法学院——在这些大学我获得了一系列的学位。如今,我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教书,我的学生与年轻时的我惊人地相似:他们大多都是精英父母和一流大学教育下的天之骄子。如今,我又把从老师那学来的经验传授给他们。不论是他们,还是我,都把我们的成功和社会地位归功于择优制度(meritocracy,也可译为精英制度——译注)。
20年前,当我开始写关于经济不平等的文章时,择优制度似乎更像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社会制度。择优制度的早期支持者们提倡社会的流动性。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耶鲁大学的校长小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将择优录取制度引入大学,意在打破世袭的精英制度。耶鲁大学的校友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他们的子孙有着与生俱来的权利,可以跟随他们的脚步进入耶鲁大学;而现在,耶鲁大学的学生是根据成绩,而不是教养获得入学资格。择优制度一度让才华横溢、勤奋工作的外来者,取代了洋洋自得的内部人士。
今天的才智精英仍然声称,人才要通过开放渠道的努力奋斗才能获得成功。然而事实上,如今的择优制度把几乎所有人都排除出了他们有限的精英圈子外。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学生来自收入分配前1%的家庭的数量要超过收入分配后60%的家庭。优先录取(legacy preferences,指美国一些精英私立大学会优先照顾校友后代的大学申请——译注)、裙带关系和赤裸裸的欺诈依然是富人家庭的大学申请者的腐败优势。而这种对于财富的倾向其实可以追溯到择优制度本身。平均而言,父母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孩子在SAT考试(美国中学生的大学入学能力考试——译注)中的得分,要比父母年收入在4万至6万美元之间的孩子高出250分左右。而来自最贫穷的三分之一家庭的200名儿童中,只有大约1人的SAT成绩达到了耶鲁大学的中位数。与此同时,业界顶尖的银行和律师事务所,以及其他高薪职位,几乎只从那些精英大学招聘学生。
时至今日,勤奋工作的外来者也许不再能享受真正平等的机会了。据一项社会调查显示,出生在社会最贫穷的五分之一家庭的100个孩子中,只有一个会进入前5%,而出生在中间五分之一家庭的50个孩子中,只有不到一个会进入前5%。社会经济的流动性也在下降——自上世纪中叶以来,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比父母收入更高的几率已经下降了一半以上——而且中产阶级孩子的收入下降的幅度要大于贫困阶层。而择优制度只会将这种现象归咎于他们未能达到标准,这便又在损害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种道德侮辱。
同时,公众对经济不平等的愤怒往往也针对精英机构。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显示,近五分之三的共和党人认为高等院校对美国有害。今年早些时候的高等院校入学丑闻(2019年3月份美国司法部起诉了美国迄今为止最大一起知名高校入学造假案——译注)引发了公众广泛而强烈的不满与愤怒。这种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事实。对裙带关系和其他不光彩的富人优势的愤慨,却含蓄地强调了择优制度的理想价值。然而,择优制度本身有着更大的问题——它正在削弱美国梦。择优制度创造了一种竞争的假象,即使每个人都按规则行事,也只有富人才能赢。

不过话说回来,富人究竟赢得了什么?即使作为择优制度的受益者,他们如今也因这一制度的要求而经历着痛苦。择优制度对富人的诱惑和对普通人的排斥是一样的,因为那些想要爬到金字塔顶端的人,必须用昂贵的教育和拼命的工作来获得回报。

没有人应该为富人哀悼,但择优制度对他们造成的伤害也确实存在。通过探究择优制度如何损害精英阶层的利益,我们可以试着寻找应对之道。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减少社会不平等需要加重富裕阶层的负担。但择优制度的不平等实质上对于任何人都无脾益,而摆脱择优制度陷阱的束缚将会使几乎所有人受益。
这些精英往往在童年时期就要面对来自择优制度的压力。尽管父母有时可能并不情愿,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让子女接受并非由游戏和实验主导的教育,他们不断地积累才能,抑或者说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以便进入一所精英大学,并最终成为职场精英。在纽约、波士顿和旧金山这样的城市,富裕家庭的父母通常会申请10所幼儿园,并进行一系列的论文、评估和面试——而所有这些都是为评估4岁的儿童而设计的。而接下来,申请优秀的初中和高中时又会不断重复这些经历。曾经贵族家庭的孩子得意于他们的特权生活,而现在精英制度下的孩子却要估算自己的未来——通过精心安排的自我展示,以相似的野心、希望和担忧,来规划他们的未来。
而这也是那些学校鼓励孩子所做的事情。例如,美国东北部的一所精英小学,老师会布置一个“每日问题”,不论学生们有没有充足的时间,都必须在放学回家之前解决它。而这项练习的目的,便是训练五年级的学生是否能通过多任务处理,或者牺牲课间休息时间来多挤出几分钟额外的时间来完成作业。
这样严苛的要求的确需要孩子们付出很多。如今,顶尖的初中和高中的学生每晚通常要用三到五个小时的时间来完成家庭作业。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的流行病学家警告称,学生普遍存在因学业而导致的睡眠不足。同时,富裕学生吸毒和酗酒的比率比贫困学生要高。他们的焦虑和抑郁程度是全国同龄人的三倍之多。在最近一项关于硅谷一所高中的研究中发现,80%的学生表现出中度至重度的焦虑症状,54%的学生表现出中度至重度的抑郁症状。
然而,这些学生确实有理由如此逼迫自己。就在几十年前,美国精英大学的录取率有30%,而如今录取率则不足10%。在某些院校,这种转变甚至更为显著:芝加哥大学在1995年录取了71%的申请者,但是在2019年,录取率只有不到6%。
而当他们进入职场时,竞争往往会变得更加激烈,因为只有通过竞争才能抓住机会成为职场精英。一个人在选择工作时根本无从考虑自己的兴趣或激情,因为财富和地位取决于他的人力资本。相反,他必须把工作当作一个从自身人力资本中榨取价值的机会,尤其是如果他想要一份足够的收入,并足以支撑他的孩子接受符合自身精英地位教育。他必须把自己奉献给一个相对狭窄的高收入阶层工作,集中在金融、管理、法律和医学方面。贵族曾一度认为自己是一个休闲阶层,而择优制度下的精英却在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工作着。

1962年,当时许多精英律师的收入约为今天的三分之一,美国律师协会可以自信地宣称,“普通律师每年大约有1300个小时的收费工作时间。”相比之下,在2000年,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可以同样自信地宣称,2400小时的计费工时“如果管理得当”是“合理的”, 这是“成为精英律师必要条件”的委婉说法。但是律师所有的工作时间并不都是可以计费的,所以2400小时的计费工时也就基本意味着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8点,每周工作六天,没有假期或病假。而在金融领域,从19世纪20世纪中叶,“银行的工作时间”(bankers' hours)指的是银行早上10点到下午3点的工作时间,到后来被普遍用于形容清闲的工作,而现在则被讽刺地称为“银行家的9-5”,即从早上9点第二天早上5点。精英经理人曾经是“组织者”(organization men),在一个资历重于业绩的企业等级制度中,他们被终身雇佣。而在今天,一个人想要在组织结构中爬得越高,他就越需要努力工作。比如,美国亚马逊公司的“领导原则”就要求管理者要“坚持不懈地执行高标准” 的同时“交付成果”。 公司告诉经理们,当他们在工作中“碰壁”时,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翻过这堵墙”。
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的美国人在调查中表示,他们更希望每周少工作25小时(平均来讲)。而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工作让他们陷入了“时间饥荒”(time famine)。 200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时间饥荒”影响了他们与配偶和孩子建立亲密的关系,甚至妨碍了他们过上满意性生活的能力。在哈佛商学院最近针对企业高管进行的一项调查中,一名受访者自豪地表示:“晚上陪孩子的10分钟,比花在工作上的10分钟要好上100万倍。”只有十分钟!
优雅地或至少是冷酷地承受这些“时间饥荒”的能力,已经是择优制度下成功的一个标准。美国社会学家亚莉·罗素·霍奇查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曾在她的著作《时间困扰》(The Time Bind)中采访了大公司的一些高层管理人员,她发现,充满抱负和奉献精神的经理人往往面临着“末位淘汰”的压力:“有些人因此发火,变得很奇怪,因为他们一直在工作……而顶尖的人则更聪明,工作很疯狂的同时不会发火。他们能够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保持好家庭生活与工作的平衡。他们赢得了比赛。”
一个从自身的人力资本中榨取收入和社会地位的人,毫不夸张地说,是把自己置于他人的支配之下——耗尽了自己。精英学生极度害怕失败,渴望传统意义上的成功,即使他们看穿了所谓的“金钱”和“炫耀”,甚至公开地嘲笑它们。对于精英员工来说,他们越来越难以通过工作追求真正的激情或意义。择优制度将整代人困在对卑微的恐惧和不真实的野心之中:总是饥饿,却永远找不到、甚至不知道正确的食物何在。
精英阶层不应该——也无权得到被排除在特权阶层之外普通人的同情,但忽视择优制度对他们的压迫也是谬妄无稽的。富人主导社会的发展也不是轻松写意的简单事情。曾经战胜贵族统治不平等的常见论点,并不适用于基于努力和回报的经济体系。每周不懈工作上百小时的银行家,理应免于不劳而获的指控。那么,更好的办法是让富人相信,他们的工作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他们可能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难以说服。随着精英在择优制度的陷阱中越陷越深,富人也开始反对这一主流体系。关于平衡工作和生活呼声越来越高。约三分之二的精英员工表示,如果新工作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他们会拒绝升职。当拉里·克拉默(Larry Kramer)还是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院长时,他曾告诫毕业生,顶尖律所的律师正陷入一个似乎永无止境的循环:更高的薪水需要更多的工作时间来支持,而更长的工作时间需要更高的薪水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他哀叹道,这个体系为谁的利益服务?真的有人想要吗?
但是,要摆脱择优制度的陷阱并非易事。精英阶层自然而然地会抵制那些可能损害他们特权的政策。但是,如果你不能剥削自己,不能让自己的内心生活变得贫穷,就不可能靠自己的人力资本致富,而那些希望鱼与熊掌兼得的精英人士不过是在欺骗自己。我们应当建立一个让更多的人能够获得良好教育和工作的社会——如此而言,登上社会阶级的最高层也许就不那么重要了——而这,也许是缓解目前驱使精英阶层固守自身地位压力的唯一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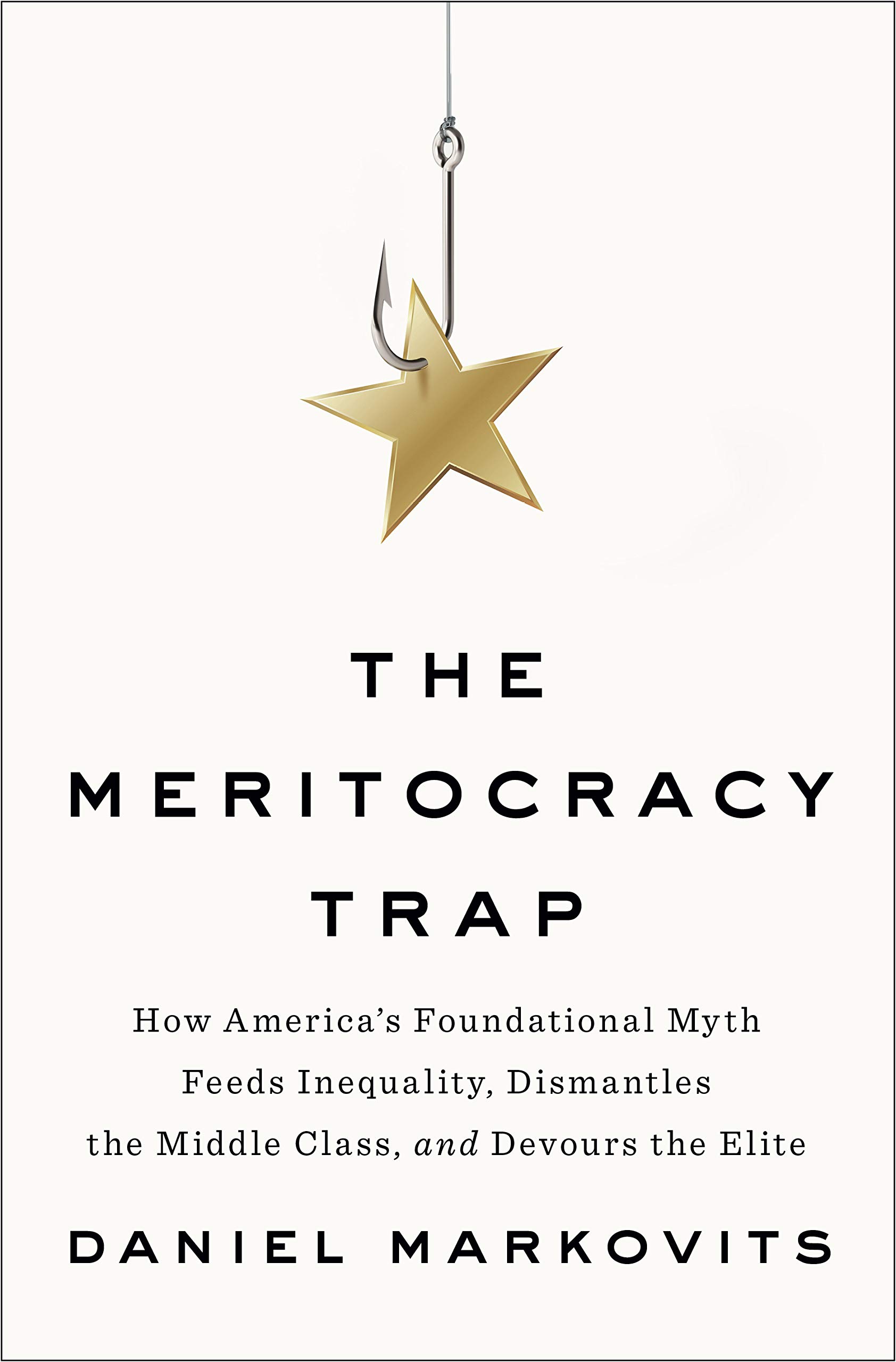
那么,要怎么做呢?首先,教育必须要变得更加包容和开放,因为教育的优质资源往往集中在那些富裕家庭中训练有素的孩子身上。除非私立学校和大学中至少有一半的学生来自收入分配中最低的三分之二的家庭,否则它们就应该失去作为大学的免税资格。而政府的公共补贴应该鼓励学校通过扩大招生来满足这一要求。
与此同时,政府应该改革政策,支持那些缺乏专业培训或高等学位的普通工人。例如,卫生保健系统应该更多地强调公共卫生、预防保健和其他主要由护士从业人员可以胜任的措施,而不是那些需要专业医生的高科技治疗方式。法律体系应该部署“法律技术人员”——不是所有地方都需要有法学博士学位,比如房地产交易、简单的遗嘱,甚至是毫无争议的离婚案件。在金融业中,限制外部金融项目,推动地区性小型银行将工作岗位转移给中等技能人员。而管理人员应该接受将控制权分散到最高管理层之外的做法,让公司中的其他人也能拥有适当的权力。
而克服择优制度不平等的主要障碍不是技术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如今这一情况引起的不满和普遍的悲观情绪,已经让人们近乎绝望。美国政治学家杰弗里·A·温特斯(Jeffrey A. Winters)曾在他的著作《寡头政治》(Oligarchy)中考察了从古典时期到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并且记录了将收入和财富集中在少数精英阶层的社会最终发展。在几乎每一个例子中,这种不平等的瓦解都伴随着社会的崩溃,比如军事失败(如罗马帝国)或革命(如法国和俄国)。
然而,我们仍有理由怀着希望。历史确实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脉络,表明美国正有序地从高度不平等中走出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在应对大萧条时采取了罗斯福新政,最终建立起了世纪中叶的中产阶级。其中至关重要的是,政府再分配并不是这一政策中的主要动力。罗斯福新政所建立的广泛共享的经济繁荣,主要来自于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而且通过像《美国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那样大幅扩大受教育的机会,将中等技能的中产阶级工人置于生产的中心,从而促进了不同社会阶级在经济上的平等发展。
这些政策的改良版本在今天仍然可用:教育公平的重新扩张和对中产阶级工作的重新重视可以相互促进;精英阶层用可以接受的收入和地位,换来属于自己的闲暇时间;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可以重新获得收入和地位,重新成为美国社会生活的中心。
重建一个民主经济秩序的过程困难重重。但是经济民主所带来的好处——就是让每个人的努力都有回报。无所作为的后果只能是暴力与崩溃,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尽力而为。
本文改编自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尼尔·马尔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即将出版的新书《择优制度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
(翻译:张海宁)
来源:大西洋月刊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