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在其犀利且引人入胜的生态批评著作《大紊乱》(The Great Derangement)中指出:尽管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气候危机是人为引发的,但是这一点在文学作品中尚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小说家在围绕气候变化这一主题进行创作时,大多采取的是推理小说的形式(高希援引了詹姆斯·巴拉德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两位作家,称他们为新兴分支流派“气候变化小说”的先驱),抑或像伊恩·麦克尤恩的讽刺小说《追日》那样的荒诞喜剧。高希认为,在“严肃小说的殿堂”之中(这里指现实主义传统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小说),几乎没有气候变化小说的一席之地。
在他看来,气候变化小说的匮乏或许可以通过其最初的起源来解释。现代小说和气候变化一样,本质上都是工业化的产物。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得益于高碳经济和殖民主义对全球资源的剥削碳化以及殖民主义对全球资源的开发,图书印刷成本大大降低,同时人们的识字率不断提升,闲暇时间也越来越多,这一系列进步催生出了大量的读者群体。为满足当时旺盛的阅读需求,现代小说应运而生。这些社会和技术的发展使那些值得讲述的故事发生了转变。高希说:“正是在人类活动改变地球大气层的时期,文学创造才从根本上开始以人类为中心。”
气候变化与现代主体性在人类世范畴下相统一,而二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文学小说中最为显著,因为小说对偶然性很包容(高希顺便指出,概率论的数学理论与小说大致是同时诞生的)。随着宗教宿命论在世俗世界的破灭,小说人物被赋予了选择的自由,然后便拥有了心理深度。人们开始觉得命运掌控在自己手中,文学也开始不再关注英雄或神明的故事,转而关注起日常生活中个人的庸常经历。小说家的工作就是把那些我们后来称之为“情节”的元素组织得既真实可信又难以预料。
重新思考现实主义
高希认为,作为现实主义小说(或者现实主义的小说)的两个指标,个人自主性与不可能性之间的微妙平衡近来已经走向了瓦解。气候变化是“不可能”的,因为气候事件早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尽管我们似乎仍然不愿意正视这一层现实:每场飓风似乎都比以往更强劲,每年夏天的高温似乎都在刷新历史记录,号称“史无前例”的洪水的前例往往又不计其数。高希说,“好像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它将由一系列事件来定义,而这些事件以我们目前的常态来看是极不可能发生的。”因此,小说无法应对气候变化既是一个代表性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就好比我们所处的地球变成了一个文学批评家,讥讽着福楼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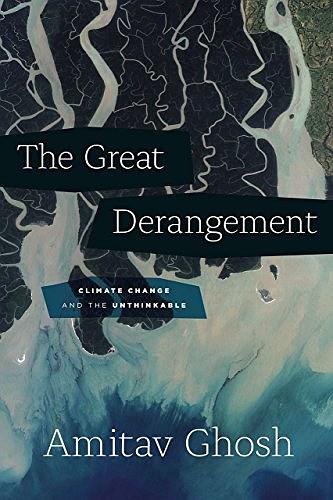
高希在新书中透露,他长期以来都在探究这些问题:个人生活与全球人口变化的关系、殖民主义的遗产以及气候问题。他2000年出版的小说《玻璃宫殿》(The Glass Palace)部分背景设定在缅甸仁安羌的油田。早在19世纪,仁安羌就是缅甸的石油生产中心,在西方殖民者试图对该产业进行“现代化”以及进一步垄断之前就已开始运作。

2004年出版的《饥饿的潮水》(The Hungry Tide)是一项关于生态退化的研究,背景设定在孟加拉湾红树林茂盛和水系发达的“潮汐之乡”孙德尔本斯。小说主人公皮娅·罗伊是一位孟加拉裔美国生物学家,来孙德尔本斯研究伊洛瓦底江海豚的生命周期。在研究过程中,她渐渐发觉本土知识比现代化的热情更为重要。皮娅是在与当地一位名叫福基尔的渔夫交往的过程中领悟到这一点的。在小说的高潮部分,为了在一场恶劣的暴风雨中解救皮娅,福基尔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高希新书《枪岛》(Gun Island)回归孙德尔本斯,从情节上来说算是《饥饿的潮水》的续作。从为人类和动物种群以及小说的未来所带来的影响来看,这部作品也标志着他通过小说适应气候变化最持久的尝试。这次尝试所取得的部分成功恰恰证明了突破故事的结构和思维习惯有多么困难。高希曾在《大紊乱》一书中指出,这些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试图证明的现象之产物。
《枪岛》的故事发生在《饥饿的潮水》设定之后的几年,叙述者是迪纳塔·迪恩·达塔,一个珍本书商,成长于加尔各答,但现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布鲁克林(和高希自身的经历很像)。他受一位亲戚之托,到孙德尔本斯去调查邦杜基·萨德格尔的故事(邦杜基·萨德格尔是孟加拉民间故事中一个失踪的枪支贩)。枪支贩的传说与孙德尔本斯当地的一座圣陵有关,由一个船夫家族照管。他们通过口头诗歌的形式将这个传说沿袭下来,不过诗歌的大部分内容都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被遗忘了。
从设定来看,高希这部新作是一个冒险故事,而他则大胆运用这一体裁最俗套的那些套路:一个老学究式的叙述者受命破解一个文学谜题,却不得已“上演”了一出动作片的戏码。迪恩像丹·布朗小说中经典桥段所描述的那样遇见了一条蛇,随后他回忆道:“真不敢相信,我竟然进入了眼镜蛇的巢穴。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一个我这么‘宅’的古文物研究者身上,我醒着的大部分时间可都是在跟电脑屏幕和旧书打交道的。”
迪恩不仅遇到了野生动物,还在孙德尔本斯遇见了皮娅(她仍在进行自己的研究)和提普。提普是对皮娅有救命之恩的渔夫福基尔之子,因此皮娅一直对他照顾有加。自从皮娅第一次到访以来,这个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游新建的炼油厂向河流中排放废水、暴风雨愈发频繁、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手机、动物的活动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海豚,它们的数量已经所剩无几。
提普是个世俗的人(他十几岁时曾与皮娅在美国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他对长辈们的民间知识嗤之以鼻。他说起话来就像20世纪80年代好莱坞电影里的捣蛋小鬼,爱把迪恩叫“老爹”,还喜欢说:“哥们儿你有事吗?看你好像有话想说。”他把孙德尔本斯的现状看在眼里。“能捕到的鱼越来越少了,土地盐度也越来越高,不贿赂护卫也不能进丛林了。”他边说边嘬着一根小树枝,准备去枪贩子那里。有条迁徙路线可以通往欧洲,擅长信息技术的提普做起了人口贩卖的生意。他最喜欢为客户捏造经历,好让他们有正当的理由来寻求庇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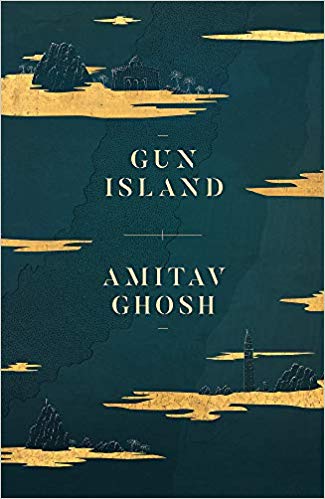
提普和他的朋友拉菲在带迪恩调查枪支贩所在的寺庙之后离奇失踪,迪恩在老朋友辛塔的帮助下寻找他们。在经历了一系列不大可能的遭遇(小说中有很多这样的遭遇),他们来到了威尼斯,另一个受到海平面上升威胁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亲眼目睹了当地人因受到气候变化影响而被迫迁徙移民。
精彩的拼贴之作
《枪岛》几乎完全是借着牵强的巧合和意外来推进的。比如,迪恩拿起他的录音设备,本想删除一篇采访,却意外按错按钮,导致录音开始播放。其中一些过于细小,不难看出是小说家为满足现实主义需要所进行的必要设计,另一些不大可能却发生了的切合则让人觉得实在太过刻意:辛塔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然后给他打电话,此前他们有好几个月都没说过话,迪恩“对突如其来的这通电话感到不安”,很明显我们读者的感受也是如此。书中人物总会这样说:“我们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但我有种认识了你很久的感觉。”当提普预测会有大量海豚搁浅时,迪恩问皮娅:“即使只是巧合,你不觉得这很有意思吗?”她不觉得。
丢失的笔记本、解码的符号和隐藏的圣坛……《枪岛》的叙事方式有些吉卜林短篇小说或约翰·巴肯的理查德·汉内系列悬疑小说的味道——与殖民活动息息相关。这一点肯定是作者故意为之,揭示人类在气候变化和殖民主义上的自我中心本质(人类世这一说法让我们真的认为自己是我们所处世界的中心),但结果是,这部小说读起来时常让人感觉像是一个对从前文学形式的模仿,而不是全新的创作。
要使我们自己的毁灭成为可想象的“不可想象之事”,一种方法便是将其设定在过去。在威尼斯散步时,辛塔和狄恩路过了安康圣母教堂。这座教堂是专门为圣母玛利亚而建造的,以此感谢圣母庇佑他们摆脱1630年那场瘟疫的侵袭。辛塔以艺术史讲师的口吻说道,“可以说,它是一场浩劫的纪念碑,是小冰期可怕疾病的纪念碑。”这仿佛是在安慰我们:糟糕的时代有时会造就伟大的艺术。
但高希在《大紊乱》一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却是,气候变化给作家带来了一种负担,这是其它灾难不曾抛出的问题——它引起了一项重大且重要的疑问。这个问题不是全球变暖是否会让小说获得新生,而是小说能否为阻止全球变暖恶化作出贡献。
从《枪岛》的表现来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这的确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作品,一段跌宕起伏又扣人心弦的故事,塑造得很成功,文笔也十分优美,但它为我们带来的那种满足感并不新鲜。在《大紊乱》一书中,高希曾总结说人类世对文学小说的抵抗将最终催生出“新的、混合的文学形式”,“阅读行为也将发生改变”。而令人意外的是,在书写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时,高希并没有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故事,而是呈上了以各种老套故事为素材的拼贴作品。《枪岛》对凶兆、预示和怪异的动物行为很感兴趣,它要求我们直接接受这些看似不可能存在的事实。与其说这部小说是在与从前的神话小说、流浪汉小说和哥特小说等文学派别决裂,不如说它更像是一次回归。
(翻译:张璟萱)
来源:前景杂志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