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宇辉 |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如果十年前有人跟你说,“人生不是一场游戏”,他的意思很明白:人生不是儿戏,真的挂了,再充钱也是不能重来的。但如果现在的90后、00后的孩子听到这句话,他/她的反应可能恰恰相反:人生当然不是游戏,那是因为游戏可比人生好玩多了。那就让我们从此处展开当下的反省。
游戏到底好玩在哪里呢?表面看起来,它其实与人生并无二致,只是将人生之中(暂时)难以实现的种种目标和价值转移到了虚拟的网络空间而已。看似一个个或美轮美奂或冰冷阴森的数字时空充满着不食人间烟火的气息,但其实戳破这个脆弱的肥皂泡表面,里面同样充斥着钩心斗角、争名逐利、尔虞我诈、阳奉阴违所有这些在日常生活中也令人厌恶乃至不齿的黑暗人性。
或许,游戏之所以好玩,是因为我们可以肆意妄为、毫不掩饰地在虚拟世界中展现、释放这些在真实生活中总是被压制、被禁止、被掩饰的邪恶欲望。你可能直接就会想到红遍世界甚至彻底改变游戏界格局的《侠盗飞车》(Grand Theft Auto)系列。在其中,你可以杀人、放火、抢劫、诈骗,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暴徒,但却总是乐此不疲、迷途不知返。因为无论你怎么坏,怎么恶,都不会受到任何真实的惩罚和伤害。当你拿着火焰喷射器扫荡“罪恶都市”街头的那些无辜的市民之时,心中定然会涌起一阵尤为强烈的扭曲的快感,即感觉自己分裂为两个部分:屏幕上的你在杀戮、在犯罪,而坐在电脑前面吃着薯片的你则在审视、在唾弃,在诅咒屏幕上的另一个自己。

世界分裂了,化为两个截然分离的部分,一个是真实的,另一个是虚拟的。你的这种最强烈的扭曲而邪恶的快感恰恰以此种分裂和分离为前提。正是因为这两个世界彼此阻隔、泾渭分明,才会为你的快感提供一个必需的安全堡垒,令你如隔岸观火的看客一般,与那个虚拟世界中的战火与血腥划开了必需的边界。
私人与公共:游戏何以是“世界”
游戏就是发泄被禁止的欲望。游戏就是在现实和虚拟之间划出一条安全的界限。然而,伴随着游戏平台的日益多样化、游戏介质的日益数字化、游戏环境的日益复杂化,以上这两种曾经主流的观点如今越来越变为陈见乃至偏见。确实,当你玩《魔兽世界》《守望先锋》《绝地求生》这些最主流的联网对战游戏时,表面上看一切平静,你还是安全地坐在真实的书桌前面对着屏幕上那一场场虚拟的腥风血雨。但在这个相似性的表面之下,我们却清晰地发现,游戏作为一种“根本性的人类活动”,它的本质特征及其所牵涉的“基本境况”都发生了鲜明的变化。

首先,如今的电子游戏似乎越来越回归游戏的真正本性,即作为一个自足而自律的存在领域。我们可以如赫伊津哈那般将其追溯至文化和历史的本源(《游戏的人》),亦可以如伽达默尔那般将其提升至超越个体的精神境界(《真理与方法》),它所揭示的无非是一个显见的事实:今天的孩子们如果说仍然在游戏中追逐着欲望之实现的话,那么其本源往往更多地是来自游戏本身,而几乎不再指向那些被禁止、被压抑的力比多。今天的游戏之所以“好玩”,是因为它“本身”就真的很好玩,而不再是因为那些在现实中屡受挫折的灵魂需要在另一个虚拟的世界之中寻求安慰和庇护。游戏为参与者提供了更多实现欲望和快感的形态与方式,比如荣誉、技艺、敏捷、合作甚至单单只是语言和行动的互动这些社交上面的需求,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只能从游戏之中获得,与真实世界的规则、日常生活的需求等都没有直接的、显见的关系。游戏为每一个参与者提供了远比真实更为丰富而多样的展现自我、实现自我、彼此沟通和互动的媒介——这大概是游戏比人生好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这样一种立场仍然不足以揭示当今的电子游戏不同以往的基本特征。纪录片《心竞技》(Free to Play)极为敏锐而又生动地捕捉到了此种关键的差异。在片中,有一个选手曾将电子竞技的本质概括为“象棋和足球”的混合体,但这并没有太强的说服力。因为新的电子游戏并非仅仅是在数码平台上对以往的游戏形式进行简单的综合,而是体现出一种全新的“人类活动”的本质特征。观者会有一个鲜明的印象,那就是这些孩子并非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选手或运动员,因为他们几乎所有的生活都围绕着游戏而展开。问题已经不再是他们在游戏中寻求生活中所缺少的东西,正相反,他们想要获得的一切“重要的”东西几乎都源自、只源自游戏,而生活似乎仅为他们提供生存必需的基本条件(可以借用阿伦特的概念“necessity”)。在游戏世界的日益拓展面前,日常世界反倒是变得越来越萎缩,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越来越减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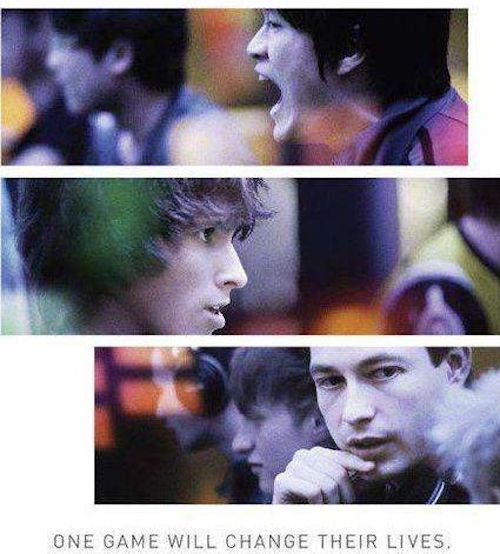
这就让人想到阿甘本在《身体之用》(The Use of Bodies)开篇提及的居伊·德波的那个耐人寻味的说法,即“私人生活的隐秘性”。此种“隐秘性”尤其体现为一种“无法穿透的(impenetrable)”“难以把握的”颇为悖谬的强烈体验。若说公共领域始终是有形的、可见的,那么私人生活就恰恰相反,它总是隐藏的、逃逸的,因而很难以个体间的种种交流媒介来表达和沟通。维特根斯坦对私人语言的批判可以作为一种证明。而德波自己的描摹则更为生动:真正被记录下来的私人生活其实最终只是“可笑而又微不足道的”。然而,即便私人生活就像是难以把握亦难以言传的暗影和幽灵,时时处处伴随着、纠缠着可见的公共世界,但这并不证明它就是无足轻重的。正相反,当你真正直面私人生活本身之时,反倒会发现它才是“真正的生活”,它才能展现出那种真正的生命的“强度”。由此,阿甘本最后极为敏锐地点出核心问题:正是私人生活的此种“不透明性”和“不可沟通性”,才使得当代的种种政治话语在它面前屡屡遭遇失败。
不过,基于德波的这一番剖析,我们发现今天以电竞和网游所建构起来的游戏世界几乎全然而彻底地抹除了私人生活和公共领域之间的明确边界。对于电竞选手和游戏玩家来说,私人生活这个原本最为真实而生动的本己领域越来越弱化为背景、退化为边缘、简化为最基本的“必需”。初看起来,这里面有一个显见的、但极为值得反思的悖论。一方面,大家都习惯于将沉迷游戏的人称为“御宅族(otaku)”,因为他们整天关在房间里,跟“外面”的公共世界毫无瓜葛。但另一方面,仅就电子游戏这种活动而言,御宅族之所以毫无迈出私人房间、进入公共领域的动机和意愿,正是因为公与私的关系在他们身上发生着明显而极端的变化。对于他们,只有网络和游戏的世界才是唯一真实的世界,他们在游戏里面得以展现自我、得以彼此互通、得以建构起种种复杂而多样的群体性关联。
不妨再度以德波为参照进行对比。德波之所以苦心孤诣地要为私人生活正名,无非是因为它显然是在无限蔓延的、同质化的景观社会秩序之下留存本真生命的一丝希望。简言之,真实的、鲜活的生命正是在景观秩序无从渗透和操控的私人生活的旮旯角落之处进行着顽强的却注定失败的抵抗。但对于今天的御宅族来说,这样的文人情怀只是伤感的怀旧而已,因为他们每一个人的私人生活和个体性完全不需要在挣脱公共秩序的暗处去寻觅,恰恰相反,只有在游戏世界的普照光芒和遍在网络之中,个体才能真正拥有个体性,私人生活才能真正显现出私人性。因此,游戏世界绝非是那种碾平一切差异的“常人”状态(《存在与时间》)或景观秩序,而恰恰是将差异性的个体连接在一起的崭新的共同体,“志愿精神、奉献与参与”正是其基本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游戏世界恰恰可以对阿甘本所忧虑的政治关怀给出一个明确的回应:“和游戏相比,现实是疏离的。游戏建立了更强的社会纽带,创造了更活跃的社交网络。”
有人肯定会说这样一番描述太过理想化和乌托邦化了。我们是否赋予了游戏世界太多积极的政治内涵?游戏的玩家,大多只是中学生和大学生,他们即便人数众多,但真的能在公共领域中产生多大的现实力量?再进一步说,游戏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产品,它又在多大程度上真的能够挣脱景观秩序的操控?说到底游戏难道不是让年轻人放弃抵抗、束手就擒的洗脑装置?我们不会真的认为那些玩游戏玩到上瘾、痴呆,甚至退化成“植物灵魂”的孩子们能够成为积极主动的政治主体吧?
要想从根本上回应这些常见的尖刻批评,单纯地罗列个案或进行现象描述显然是不够的。势必需要回归到根本的问题,跟随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奠定的基本框架进行双重追问:游戏究竟是怎样一种人类的活动?它对应的又是人类生活的怎样一种全新的基本境况?

先从第一个问题入手。在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三元分类之中,游戏居于何处?它肯定不是劳动,因为在游戏活动中,那些“人身体的生物过程”显然已经降到最低程度。游戏与工作确实有着非常明显的相似性。这里的工作当然不是单纯指“职业”,因为以游戏为业的职业选手毕竟只是少数。这里的工作也一定要从“境况”的角度来理解,也即,它鲜明体现出一种“世界性”:“每个人都居住在这个世界之内,但这个世界本身却注定要超越所有的人而长久存在。”这堪称是对游戏世界最为恰切的描摹和界定。
概括说来,阿伦特对“世界”的界定有三个基本特征:人造性(artificiality)、空间性以及公私之分化。首先,人造性强调的是“人类在自然大地之上建立起一个自己的世界”。这也就意味着,人造世界而非自然世界才是思索人类活动及境况的真正起点。由此也就从根本上斥破了那种常见的俗套,即认为网络空间和游戏世界只是虚拟的、不真实的世界,它必须依附于实在的、物理的世界方能获得自身的根基与意义。阿伦特提醒我们的恰恰是,对于不可胜数的玩家、御宅和选手来说,游戏世界才是唯一真实的空间,正是在这个人造的、但却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之中,个体才真正开始生存,个体之间才真正开始发生彼此的关联。所谓自然的、“真实”的世界早已退化为“外部”和“布景”:“现实已停滞不前,而游戏让我们共同想象并创造未来。游戏,将成为地球生命的下一种突破性结构。”一句话,游戏世界的真实性和本原地位,这个理当是所有思索的真正起点。
而世界的“空间性”则是对此种本原地位的进一步证明。它首先强调的是世界的“持存性”和“客观性”:“正是这种持存性,使世界之物相对来说独立于生产和使用它们的人,而它们的‘客观性’,使它们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能经受住、‘抵挡住’它们的制造者和使用者的贪婪无度的需求。”这也就意味着,游戏世界并非仅存在于玩家的感受和心灵之中,也并非仅仅指向不可见的、无形的人际关系,相反,它从本质上明确体现于技术媒介与平台环境之中。但世界的此种物性并非仅仅是惰性的介质,而更具有一种激活行动的本原力量。诚如伽罗威(Alexander R. Galloway)的经典概括:“离开玩家、机器的主动参与,电子游戏就只是静态的电脑代码。当机器被发动、软件被执行之时,电子游戏才开始存在;……电子游戏就是行动。”何为行动?无非就是在一个人造性的、空间性的世界之中所发生的独特个体之间的“创生性”的彼此关联。
就此而言,游戏世界无疑为每个人的行动提供了最为切实的基础和前提。如今的玩家不再是一个躲在屏幕后面泄欲的偷窥者,相反,唯有当他走进那个空间之际,才开始拥有真实的身份、行动和关系。这真的颇有几分近似阿伦特心目中的古希腊:“对希腊人来说,在共同世界之外,‘一个人自己的’(idion)隐私中度过的生活,按定义就是‘愚蠢的’(idiotic)”。
控制与反制:游戏到底是“共同世界”还是“社会装置”
然而,与阿伦特的类比看来在这里要暂时打住了。因为她心目之中的世界是“‘介于之间(in-between)’的东西”,也即将个体之间“既联系又分开的力量”,由此建构起一个“作为共同世界的公共领域”。关键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即便游戏世界颇为吻合“人造性”和“空间性”这两个基本特征,但它真的是在阿伦特的意义上得以对抗“社会(society)”的“共同世界”吗?仔细品读阿伦特对共同世界的细致描述,得出的结论可能正相反:游戏或许恰恰是一种“社会装置”而非共同世界。
概括起来,阿伦特笔下的共同世界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卓越”,它“总是被指定给公共领域,因为只有在那里,一个人可以胜过其他人,让自己从众人中脱颖而出”。因而,一个人之所以卓越,必然是在与之密切相关、休戚与共的公共领域之中方能实现。他展现出自身非同寻常的能力,进而获得同样分享这个公共领域的他人的尊重和肯定。很明显,这里自我和他人的关系是既“联系”(共同)又“分开”(“胜过”)。
第二个特征是“不朽”。这个特征源自“基督教社团”的历史形态,但亦完全可以视作共同世界的普遍特征,即作为“一个我们出生时进入、死亡时离开的地方,它超出我们的生命时间,同时向过去和未来开放”。这个特征一方面强调的是世界的“持存性”和“客观性”;另一方面突出了世界逾越于个体之上的那种历史性。真正的世界,并非仅仅是空间上的共享,还理应指向历史上的世世代代。
由此也就导向第三个重要的特征,即“视角”。世界是由差异性的、追求卓越的个体所构成的,它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拓展和持存,但贯穿所有这些差异的视角和绵延的世代,世界仍然保持自身为“一”。相反,“当共同世界只在一个立场上被观看,只被允许从一个角度上显示自身时,它的终结就来临了”。
然而,从这三个基本特征来衡量,游戏世界其实完全不符合共同世界的标准,甚至处处都走向其反面,即“社会”。首先,你可能会觉得所有电子游戏的本质都是追求卓越,都是为了刷出更高的分数,排上更高的等级。即便对于那些并不以直面厮杀为乐的游戏类型(比如生存类和经营/模拟类游戏),其背后仍然有一个庞大的群雄逐鹿的玩家排行榜甚至名人堂。
但真的是这样吗?共同世界中的卓越是以每个人之间的不可通约的差异(即复数性[阿伦特]或特异性[内格里])为前提的,但游戏世界里的竞争性的卓越恰恰是以抹杀差异的同一而普遍的衡量尺度为前提的。固然,在刷分和练级的漫长艰辛过程中,每个玩家势必要展现出自身“独特”的能力,比如操作技巧、统筹眼光乃至领导才能等,但所有这些能力最终所指向的并非是你的不可还原的特异性,而恰恰最终都要换算为普遍的、可通约的数与量的价值尺度。而这难道不恰恰就是阿伦特所着力批判的“社会”系统?
通观阿伦特对“社会”兴起过程的细致阐释,关键一环正是古希腊那里的polis和oikos之间的明确边界逐渐模糊,进而逐渐形成“公共家政(public oikos)”这样一种融合形态。随后,更是进一步演变成近现代意义上的“普遍经济学”,它清除了家庭关系之中所预设的家长制的不平等关系,但却最终建立起一种“无人的统治(no-man rule)”。此种统治体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行动、意见和利益的“趋同”,二是以一种普遍而同质的计量尺度来进行调节、管理乃至操控(“看不见的手”)。这两点亦活脱脱正是游戏世界的真实写照,甚至在其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不妨再以不朽和视角这两个基本特征来进行比照。在游戏世界里面,也确实存在着近乎无限的时空拓展,但这并非真正的不朽,而只是地图编辑器的强大运算能力的展现而已。像通关时间的长度、线程的复杂度乃至世界的开放度等现在都是衡量一个游戏的可玩性和耐玩性的重要参数,但这些都全然不能展现共同世界的持久性和客观性,同样,在如今的游戏里面,多重视角及其“切换”亦是一个极为常见的操作,但这些变幻无穷的视角都跟你自身的特异性没有任何关系,而只是同一个数字化的参照系中的不同坐标定位而已。确实,当你从第一人称视角切换成俯瞰全景模式之时,你所置身的世界仍然保持“同一”,但这样一个世界里面并没有“复数”的个体,而只有无限计算生成的“位置”。
回到阿伦特对人类活动的三元区分,在这里不妨总结说,游戏至多只能算是“工作”,而且最终只是在一个由看不见的手所掌控的“社会”系统之中被定位、被管理、被计量的工作。它既然无法真正实现“行动”所预设的复数性,也就根本无法达成行动所指向的鲜明的政治诉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游戏最终只是一部强大而遍在的捕获性的“社会装置”而已。
不妨借用阿伦特的一个极为鲜明的形象来描绘此种困境:“这种情形的诡异就有点像在一个降神会上,许多人围桌而坐,由于突然降临的某种魔法,他们看到中间的桌子消失不见了,以致相对而坐的两个人不仅无法隔开,而且也完全没有什么有形的东西能把他们联系起来。”游戏世界不正是这样一个会降临的“诡异”场景?每个人似乎都在分享同一个真实而持存的世界,但实际上这个世界却只是以无形的、不可见的方式消弭了每个人的特异性,最终将他们抛入一个无尽空虚的数码深渊之中。在游戏世界之中,不再有复数的行动者,而只有共享着语言和认知的“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诸众(multitude)”。
然而,结论本可以不必如此灰暗悲观。因为即便游戏世界只是“社会”的极致形态,即便游戏作为一种基本的人类活动完全没有上升至“行动”的可能,但仅就阿伦特的这个三元区分而言,显然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反向的可能,也即深入到、返归到“劳动”这个基本层次,也就是回归到身体性这个基础和本原。你可以说游戏玩家少不经事,只是任由社会装置摆布的傀儡,但是否在他们的肉身之中,仍然蕴藏着某种难以被彻底操控和规训的“潜能”?
只不过,阿伦特的答案可能恰恰相反。在卡诺万(Margaret Canovan)精准提炼出的劳动的六个基本特征中,“私人性”是最后一个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特征。“唯一与这种无世界的经验,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痛苦中丧失世界的经验严格一致的活动,是劳动。在劳动中人尽管也活动着,却被抛回到了自身,除了关心他自己的活着之外什么也不关心。”显然,在这番基本界定中,劳动完全没有体现出任何真正创造或行动的潜能,它深陷自然性的生理需要之中,紧闭于自我的狭窄范域之中,就是全无反思、甚至对周围的世界至为冷漠的“存在者”。
然而,用“冷漠”这个词并不恰当,因为阿伦特在这句话中(及上下文之间)暗示出一层极为关键的含义:劳动着的“私人”虽然没有世界,但却在最强烈的意义上能够体会到自身的存在。这样一种体验的极致形态正是痛苦,以及“摆脱痛苦”这种反向的、但却同样强烈而极致的体验。反复强调“强烈”“极致”这些形容词,正是要突出这样一个要点,即这里所涉及的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情感”体验,而更是维尔诺(Paolo Virno)(在康德和海德格尔意义上)所阐发的基于、源于“在世”之根本体验(“inherent in my very being in this world”)。
“一般情感”与“在世体验”的这个区别是极为关键的。首先,在这样一个情感日益智能化、工业化、商品化的时代,要想在其中重新敞开创造之潜能近乎痴人说梦。游戏世界正是这个困局的鲜明写照。作为一个人造的、持存的、客观的社会装置,游戏世界并非是一个冷冰冰的数码宇宙,恰恰相反,它其中越来越充溢着丰富、多样、多变的情感体验。晚近以来的游戏设计中对情感效应的突出强调正是明证。就此而言,它异常吻合德勒兹与加塔利对捕获装置的基本界定,即以流动性的、生产性的、诱惑性的方式来实现灵活多变的规训与控制:“有了数字媒介,我们则可能在一种高度兴奋和期待的状态下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在这种新的情形下,我们自己都能够创造出让我们高度兴奋的环境和状态。”
正是因此,维尔诺借自海德格尔的那一对著名概念“怕/畏”恰好为挣脱这个情感汹涌的捕获装置提供了一个可行出路。“怕位于共同体及其生活和沟通形式的内部。而畏则相反,它只有从所归属的共同体之中分离出来之际方才显现自身。”显然,如果说怕是游戏世界之内的“极端的情绪激活”,那么畏就更为根源地指向极致的在世痛感。游戏中的怕固然跌宕起伏、惊心动魄,但说到底都是有着或明或暗的“具体”对象,进而激发你做出相应的“操作”。即便在那些以“氛围”著称的恐怖游戏(《寂静岭》《生化危机》)之中,此种看似“无对象”的氛围也全然不能等同于“畏”的那种“绝对的”“不确定性”,因为沉浸在恐怖的黑暗氛围中的玩家并非茫然失措、迷失方向,反倒是被激发出一种更为强烈而明确的“怕”之体验,保持着高度警惕,面对下一秒就可能骤然从暗处跃出的邪灵与僵尸。

然而,玩家并非只有“怕”,还必然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挥之不去的“畏”之体验。怕是一种公共的情感,而畏则属于那些被同伴孤立的个体。而此种从社会性的游戏世界里面(暂时)挣脱出来的带有鲜明“私人性”的情感体验,或许恰恰正是阿伦特所言的直接源自在世肉身的那种“痛感”。你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在游戏世界中获得“安全”的庇护,正相反,肉身之中那种“绝对”不可消除的、完全“不确定”地袭来的痛楚还时时刻刻提醒你自己是一个在世的生命体。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本文开始处所描述的那种在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辩证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现实世界不再是安全的港湾,为你在虚拟世界之中的杀戮和冒险提供一个庇护的前提;正相反,如今,游戏世界才是终极的庇护所,而真实的世界仅以阵痛的方式残存于身体这个不可消除的“残余(residue)”和难以愈合的“伤痕(trauma)”之中。也正是因此,这个在世的痛感构成了对于游戏世界这部强大而遍在的捕获装置的终极反制和抵抗。
身体之“用”——游戏何以“自制”
对于阿伦特,劳动及其所指向的肉身性这个基础根本无法作为抵抗和解放的真正力量,反而其自然性的生命力量会越来越深陷到“未来自动化的危险”之中。显然,社会装置并非仅仅运作于游戏世界之中,而更是对玩家的真实肉身同样施加着深入的规训与操控。所谓的“网瘾”的根源也正在此处。网瘾并非只是现实世界中的种种上瘾行为在游戏空间中的投射,更是在身体层次所不断形成的“自动化”的惯性,是生命本身不断陷入被技术所操控的机械循环的重复节律之中。
然而,基于维尔诺及其所代表的诸众理论,我们却本不必持如此悲观的立场。既然在当今的世界,私人生活与公共领域间的边界早已模糊不定乃至彼此融合渗透,那么诸众身上的情感体验也就不能简单以怕与畏来描摹。至少就游戏玩家而言,肉身的痛感绝非是全然私密之体验,而是震荡于公与私、外与内、群与己之间的始终焦灼的、难以化解的张力。诸众的解放潜能也往往正是源自此种张力。这一要点后来在哈特(Michael Hardt)与内格里(Antonio Negri)对“诸众的生产性肉身(productive flesh)”的论述中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他们进一步乞灵于肉身性的情感力量,试图在不同的特异性个体之间重新建构起彼此共振、互通的“共同世界”。
但诸众理论仍有一个明显症结,即将创造的潜能归于一种“无序而自发”的情动,因而全然无法揭示主体自身何以能够主动地进行反思、判断乃至决定。而阿甘本结合思想史背景所详述的身体之用恰恰可以为此种僵局提供解决的对策。他将此种主体性的自控与决断称为“沉思(contemplation)”:“沉思就是使用之范式(the paradigm of use)。沉思并没有一个主体,因为沉思者在其中已然彻底消失和消解;与使用一样,沉思也没有一个客体,因为它在成品(work)中所沉思的唯有(自己的)潜能。”显然,沉思对身体的“使用”亦并非如诸众理论那般任由潜能向着现实进行不可遏制的生产,而是更强调回归于“无作性(inoperativity)”这个核心的“用法”,进而从根本上实现主体对自身的“自制(use-of-themselves)”。并不令人惊异的是,阿甘本的论述或许恰好为《人的境况》中所构想的“沉思”式积极生活在身体层次提供了一个切实的操作。
在晚近以来的游戏实践与理论之中,“身体”与“用”无疑是两个要点。比如简·麦戈尼格尔在新书《游戏改变人生》中就探索了如何开发身体的潜能以便能量满满地回归游戏世界的怀抱。再比如,利亚姆·米切尔所提出的“反玩(counterplay)”就是倡导在玩的过程之中发挥自主的掌控力和自由的创造力,以更为“介入和自省(engaged and reflective)”的方式来对抗游戏世界对主体的控制和规训:“玩也可以对控制构成一种有效的挑战”。
然而,还是本身就有着深刻的游戏设计和哲学理论背景的博格斯特真正将身体与用结合在一起,启示出未来的方向。在《玩的就是规则》中,他首先从根本上区分了面对世界的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即反讽和游戏。“热衷反讽的人不接受现实、不创造现实,也不会采取其他方式接受世界本质上的荒诞,更不会与之互动。”但真正的游戏精神则正相反,它尤其体现为三个渐次递进的步骤。首先,“玩是事物的特性,而不是它们带来的体验”。这也就要求我们首先承认游戏世界的持存而延展的物性,真正地进入其中,而绝非徒劳地、自以为是地退回到主观、私人的“体验”(无论是情感的体验还是肉身的体验)中来进行反讽式拒斥和抵抗。其次,“玩的核心体验不是随心所欲或者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而是经过认真审慎的思考,用心处理情境中的各种材料”。这恰恰揭示出,游戏的最基本精神正是“自制”而绝非“自由”。这也正是自制与“反玩”在反省态度上的根本差异。二者虽然皆以接受游戏世界的现实和规则为前提,但反玩是以游戏产品为起点和核心,在发明、创造出层出不穷的新玩法的过程中展现出主体的自由;而自制正相反,它不是追求“多多益善”,反倒是恪守“臻于完美,……减无可减”的基本信条。一句话,反玩最终仍然落入欲望-机器的捕获之流难以自拔,而自制正相反,它最终试图以极简的操作敞开反思的间距,确定主体的位置。
游戏之为自制,在他更具哲学思辨色彩的著作Alien Phenomenology之中得到了进一步阐发。在这里,博格斯特基于思辨实在论背景所提出的“思辨(speculation)”堪称对于“沉思生活”最具创意的推进:“物在思辨,而且,这样一种(哲学)正是要对物如何思辨进行思辨。”思辨不再仅仅是人类之能力,而拓展为万物之“道”。因而真正的思辨和沉思的生活并非仅仅旨在建立人类主体之间的自由而积极的关联,而更是要将每一个人类个体化入更大的物的体系和宇宙之中。这正是游戏之“大用”。在当今的世界,还有何种媒介能够将最为多样而复杂的存在要素缠结卷携在一起,构成一个“物导向(object-oriented)”的聚合体?
博格斯特以Atari公司1982年出品的游戏E.T.为例,列出了游戏的十一个并存而交织的面貌:作为代码、介质、商品、规则、经验,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游戏的世界早已远远超越了阿伦特和内格里所追求的大同世界,而成为建构“万物平等”的扁平本体论(flat ontology)的终极力量。由此,游戏所激活的思辨也为阿甘本所玄想的“沉思”提供了切实的策略。思辨,正是在深入物的缠结网络之际抽身自制,恪守着不可还原的内在的物性深度。
这尤其体现于晚近游戏设计中的两大特征。首先是枚举(listing)和命名。这在冒险解谜(AVG)类游戏中最为常见。在一个密集堆积着物品的房间之中按图索骥、分门别类、整理次序,这尤其考量玩家在一个物的宇宙中发现、记录、延展“痕迹”的能力。其次是所谓“分解图”模式(exploded-view diagram),就是在一个极为复杂的物的空间内部展开操作,以敞开种种陌异的、不可思议的面向和维度。这一特征在手机平台上的几何和物理类游戏中有着极致体现。如《纪念碑谷》玩家所经历的最大喜悦或许远非充满亲情的心路历程,而恰恰是源自迷失于、穿梭于物的迷宫中的那种无可比拟的刺激。何为自制?那正是在深深卷入物的秩序的同时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如何自制?那正是在无限复杂缠结的网络之中以留存和延展痕迹的方式来实施“化繁为简”的操作。

“玩是谦恭,不是解放”,不妨将此视作游戏世界的“未来启示录”。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4期,原标题为《作为控制、反制与自制的电子游戏》。)
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