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提出,2016年以来在英国和美国所发生的一系列混乱政治事件是由一场突然的民粹主义热潮引发的,如今这种观点已然变成了一种文化神话。无论是时事评论员还是政界人士,在提到过去几年甚至几十年时无不带着一种温和而怀旧的情怀,他们将2012年奥运会开幕式、奥巴马的当选以及女王登基50周年庆典视为自由主义的试金石,却忽视了财政紧缩、无人机袭击和帝国残余。
在文化研究和其他领域,“迷思”一词长期以来都被用来说明事件和图像如何被用于意识形态层面: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称之为一种巩固自然与历史之间混淆的体系。在《我们需要新故事》(We Need New Stories)一书中,奈斯琳·马利克(Nesrine Malik)解构了当代西方社会的“六大迷思”,并借此对定义当前政治形势的“例外论”提出质疑。马利克认为,这些杜撰包括性别平等的迷思、政治正确“危机”、善意溯源(粉饰历史以建构民族自豪感叙事的倾向)、言论自由“危机”、“有害的”身份政治以及可靠叙述者的迷思(拒绝承认自己特权的叙述者)。
马利克用严谨的理据一一反驳了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说法,解释了过去三年发生的事件实际上是一个历史连续体中的一个节点。从18世纪晚期“政治正确”一词的法律起源到大众媒体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再到美国校园红色恐慌的历史,权势人物的道德恐慌始终相互联系,他们默许了那些重大伤害的发生,并使之走向合法化。
马利克把政治正确归为一种原型迷思。正如一直以来太多“进步不仅存在,甚至发展得太过泛滥和迅猛”这样的主张导致社会现状停滞不前一样,政治正确也如此。至于被捏造出来的言论自由“危机”,则是由一个错误对等关系系统造成的,诸如言论自由权被等同于可以在论坛随意发言,以及任何因引战言论而被限制发言的现象被等同于审查,而政治正确的迷思是根植于强大焦虑之中的意识形态工具。本书用一条线索将六个迷思联系起来,那就是弱者总是会被塑造成侵略者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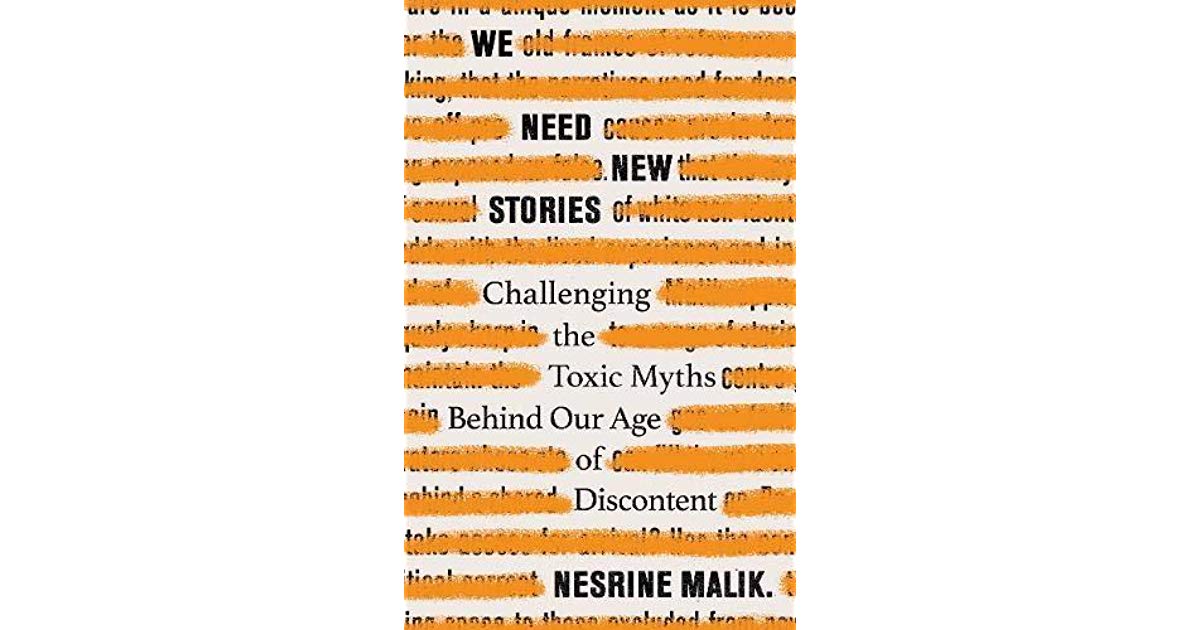
从某些热切捍卫言论自由人士扬言要起诉诽谤他们的批评者的讽刺事实,到诸如乔丹·彼得森、史蒂文·平克以及道格拉斯·穆雷(穆雷在《旁观者》发表了针对MeToo运动的声明,称这项运动“预示了人类的毁灭”)等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名人作品中“现代社会生物学决定论”的复兴,马利克揭露了一系列伪理中客博主的歇斯底里。她在书中阐明,“有害的”身份政治迷思背后其实暗含着一种错误的观念,即认为白人身份政治并不存在。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总是被人们用“白人的脆弱性”和“经济焦虑”等委婉语加以掩饰(在某种程度上,激进白人至上主义其实是“经济焦虑”而非恐怖主义的表现)。她厌倦地指出,“大多数经济焦虑基本都发生在公共交通上。”

马利克从事金融相关工作10年,对晚期资本主义下的生活有着独到的经济学理解。她发现某些群体不仅通过财力巩固对公共话语的控制,而且还是以一种阴险的方式进行着这些操作,他们让各方面的事务都染上了交易的味道。说到女性一辈子为了平衡工作与家庭所做出的一系列妥协,她指出:“无论自身条件、处境如何,每个女性都要面对这种不断讨价还价的困境。”尽管马利克在书中对性别平等迷思的讨论只集中在它对政策和立法的阻碍,及其对于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的默认合法化上,但她对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女权主义所扮演的角色也是持批判态度的。
她对一直在扩大的兜售“少数族裔经历”相关私人证言的压力同样持批判态度,劳拉·班尼特(Laura Bennett)将这种证言称为“第一人称的工业综合体”。马利克也指出了自己处境的尴尬之处:写厌女症、伊斯兰恐惧症和种族主义的需要和被边缘化的危险之间的矛盾对立,“害怕我发出的声音会被‘作为’一种话语加以利用。”马利克以广泛的研究和访谈为素材,书写出了对现状的全面、深入的讯问,她承认自己怀有主观上的敌意,并将之视为写书的动力,当然这种敌意也超出了具体的针对范围:“我希望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能够把它看作一种对迷思的见证,并且和我一起企盼这本书对最有害的那一群人构成一些实在的挑战。”
重要的是,这种见证并不是被动的。在描述迷思的运作方式时,马利克的语言背后暗含了这样一种理念,即:理解迷思的构造可以帮助我们对抗它们。谈到帝国的“残余”,马利克更关注它这种不对抗机制的本质,而非残余本身,虽然她也激动地为自己出生地苏丹设想了另一条可能的历史道路,而它还是一步一步地走上了现在这条道路。这种以“保持冷静,坚持下去”口号为标志的英国式镇压发生在国民心理层面,表现为对一个从未真实存在过的帝国的怀旧情结,而这种怀念是由一门聚焦“希特勒和亨利一家”的课程所煽动起来的。《我们需要新故事》的写作意图是扭转大众的视角。作者在善意溯源迷思部分的一开篇就说:“每个国家的主流历史都是一种集体幻觉。”那么,我们可以把这本书当作一部反主流的历史来读,毕竟它碾碎了为那么多伤害洗地的荒谬迷思。
(翻译:张璟萱)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