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歌手董宝石的歌曲《野狼disco》日前掀起一阵热潮。这首歌自带浓烈的东北味与律动感,歌词以东北方言形象地指示了听众应当如何参与这首歌:
“来左边儿 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儿 画一道彩虹/来左边儿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儿 再画个龙/在你胸口上比划一个郭富城/左边儿右边儿摇摇头/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指向闪耀的灯球。”
在某短视频平台上,这首歌演绎版本众多,不同地方的人们在建筑工地、迎新晚会甚至是婚礼现场上唱起这首歌,亮出自己的“画龙”和“画彩虹”,构成了一幅幅喜庆斑斓又略显荒诞的场面。明星们也纷纷加入效仿,罗志祥上传了自己的版本,就在前几日,陈伟霆也加入了演唱,负责粤语部分。
《野狼disco》引发了一场关于土俗与洋气审美标准的讨论,有人认为这首歌“抓耳洗脑”“清晰还原了一段时期的社会风貌”,致敬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粤语流行风潮,可以称得上是一件艺术品,也有人认为这首歌就是土嗨,本质上属于典型的口水网络歌曲。究竟是土气还是洋气暂且不论,我们或许可以将这首歌作为东北文艺创作样本,寻找它与其他东北文本之间的共同关键词,比如干仗、你老舅以及小品。
干仗叙事

这段歌曲引人注意的不仅是其东北方言,还在于强烈的叙事特征。歌曲开头模拟了一段急急忙忙要挂断电话的情节,结尾处是此男子不得不接起电话并问道,“啥?干了?对方啥阵型?442?踢你呀,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
以挂断电话开始,以接起电话为结束,虽然电话对话在各种重演中被视为铺垫并因此常常被省略,但这一头一尾无疑将这首歌框定在了特定的东北时空里,并指向了娱乐场域之外的社会生活情境。相较于东北二人转摇滚“二手玫瑰”歌曲《伎俩》在前面附加的广播内容,《野狼disco》中的电话对话显然更能体现出歌舞者的生活处境。
对话向听众交代了一个草蛇灰线般的情节和背景:面前唱跳disco的人,在这个场子结束后,即将奔赴另一个干仗的现场;如果我们以男声颇不耐烦又久经考验的通话语气、在电话里关心对方阵型的通话内容来推断,这样的事很可能天天都有。——上次听到这样交代日常活动线索的歌曲,还是Gai的《垃圾话》,二娃吃完羊肉汤,要在网吧混一晚上。
《野狼disco》的干仗氛围,不禁令人联想起东北主题小说里相似的斗狠情节。在班宇的小说《冬泳》中,故事最高潮出现在主人公“我”给了情敌一记砖头,这次攻击行动被描写得既突如其来又仿佛经过深思熟虑。
“就在这时,我几步奔过去,攥紧砖头,露出带尖的那面,不等他回身,跳起来直接砸在他的后脑勺上,力度很大,他立即扑倒在地,捂着脑袋回头看我,说了句,哎我操,充满疑问的语气……”
这个进攻过程是持续的,“我”看对方没有被立即撂倒,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我拎着砖头,照着眼眶猛砸,左右左右,轮着一顿搂,打得我掌心发麻……”通过暴力的干仗和斗狠,“我”压抑已久男性力量得到了复苏。在成功打趴了情敌之后,“我”又回到情人家,粗暴地占有了她,“先从后面跟她干了一次,有点粗暴,隋菲叫得很凶,后来还带着哭腔。”对情敌拍砖成为了故事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我”对情敌的敌意仅仅停留在言语的试探;在这之后,对情敌的征服跟对情人的占有似乎成了一回事——两场战斗都以对方一动不动、彻底投降为结局。

班宇 著
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 2018年11月
班宇在另一篇小说《盘锦豹子》中也写到了类似的时刻。花名为“盘锦豹子”的前姑父,半生活得谦卑忍让,老婆跑了都不问原因;最终在房子被抵押、有人前来看房时,爆发成为一头猛兽。
“我的姑父孙旭庭,咣当一把推开家门,挺着胸膛踏步奔出,整个楼板为之一振,他趿拉着拖鞋,表情凶狠,裸着上身,胳膊和后辈上都是黑棕色的火罐印子……在逆光里,那些火罐印子恰如花豹的斑纹,生动、鲜亮并且精纯……”
“孙旭东看见自己的父亲手拎着一把生锈的菜刀,大喝一声,进来看啊,我操你妈,然后极为矫健地腾空跃起,从裂开的风里再次出世……”
与班宇所写的隐忍中爆发的场面相比,双雪涛短篇小说《跷跷板》中的谋杀显得尤为冷酷,加之故事发生在冰天雪地之中,直教人冷上加冷。《跷跷板》借由一个病入膏肓、思维混乱的病人讲述了一段杀人经历。厂长刘庆革1995年让一个工人下了岗,这个工人跟他纠缠不休,厂长不堪其扰本想找人“把他做了”,后来决定还是自己来——“我用扳子把他敲倒了,然后又拿尼龙绳勒了他的脖子。”行动后,他确认了对方的死亡结果:
“我确定他死了,眼睛比过去还突出,舌头也咬折了,我就把他拖到厂子尽里头的幼儿园,用铁锹挖了个坑,把他埋了。就在院子里跷跷板的底下……”
为了完成厂长迁骨安葬的托付,“我”在冬天的夜里潜入厂子,在跷跷板下开挖,最终找到一具骸骨,也证实了厂长杀工人的真实性。

双雪涛 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 2017年8月
在东北,干仗和杀人工具除了菜刀、板砖和扳子,还有刨锛。在班宇的小说《肃杀》中,父亲跟正在写作业的、十一岁的“我”解释了“刨锛帮”是什么——父亲说“刨锛帮”一个专刨后脑勺的组织,好一点人直接死了,点子背就一辈子植物人。需要注意的是,与集中偶然的暴力爆发场面不同,这只是一段描写日常饭后父子交谈的闲笔,与主要故事线索基本没有关系。
班宇的小说里此类闲笔颇为常见。在另一篇《空中道路》中,“我”的父亲班立新“惹不起”“能干仗”的形象并不是正面写出,而是在与他人的多次交谈中从侧面烘托出来的,比如他与保卫科的人交谈:
“保卫科的人看看手里的名单,说道,我知道你,姓班,刺头儿,爱干仗,进去过……保卫科的人说,因为啥呢?班立新说,没啥,聚众斗殴,多少年前的事儿了。”
后文也补足了父亲年轻时包里放匕首的习惯:
“他摸到那把冰凉的冰凉的硬物,刚想掏出来,却又想起自己刚满半岁的儿子……”
由此可见,在这类东北文学的文本当中,干仗斗狠不仅可以构成故事的转折点以及悬念,同时也是一种弥散于文本之间的氛围——干仗的激情迸发于冰天雪地之中,犯罪团伙成为茶余饭后的都市传说,指向了与《野狼disco》一致的氛围暗示与背景延伸。
你老舅
《野狼disco》收录于董宝石名为《你的老舅》的专辑里。老舅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情景喜剧《东北一家人》第一集就交代了老舅牛小伟这个人物,他负责教会外甥军军油腔滑调,用姥姥的话说,“(他)跟谁学的,还不是跟他老舅你学的。”在董宝石的另外一首歌曲《社会老舅摇》里,老舅又扮演了一个借助蹦迪安慰失恋外甥女(如果真的是外甥女的话)的可靠角色。
“他一定会伤你的心/因为你们都还年轻/你就喝吧别怕懵/待会老舅会把你抱紧。”

董宝石在接受“GQtalk”采访时提到,老舅这样的形象反映了东北很多男性身上都有的“社会大哥”气质——他们不是大哥但装作大哥,身穿貂皮大衣,颈系大金链子,以掩饰自己内心的脆弱。《野狼disco》的核心部分都在教人如何比划好街舞,所谓“踹翻富二代”“卡死小黄毛”只不过是摆好架势、营造气氛,并不会造成一丁点儿真正的危险或伤害。
有人将《野狼disco》与Gai出道之前的流传于网络的作品《超社会》对比。从歌词看来,《超社会》不仅反复发出“老子社会上的”这类宣言,还展现出了黑帮贩毒卖淫、不服管制等反社会的危险特征,相较之下,《野狼disco》里单枪匹马、唱跳街舞的老舅实在非常安全。
神秘的是,《野狼disco》确实营造出了一种危险的氛围——东北话的江湖味与粤语电影的刀光剑影掺杂组合,梁朝伟、《无间道》、郭富城、中意你,与胯胯轴和窜天猴神奇地混杂在了一首歌曲当中。其中对粤语电影的怀念,可能不仅是创作者董宝石在“GQTalk”中和对谈者班宇聊到的、在追忆自己青少年时代浸淫过的粤语流行文化,而更带有一丝惺惺相惜的意味——借由不标准的粤语和支离破碎的港式片段,地域遥远的东北青年想象着粤语电影的刀光血影与江湖义气,又以摇动胯胯轴、比划郭富城迅速将这种想象瓦解至一套易模仿、可重复的表演。末了那句常见于二人转演出的活跃全场气氛的“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才是这首歌的题眼所在——实际上,参与这段掺入粤语的歌舞表演与欣赏二人转本质区别不大,就像董宝石所说,现在主流就是轻松愉快,“别整啥深刻的。”
回到老舅的问题,外表危险、内里脆弱的老舅型男性形象其实常见于东北文学之中—— 说到外表危险,如前文所述,老舅的会干仗可能是一种弥漫于文本之间的氛围;那么说到内里脆弱,其脆弱感又是从何而来呢?
《冬泳》里的东哥是“我”情人的前夫,他成日不务正业,混迹于歌舞场和赌场之中,经常上门勒索前妻,见到“我”跟他前妻好了,不仅用“小逼个子”“逼样吧”称呼“我”,还威风凛凛地威胁“我”给他交钱,但真正打起来却毫无招架之力,只会感慨一句“唉我操”。《空中道路》中的“我”父亲班立新也是一位“进去过”的厉害人物,对外声称根本不怕处分,“谁啊,敢处分我,借他俩胆儿,”但一遇上厂里的记过处罚,他还是老实起来,不再打牌喝酒,工作比以往都辛苦,人却比之前更沉默。
东哥的脆弱是因为年纪增长体力不行、缺少反击之力;班立新仍然可以干仗,只是担心自己会被开除,再无能力庇护他的家庭。这种个体的脆弱感又与时代的变革相关联:在工厂改制、下岗大潮涌动之时,他更需要小心翼翼护好手中的饭碗。班立新的朋友李叔在被通知下岗之后说自己无事可做,本来觉得一辈子开吊车挺没意思的,现在觉得开一辈子吊车也蛮好的,正是对自己不能开一辈子开吊车的类似忧虑,使得班立新从“狠人”变得脆弱。
“他本来以为自己并不在乎,但在不经意间,却发现自己的所有行动变得小心。”
如果我们了解同时期东北工人的真实生活状况,便也可以理解班立新的顾虑了。出版于2012年的《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工人》一书记述了那个时代面临精简的国企员工的困境——被精简下来的工人不得不重新开始找工作,做点小生意,对被精简掉的员工来说,他们确实有了寻找工作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在多数情况下只意味着“饿肚子的自由”。这就像班宇在《三联生活周刊》的口述中所说的,他从前住的变压器厂宿舍楼里的大部分人都下岗了,他们或是做点小买卖,或是出去打工,每家人都在用自己的方法活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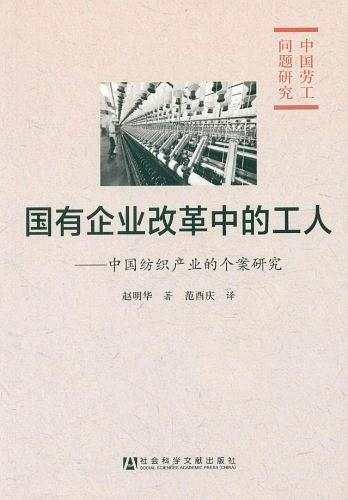
赵明华 著 范西庆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7月
小品化
在一档名为《旋转吧假期》的央视综艺节目中,小品演员潘长江表示不想再跳1996年春晚经典节目《过河》了,转而跳起了流行神曲《野狼disco》。从《过河》到《野狼disco》,东北风味神曲仿佛经历了一次更新迭代——《过河》已经远去,《野狼disco》才是当下最流行。这样一首带有夜店蹦迪风格的歌曲在央视综艺节目中播出,并且由一位正统东北喜剧演员进行表演,这无疑减弱了它的夜店风格,并同时强化了其喜剧色彩。有网友评论称《野狼disco》“太乐了”“好搞笑”,这不是唯一一首被评价“搞笑”的东北风味歌曲,“二手玫瑰”一系列歌曲也以喜感著称,其作品有着明显的二人转唱腔,比如《命运》里的“哎呀我说”,与歌曲对命运的咏叹形成了明显的反差。那么《野狼disco》为什么会令人觉得好笑?仅仅因为是它的东北味吗?
正如前文所述,《野狼disco》的开头结尾都有电话对话。专辑中其他歌曲如《同学聚会》和《社会老舅摇》里也有类似的对话,一次是老舅安慰失恋的外甥女过来蹦迪,另一次是老舅同学聚会喝多了要求外甥女前来代驾。这类对话映照出了不同的生活情境,其真实感甚至延续到了与明星的对话里——老舅和陈伟霆通电话商议,如果他去给陈伟霆演唱会帮忙能拿多少钱,犹如小品《昨天今天明天》里赵本山问崔永元能不能把来的火车票报了。情境的真实具体以及随机应变的即兴发挥,赋予了这些歌曲一种小品感和喜剧色彩。
从语言层面来看,其歌词也确实吸收了东北的方言土语,比如“捂住脑门儿晃动你的胯胯轴”“小皮裙/大波浪/跳起舞来真像样/喷的香水太香/好想和她唠一唠”,但更重要的是,歌词文本还吸收了一些看似通晓人情世故的、高屋建瓴的、合辙押韵的套话,像是“玩儿归玩儿/闹归闹/别拿蹦迪开玩笑”。有的套话甚至是对小品台词的直接改写,比如《你的老舅》里的“已经整成三胖子了/必须当头再给三棒子”改编自1998年春晚小品《拜年》的台词“乡长变成三胖子,不要再给一棒子”。

人们可能已对赵本山系列小品中的金句非常熟悉,其实除了著名的“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和“挖社会主义墙角,薅社会主义羊毛”之外,类似的套话在东北喜剧表演中非常密集,层出不穷,彼此叠加,而且不一定是由负责搞笑的主角来演绎。举个例子,在赵本山的辽视春晚小品《相亲》里,相对正经的女性角色海燕先是说自己的前夫老头死了,又随口补充,“没死,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最极端的情况是每个人说话都像一串顺口溜,比如情景喜剧《候车室的故事》中的董六,是一个不押韵说不出话来的盲流,再比如1999年春晚小品《打气儿》中表达心迹的高光时刻,黄宏说出来的也是一串顺口溜:
“十八岁毕业就入了自行车厂/先入团后入党上过三次光荣榜/厂长特别器重我眼瞅要做副组长/领导一直找我谈话说单位减员要并厂/当时我就表了态/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在东北作家的小说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修辞方式,比如在班宇的《盘锦豹子》里,“我”爸对做印刷厂工作的“盘锦豹子”“我”姑父说,教育问题必须得重视,而且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对方则回应道,哥,你对社会理解挺深啊。这样“一套一套”的对话如果用东北话来评价,大概正是——“你对社会理解挺深啊”。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