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朱利安·巴恩斯出版了一部名为《英格兰,英格兰》的讽刺小说,对英国传统与国家地位大加戏谑。由于英国一直麻烦多多,“以执拗的无理”进行谈判,最终在小说结尾,英国不得不付出代价,被赶出了欧盟。巴恩斯在这部20多年前的小说中写道:“不可否认,这个国家所有人早就达成共识——要完成增长经济实力、提升政治影响、加强军事力量、占据道德高位等目标,但这些现在都被抛之脑后了。”

[英] 朱利安·巴恩斯 著 周晓阳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9-3
“碰巧有点远见而已。”当我们坐下来谈论他的新书时,这位布克奖得主小说家淡淡地说。虽然他只允许自己直接提一次“英国自欺欺人且自虐成狂的脱欧历程”,但在书中结尾的注释中,他坦承《红袍男子》(The Man in the Red Coat)的出版非常及时。这是一部集传记、历史和艺术于一身的优雅小说,它讲述了一名19世纪巴黎医生的人生,主角现在已经鲜为人知。巴恩斯将主人公描述为在闪闪发光的“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中探索黑暗水域的“领航鱼”,那是“一个神经过敏的时代,到处充斥着歇斯底里的国民焦虑,举目尽是政治动荡、危机和丑闻”。
事实上,巴恩斯早在2015年就萌生了撰写此书的想法,那时脱欧公投还未开始。当时英国国家肖像馆举办了约翰·辛格·萨金特的作品展,其中一幅画激起了巴恩斯的好奇心。作品展中绝大多数画像描绘的都是名人,包括穿着红色长袍的妇科医生塞缪尔-让·波齐(Samuel-Jean Pozzi)。图解上说,他是个唐璜式的风流人物。“我第一次看见到这幅画的时候,还不知道它的背景和现在的英国有任何联系,”巴恩斯谈到他第一次看到《在家中的波齐医生》这幅画时的情形,但随着他对那段时期的研究不断深入,二者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极端民族主义、本土保护主义、反犹主义、仇外情绪……那个时代非常可怕,我们现在也处于一个很可怕的时代。”

那么,为什么巴恩斯不再写一部像《英格兰,英格兰》那样的讽刺作品,或者写一部像伊恩·麦克尤恩近期出版的英国脱欧幽默讽刺小说《蟑螂》那样的作品呢?“我是那种需要时间思考如何下笔的作家,”他回答道,“所以我很高兴看到伊恩可以直抒胸臆。他是我的老朋友了,我们关系很亲近,但我们是两种不同的作家。你看,我以前写了我想写的东西,结果现实真的应验了!”

那又为什么不以小说形式讲述波齐和他们圈子的故事,讲述他们的决斗、不忠和“华丽结局”,就像曾经讲述俄国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虚构传记《时间的噪音》,或基于事实改编的《亚瑟与乔治》,甚至是《福楼拜的鹦鹉》那样?“我们通过一幅真实的画像认识波齐,”巴恩斯说,“我觉得如果我将他的故事作为小说来处理,它可能会更普通,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些夸张绚丽的情节只是作者虚构出来的。偶尔回归非虚构类创作的严谨性是件好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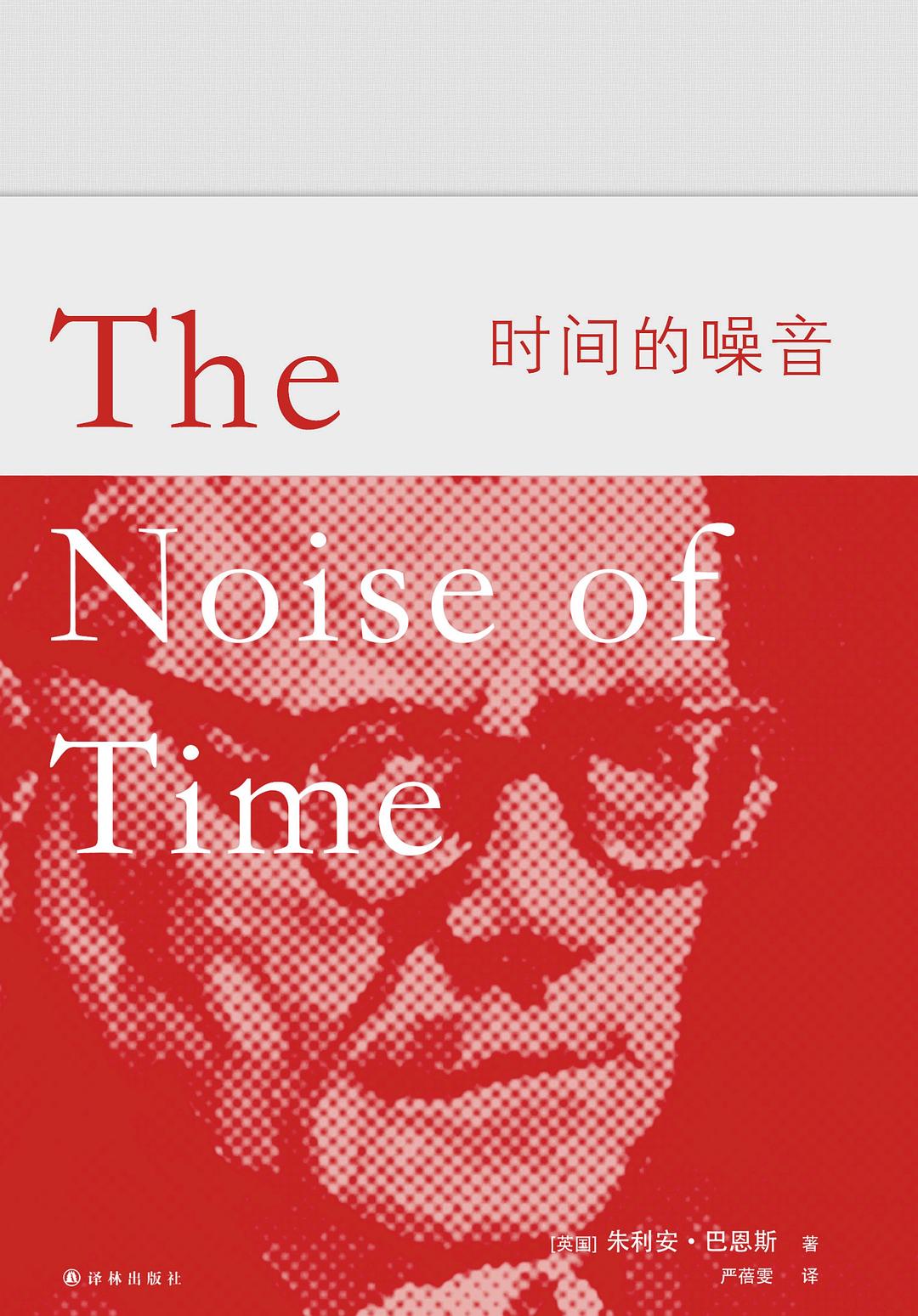
[英] 朱利安·巴恩斯 著 严蓓雯 译
译林出版社 2018-1
1885年夏天,在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王子(Prince Edmond de Polignac)和罗贝尔·孟德斯鸠伯爵(Count Robert deMontesquiou)的陪同下,波齐前往伦敦,开始了一趟“智识与美学的购物之旅”。这引起了巴恩斯极大的兴趣。这个“奇怪的三人组合”——“一个直得不能再直的平民和两个‘希腊化’的贵族”从萨金特那里得到了一封介绍信,送呈亨利·詹姆斯。“他们是‘五大人物’(the big five)。”巴恩斯说。花花公子孟德斯鸠养了一只宠物乌龟,乌龟壳涂成金色,上镶珍贵的宝石。书中的故事虽然分散,但互有关联,细节闪闪发光,全部打磨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巴恩斯式光泽,这本书最初甚至可以定名为“孟德斯鸠的乌龟”。
“《福楼拜的鹦鹉》出版之后,经常有人建议我写《普希金的纽扣》或《托尔斯泰的沙鼠》,要是每次我能得到6便士或1欧元……”巴恩斯憨厚地打趣道,但他又好像并没有在笑。
这种混合叙事方式,在巴恩斯2008年出版的关于死亡的回忆录兼沉思录《没什么好怕的》中早有体现,“就像大脑在思考死亡、家庭之类的事时一样”,他解释道,“这就是我思考的方式,也是我写作的方式。”这也是他说话的方式。采访中他的表达引经据典,不时穿插轶事;他喜欢在写作中充满讽刺地旁敲侧击,这也直接反映在他的言谈习惯上,甚至令人有些不习惯。他好像先向一个不存在的第三方讲话,然后才切入到笑点上。大家经常说巴恩斯“温文儒雅”(他并不太喜欢被描述成有“绅士风度”,因为这显得“有点傲慢”)——他和蔼可亲,但态度略带揶揄;他衣着整洁,说话谨慎(他自认对细节一丝不苟,刚出社会时他曾参与《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工作),他很适合出演约翰·勒卡雷的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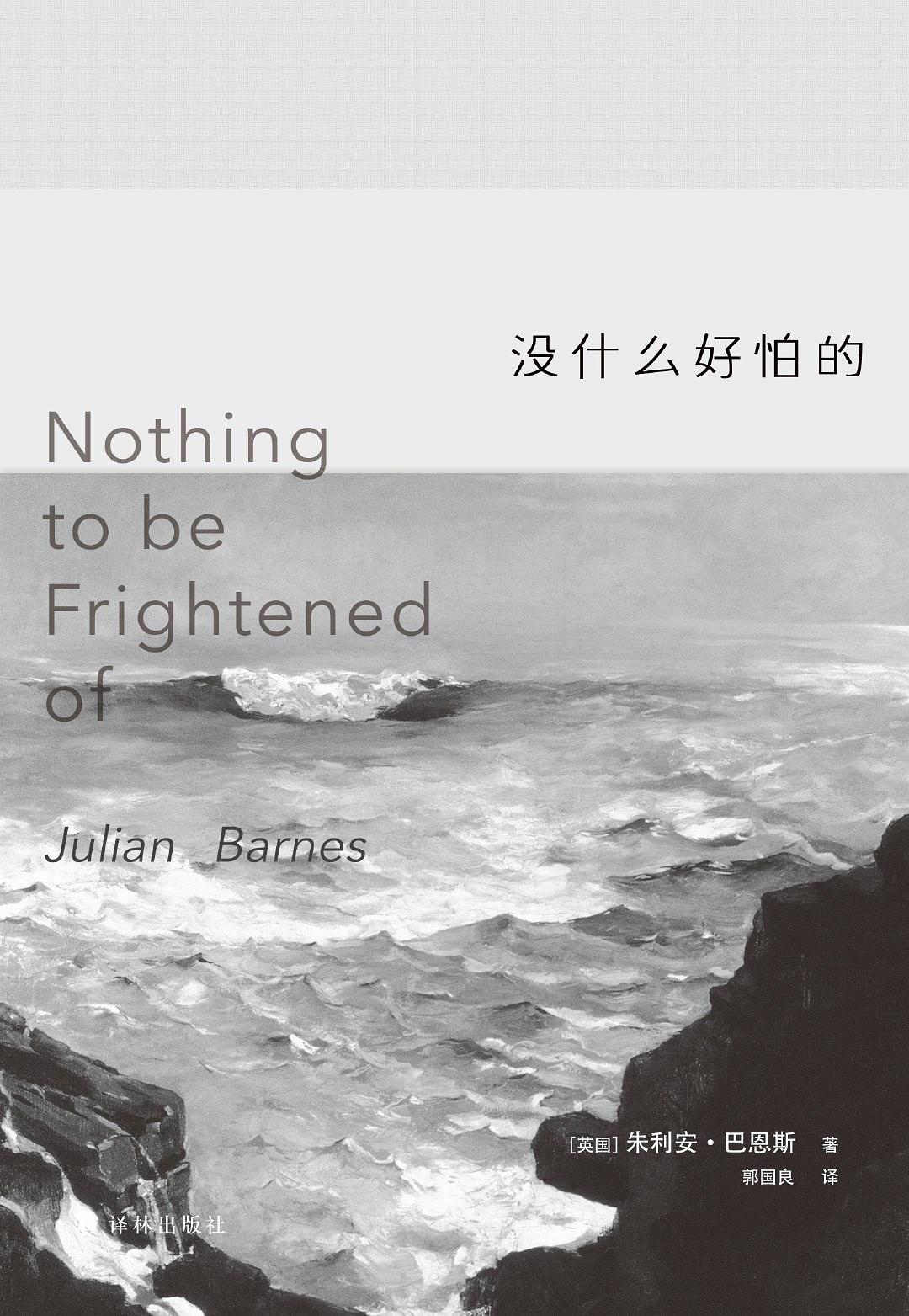
[英] 朱利安·巴恩斯 著 郭国良 译
译林出版社 2019-4
《没什么好怕的》描述了巴恩斯在二战后成长过程中“得体的乏味”。他的父母都是法语教师,在他出生后不久,他们从莱斯特搬到了伦敦西北部的诺斯伍德,也就是他第一部作品《伦敦郊区》中的“都市郊区”。到明年3月,巴恩斯将已踏入作家行列40周年:他写过十三部小说(不包括1980年代以丹·卡瓦纳笔名发表的四部侦探小说),四次入围布克奖决选,并于2011年凭《终结的感觉》斩获布克奖。我们要感谢巴恩斯,因他曾于1987年将布克奖称为“豪华宾果游戏”:把布克奖视作宾果游戏是最终获奖的唯一办法——他现在也这样说。“直到你赢……”
10月20日是巴恩斯的妻子、令人敬畏的文学经纪人帕特·凯伐纳(Pat Kavanagh)逝世十一周年纪念日。“我们相遇时,我三十二岁;她去世时,我六十二岁。”他在《生命的层级》这一令人动容的哀思之书中写道,“她是我的生之所在,心之所向。”三十年来,他们是伦敦文坛上的重要人物,此外伊恩·麦克尤恩、马丁·艾米斯、石黑一雄和萨尔曼·拉什迪等自上世纪末开始活跃的英国“五大作家”(Big Five)也各有纷纭嘈杂。如巴恩斯所写,1980年代就像1880年代,“名气大杂烩”主要聚焦于男性身上。如今,尽管他有很好的男性朋友,“我更喜欢和女性待在一起——她们不会给我那种公鹿互相对撞的感觉,”他表示,“没有什么比女子双人、四人、八人赛艇比赛中的夺冠场面更令我动容的了,我很少看男子比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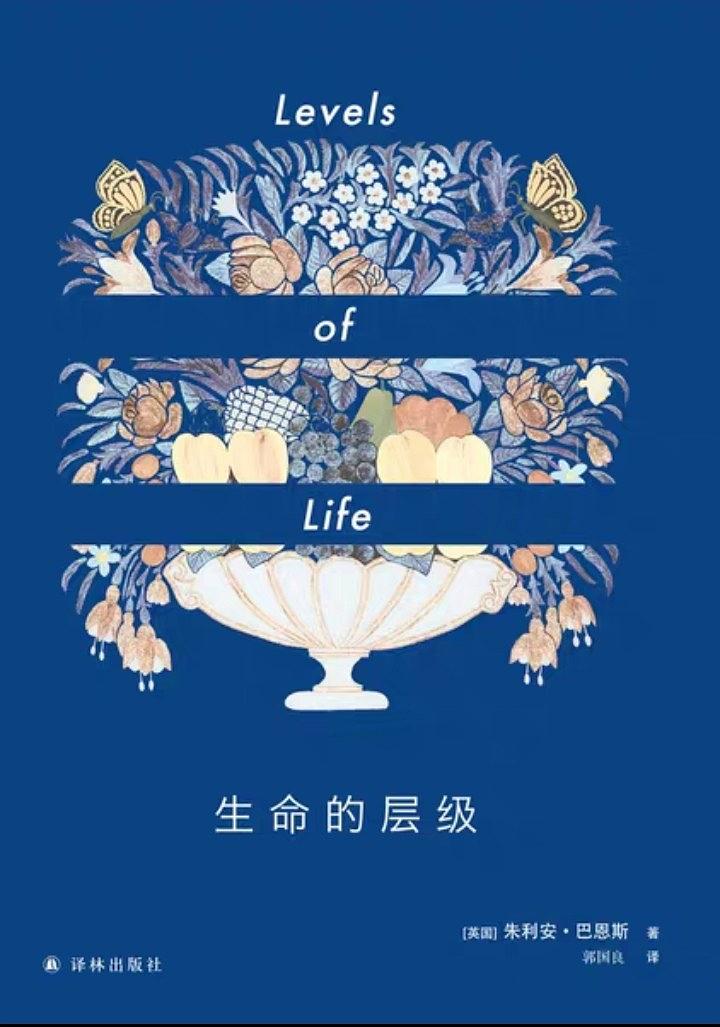
[英]朱利安·巴恩斯 著 郭国良 译
译林出版社 2019-8
他是一个足球迷(莱切斯特城队终身球迷)、罗杰·费德勒粉丝(因为费德勒不像“那些耀武扬威的男人那样说屁话”)、吃货(他在《卫报》有一个名为“厨房里的书呆子”[The Pedant inthe Kitchen]的专栏)、福楼拜狂粉(他对福楼拜的热爱始终坚定不移)。如巴恩斯所言,从《伦敦郊区》开始,他的工作可用其1996年短篇小说集《穿越海峡》的题目来概括:在海上漂泊,抛锚在某处。《红袍男子》的撰写也不例外,副词“法国地”(Frenchly)放肆地贯穿全书。他的小说以对英国国民性的冷静剖析和欧洲式的嬉闹而闻名,正如他母亲所指出的,书中有大量“污言秽语”。“我以前确实在书里写过与性有关的内容。”他不无幽默地说。但在法国,这个他拥有一批忠实追随者并于2017年被荣誉军团勋章的国家,他却被视为典型的英国人。此前有法国记者采访他,在报道中写他早上自己遛狗,下午修剪草坪。但是他没有养狗,而且每次修剪草坪“都不情不愿”,他笑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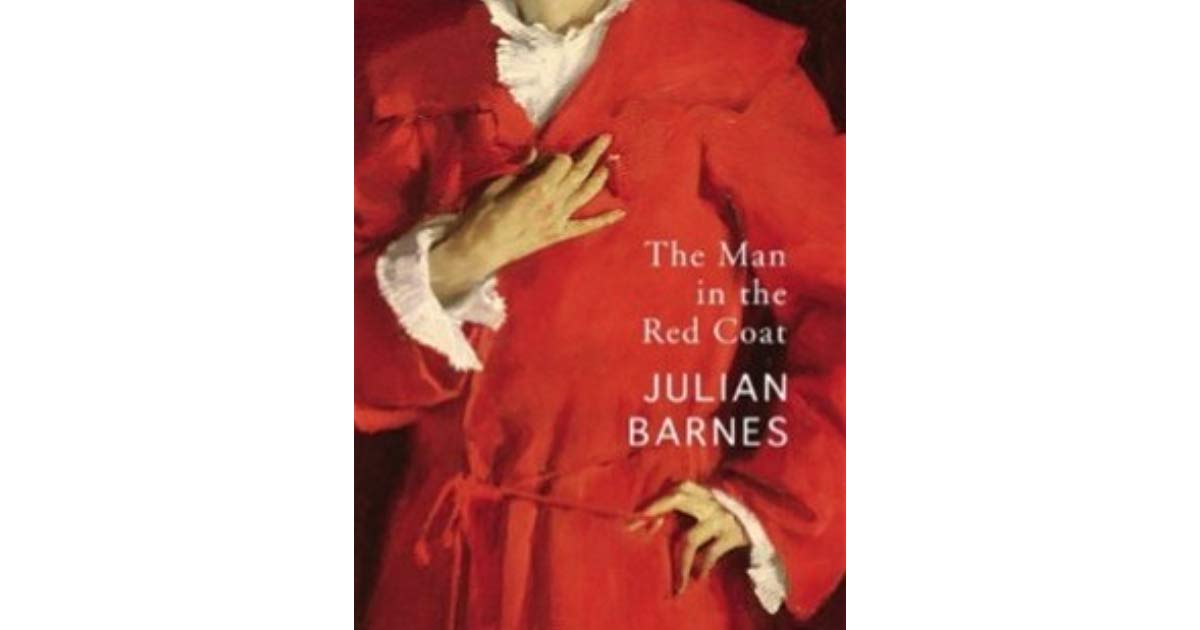
法国人“一直对我很好”,他说,“他们几乎不假思索就引进了《福楼拜的鹦鹉》。要是有哪位籍籍无名的法国小说家写了一部颠覆、半虚构的狄更斯传记,英国出版社不见得会很热情。”巴恩斯去年的新作《唯一的故事》(The Only Story)讲述了一名19岁大学毕业生和一名比他年长得多的女子,在绿树成荫的萨里郡发生的爱情故事,法国人很快就把它当成了自己的故事:“啊哈,这真像马克龙夫妇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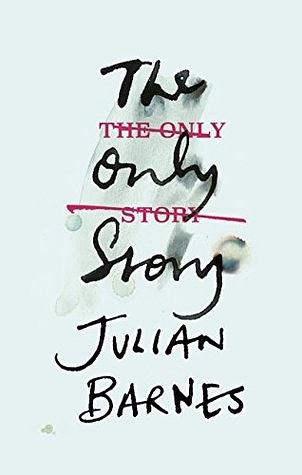
Julian Barnes / Jonathan Cape / 2018-2
巴恩斯认为,马克龙总统在英国脱欧问题上,与英国政府的沟通“受到了默克尔夫人的阻碍”。“我认为他们会对我们施加更大的压力。如果我们的首相公开称法国人为‘狗屎’,你还能指望什么?我们的前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说欧盟就像苏联。而更前一任外交大臣约翰逊说欧盟在欧洲的计划和希特勒在欧洲的计划没有两样。你觉得他们会轻易放过我们吗?(我们)那么幼稚,那么愚蠢,”他继续道,“我们马上就要就贸易协定展开谈判,谈个十年也未可知。他们总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拿到钱。”
他对英国政治精英的狭隘感到绝望,他支持“几乎所有杰里米·科尔宾的主要政策”:核裁军、铁路部门重新国有化、取消私立学校的慈善地位、向富人征税。
自1983年以来,巴恩斯一直住在伦敦北部塔夫内尔公园的同一幢房子里,在同一个书房和同一台IBM 196c电动打字机上敲字。他的电脑用来看新闻,这“极具创新性”。但在写《亚瑟与乔治》的时候,他的打字机和备用应急设备都坏了,这也许是他因嘲笑主人公柯南·道尔的唯心主义而受到的惩罚。“我想,‘上帝——你真的这样做了!’”他开玩笑地对着天空挥舞着拳头。他在电脑上写了三章,然后打印出来,但“读起来不像我写的”。这不是“松散、流畅的初稿,我最后修改了四分之三”。麦克尤恩喜欢电脑的剪切和粘贴功能,他认为这是“人脑的反映”,“但它不是我大脑的反映,电脑沉默不语,还很迟钝。而电动打字机有一种可爱的哼哼声,它会发出咔嗒、咔嗒、咔嗒、咔嗒的声音。它好像在咕哝:‘您空闲的时候就来哦,我一直都在呢。我已经做好打字的准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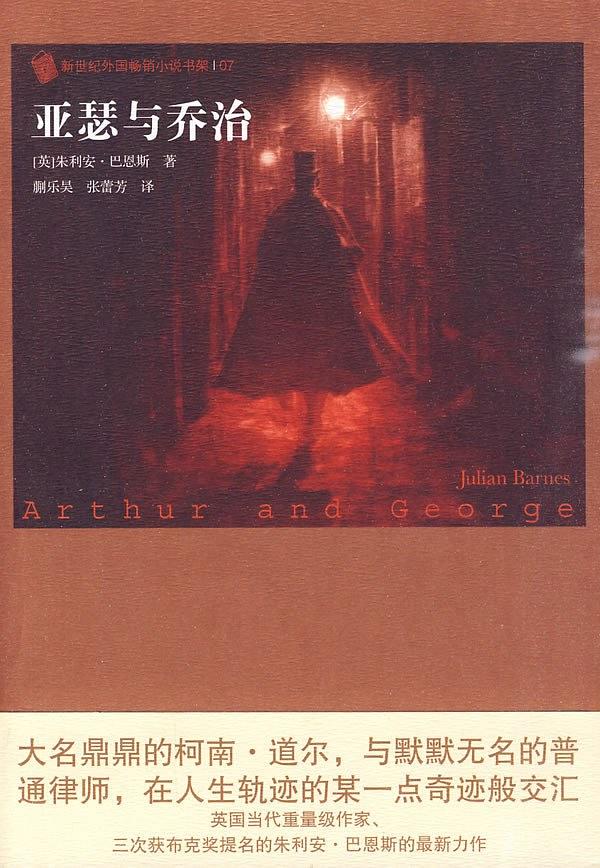
[英]朱利安·巴恩斯 著 张蕾芳 蒯乐昊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4
他同样不甚喜欢一面写作一面听音乐,因为这明显证明“你没有自己的乐章。(听着音乐)怎么能听到脑海中句子的节奏?”他严肃地反问。巴恩斯不会在创造人物之后自问他们会发生什么,而是会问“他们应该做什么”。“两性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比别处更明显、更直接,有些人可能认为我对波齐的某些行为轻轻带过,”谈及这位“屡教不改勾搭成性”的医生,他坦言,“我把我可以肯定的证据都摆出来了。但这些发生在120年前的床帏秘事,只要没有暴力、虐待或强迫,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喜欢写作,甚至愈加喜欢这项工作,如果几天不动笔,他就会变得“暴躁”。“我喜欢写作时的孤独。我总能体会到这一点。”凯伐纳去世后,他依靠写作保持清醒:“作为一名作家,你的好处是能够清楚地记录下所有发生过的不幸。我并不是说这会让人更有耐受力,但这确实意味着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从十几岁开始,巴恩斯每天都在思考自己的死亡。“我就是这样,”他的作品可以解读为穷其一生都在写的关于衰老、记忆和不可避免走向灭亡的专题报告,“基本都是这些。”但是73岁的他精神很好。与波齐在一起的时光让他感到很快乐,而《红袍男子》也并不像他许多作品那样忧郁。“也许我会开始书写年轻和快乐。”他说。
但对于目前的僵局,他只能谨慎地保持乐观。“我认为我们必须非常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我们得表现友好,找到大家的相似点和弱点,”他表示,“但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
(翻译:刘其瑜)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