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安德烈亚·隆恩·朱的作品有点像处于地震的断裂带上——不可否认,基础正在动摇。去年她发表在《n+1》(美国文学杂志,主要刊登社会评论、政治评论、杂文、艺术、诗歌、书评以及短篇小说——译注)上的文章《论宠爱女人》,开启了一些人所谓的第二波跨性别研究,挑战了传统跨性别叙事中的固有特质。朱提供了一个大胆的选择:或许性别不是“此人是谁,而是此人想成为谁”的问题呢?她提出,“性别转换表达的不是身份的真相,而是欲望的力量。”
她因为痛批《跨性家庭》制作人吉尔·索洛韦(“仅仅因为自视甚高也不能保证能写出这种垃圾”)以及布莱特·伊斯顿·埃利斯(一本“毫无必要的书”)的作品而博得大名,但是神秘的欲求仍然是她最能引发共鸣和最具煽动性的主题。她在《纽约时报》上撰写了一篇专栏文章,这篇文章讲述的是她对阴道成形术的渴望,正如文中所说:“这是我想要的,但不能保证它会让我更快乐。事实上,我也不指望它能做到。但不应该剥夺我做这件事的权利。”
最近,我在华盛顿广场公园碰到她,跟她聊了聊她的第一本书《女性》,不出所料,这本书源自一种无畏的自负:“女性不是生物体的一种解剖学或遗传学特征,而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对朱来说,“女性”是渴望成为他人欲望的载体。在这种观念下,性别不只是由自我定义,也由他人定义——性别表达的是他人之欲。
出于篇幅和表达流畅的考量,以下对话经过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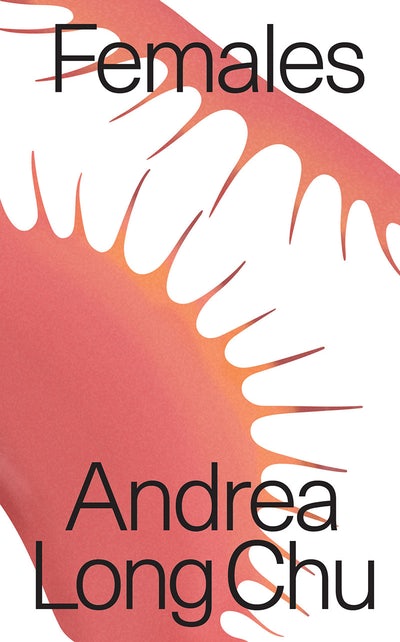
卡莉·希区柯克(Callie Hitchcock,作家、记者):我第一次知道你,可能和大多数人一样,是通过那篇《n+1》上的文章。现在的你会如何评价那篇文章?在那之后你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安德烈亚·隆恩·朱:我觉得它太长了,大约有6300个词,像个应该稍作修整的花园。但我觉得那篇文章还不错,它也真的改变了我的一生。老实说,它对我生活的改变,就好像变性带来的改变。我在推特上讲些笑话,基本上也就100来人看,非常非常少。然后,突然在一天之内就出现了所有这些关注。在之后的几周里,我收到了来自各大出版商的代表和编辑的讯息。我写这篇文章也不是为了闯进这一行,或者是什么别的目的。当时我就是个研究生。我以为这篇文章过于小众和理论化,但却引发了巨大的反响。

希区柯克:“生来如此”的论点似乎已经有点过时了,但当时似乎还没有空间去提供一个替代品。
朱:当涉及跨性别叙事时,个人随笔(personal essay)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种形式的体裁惯例,迫使你作为一个跨性别人士,去写一种特定的出柜故事,但是我的变性根本不像出柜。它不像是从衣柜里出来,而更像从你家里的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或者像是搬进一个新公寓。我还从没看过这类故事,我觉得这是一种我们需要的叙事。现在我收到一些人的邮件,说他们因为这篇文章而决定变性。
希区柯克:你觉得这本新书怎样符合了你对欲望主题的思考的变化呢?
朱:在《女性》中,欲望的隐喻转变为自我放弃或顺从。我的欲望源于自我之外,它是外部的,我是接受者。但我也把它当作自己的,不是纯粹外在的——如果真的只有纯粹外在,那只能是强迫,对吧——只不过有人想让我做点什么,或者社会想让我做点什么。但它不仅仅是“哦,我男朋友想让我穿这件衣服”,而是“我想穿这件衣服,因为我想表现我男朋友对我穿这件衣服的渴望”,所以它更微妙。我认为这种区别很重要,因为它不仅仅是外在的压力,或者与你完全疏远,它同时既是疏远又是亲近,既在外面也在内部,在渗透的框架之外仍具有意义。就是这样,我认为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希区柯克:所以,有一个外部标准被请进了内心世界。
朱:是的,我的行动代表着这个世界,或者另一个世界。我经常发现自己处于这种状况,就好比我在拍摄作者照片时,我把它们给我的女朋友看,或者给我的编辑看,我想知道他们喜欢哪一个。其实我不是想让他们挑一个自己喜欢而我不喜欢的,我是想让你选一个你喜欢的,然后我想让自己也喜欢它。我想知道这是你想要的,这样我就能做你想要我做的事。它与强迫不同。它是发自真心的。想想那些基督教妈咪博客的博主,她们谈论的是如何发自真心地为她们的丈夫服务。关键是,当它真的发生时,它不会是你的丈夫让你做某些事,而是你自己做某些事,因为它已经内化为应该怎样做——你成了你丈夫欲望的容器。
希区柯克:你书中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是,我们都是普泛化的女性,但女性是我们所选择的身份,因为我们所决定的特性是“只是女性”。朱迪斯·巴特勒有一句名言,“男性将否定和贬低的化身投射到女性领域,有效地将身体重新命名为女性。”我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决定被动性只适合于女人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什么被动性是如此的禁忌或不受欢迎,以至于我们想要把它投射到远离我们的地方?
朱:我想这是因为它具有破坏性。你会死亡。在女性特性的纯粹无介入状态下,如果要去体验自己的女性特性,那么你将被经验的力量完全压扁或彻底击溃。面对这种情况不可能坚持下去。
希区柯克:在书中,你提到了小野洋子的《切片》表演,她坐在舞台上,人们拿一把剪刀,可以做任何事。
朱:是的,所以它可能是无目的的。它将会是毁灭。如果你真的想要进入欲望,存在的状况就是成为受支配者的状况。从现象学来说,我就是世界发生的事件。一方面,经验就是我的全部。我是世界的王和主人,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世界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这就是曾活着的每个人的真实状况。同时,在存在论的等级中,这可能是最低的位置——也就是说,在这之上,在这之前,在这个背景下,世界正在发生。永远是伴娘,决成不了新娘。
希区柯克:成了新娘会是什么样?
朱:不可能成为新娘。它是在世界中成为“我”所投下的阴影。中介的一个稻草人。
希区柯克:所以,理想情况下,你希望人们如何使用这本书或这一理论?
朱:我认为本书中确实有一种性别模型,它不同于性别理论中流行的性别模型。例如,书中所说的性别是他人性欲的表现,实际上是以一种实质性的方式说什么是性别,而不是说性别差异。你们有一大堆的奖学金,关心性别如何改变、如何建构。但这些理论并不能解释是什么让性别成了性别,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
希区柯克:我觉得你的书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即为什么我们居然会有性别。
朱:对,它到底是什么呢?人们会告诉我们,性是社会建构的,种族是社会建构的,美也是。大多数事情可能都是社会建构的。即便这是真的,那性别是什么呢?它属于一类被称为社会建构的事物。这意味着让性别成为性别的东西,不可能是社会建构的事实。一定有什么东西能让它与众不同。
性别操演(朱迪斯·巴特勒提出的概念:性别与性征无关,它是被社会演化出的观念;性别被看作是天生的,即性别被看作“与性征有关的”,是为了保证对繁殖效率以及男性优势地位的持续维护——译注)已被主流化,并或多或少可以和社会建构互相替换。它强调了性别的习惯和行为,所以它确实透露了更多的信息。但它仍然不能真正解释,为什么性别是性别,而不是其他东西。
总之,我需要一种不同的性别研究范式,我认为这一新理论如果作为一种新的范式,将会有随之而来的益处。
希区柯克:所以在这一切讨论之后,现在对你来说,性别是什么?
朱:性别是他人性欲的表现。
希区柯克:性别是让正确的人渴求你的一种机制。
朱:确实。并且如果没有这种成分,我觉得你就无法让它说得通。
(翻译:鲜林)
来源:新共和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