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东方历史评论》杨靖
十九世纪中期勃兴的商业和市场是贯穿爱默生演讲始终的主题。被誉为市场“先知”的爱默生顺应了这一时期美国文学市场风气的变化,成为市场追捧的对象,并被打造为文化偶像。通过研究爱默生的演讲、写作与出版等市场行为,可以发现他并非“美国物质主义风尚的批评者”,亦非“美国哲学的绅士传统”的缔造者——恰恰相反,作为清教思想与实用主义精神结合的代表人物,爱默生代表了美国文学由高雅向通俗的历史性转变。爱默生在文学市场的成功,表明他在“超验主义和富兰克林之间取得了最佳的平衡”。
1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1804-1883)是美国超验主义代表人物,号称“康科德圣人”,但鲜为人知的是,他也被时人誉为市场的“先知”。1832年,爱默生愤然辞去波士顿第二教堂牧师一职,按一般传记作者的说法,是由于他不满于教会礼仪的陈规陋习。然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却表明,与其说冲冠一怒为礼法,毋宁说这是他权衡利弊后的审慎选择。
爱默生为何要放弃教职?他在文学市场取得成功的原因何在?本文认为他的这一选择乃基于对十九世纪中期美国文学市场走向的把握:爱默生顺应市场风气的变化,迎合市场的需求,由此成为市场追捧的对象,并被打造为文化偶像。他舍弃教堂的布道坛而走上公共的演讲坛,这不仅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也是美国文学和文化由高雅向通俗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爱默生的朋友布朗森·奥尔科特(1799-1888)曾说“公共演讲是美国的发明”——并将这一发明权归于爱默生。而爱默生本人则谦逊地坦承,作为演讲家,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830年代新英格兰兴起的“学园”(Lyceum)运动。学园运动通常由各地方行业协会主导,目的在于普及知识、教化民众。其通行做法是协会筹措专款,并指定专人负责——包括延请讲师、拟定议题、商洽报酬、落实场地等等。一次演讲不仅能扩大演讲人知名度,而且还能获得不菲的报酬,爱默生和他的友人们遂纷纷登上讲坛,利用这一方园地传播他们的思想学说——不过,谁也没有取得爱默生那样的成功。

牧师世家出身,爱默生天然具备演讲家的“布道”特质。他身材高大,声若洪钟,伴随着威严而不失礼仪的形体态度,极具感染力。当然,相对于外表,爱默生演讲的内容更为引人入胜。他本人学识丰赡,而且勤于笔记摘抄——他将个人笔记本称为“储蓄银行”,由此打造出汪洋恣肆、字字珠玑的演讲稿。譬如他在哈佛神学院名为《美国学者》的演讲,连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s)这样的文豪亦为之折服——盛赞其为“美国人思想上的独立宣言”。

演讲的成功,首要因素在于选题。爱默生演讲的题目几乎触及当时美国民众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但不限于183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兴起的禁酒、废奴、教育改革、道德改进以及妇女权益等运动。像十八世纪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历书》一样,爱默生的演讲成为普通家庭的“宝典”——爱默生本人由此也被誉为美国的“先知”。而且,与富兰克林在书中阐明的“致富之路”(The Way to Wealth)一样,爱默生演讲中尽管不乏浪漫派作家对商业及贸易一贯的鄙视与抨击,但总体而言,十九世纪中期勃兴的市场和商业却是其中贯穿始终的主题。
作为哈佛学院训练有素的古典学者,爱默生在演讲中却刻意避免奥尔科特式的“掉书袋”,转而采用通俗易懂的平实之语,许多时候甚至不惜以美国本土的粗砺意象取代欧洲文化传统中典雅的“陈词”——批评家或称之为“本土幽默”,比如他将死读书的人称为“书虫”(bookworm),以“火山渣烤鸡蛋”形容其行事荒诞;将异化的劳动者比作“破碎的残肢”,而他自己则化身为“透明的眼球”——可以洞悉宇宙自然的奥秘。类似夸张新颖的表达是爱默生长期精心锤炼的结果,别开生面,也广受欢迎。1850年代,纽约著名记者威利斯(N. P. Willis)在“商堂”聆听爱默生演讲,偌大的讲堂座无虚席,记者被“挤至墙角,终场动弹不得”。1860年代以后,爱默生如日中天,成为享誉英美和欧洲大陆的文化偶像,其演讲更是一票难求。
2
以商业取譬(analogy)是爱默生演讲的一大特色,也是他在文学市场取得成功的一大奥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劳伦斯(William Lawrence)宣称,一言以蔽之,爱默生的演讲堪称美国“致富福音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的演讲与著作中,爱默生并非丹尼尔·亚伦所说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预言家”,而是对资本主义市场持怀疑乃至批判态度。
爱默生对“商业时代”的厌恶其实与他一向奉持的个人主义信念息息相关,在他看来,自力更生不是必然结果,而是商品交易下迫不得已的牺牲品。为了赚钱,所有人都不得不“日复一日辛勤劳作,还要低三下四,阿谀奉承”。在《论自立》一文中,爱默生借用从商业交易中汲取的意象来表达他的观点,即资本主义正在消除人的独立性:“社会是一家股份制公司……为了面包,必须牺牲自由。”因此,他的结论是,“贸易如今是世界的主人——政府只是热气球上的降落伞”。
在1841年的另一篇演讲《自然的法则》中,爱默生指出,物质利益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充斥着投机和渔利的欲望,而一旦投机失败,农场、学校、教堂以及人的心理都会黯然失色,萧条贫瘠——尽管爱默生一再否认自己对“商业市场”怀有敌意,但很明显,这一时期他对市场的反复无常和剧烈波动所造成的后果充满疑虑。
然而从稍后的演讲《补偿》中可以看出,由于“财富具有道德属性”,爱默生相信具有进取心且工作中诚实守信的人,在交易过程中“有资格不去妥协”,而且“也不会染上铜臭”——此时他俨然已“成为一个工商业资本主义辩护者”。爱默生认为市场的力量足以消弭权威,消解传统,消除枷锁——很显然,他对商业和市场的态度已经开始发生改观。
与此同时,对于促进商贸发展的科学创新,爱默生并非一味拒斥,相反为之欢呼呐喊。如在《论自然》的演讲中,他赞美人类“用铁条铺路,在上面架起一辆载满人、动物和商品的列车,像老鹰或燕子一样,在乡间飞来飞去,从城镇之间来回穿梭……他去邮局,就有邮差为他跑腿。他去书店,就有作家为他读为他写”。在后来的演讲中,爱默生更是不无自豪地讴歌穿越丛林的列车,“蒸汽机头鸣响的汽笛,有如仙乐飘飘”,对比梭罗对波士顿—康科德铁路开通的嘲讽“不是铁路载人疾驰,而是人背负着铁路”,可以看出爱默生对时代潮流把握的敏锐性和预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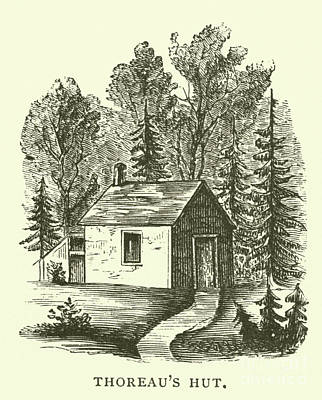
爱默生对商业的赞许也是聆听他演讲的绝大部分听众的共同心声。1851年,爱默生应邀到匹兹堡做演讲。当地店铺老板在演讲之日纷纷关门歇业,不仅是他们本人,而且连同伙计一同前往聆听演讲。在老板们看来,爱默生演讲中寓涵的“商业价值”远大于伙计一天的劳作。事实上,爱默生本人也发现,听众对具有“实际商用价值”的演讲话题更为关心,对于抽象玄妙的哲学命题则明显缺乏热情,他本人在随后的演讲中也相应作出了调整。
1830年代,爱默生的演讲年收入不到500美元。1840年代,年收入近千美元(以1946年为例,记录在案的演讲收入约900美元)。此后一路飙升,至1860年代达到高峰,公开演讲每场不低于100美元,小型的系列“谈话”通常持续一两周时间,收入过千。保守估算,此时爱默生的演讲收入已达到甚至超过他的总收入(稿酬、版税、银行利息、铁路股票等)的一半之多。对于商业演讲所取得的成功——正如他的著作出版一样——爱默生清醒地意识到这是市场的合力:由出版商、读者以及听众所组成的文学市场需要打造偶像。1870年代,爱默生曾不无感慨地说:“老年是最好的广告。你的大名在书上反复出现,证明你的书值得去买。”
3
事实上,与同时代的名人如诗人朗费罗相比,爱默生在出版市场还算不上长袖善舞——朗费罗专心致志隐居家中写诗的诀窍是先将单篇的诗歌投给文学期刊,取得一笔稿酬;然后每过几年,将散落在各处的诗篇集结整理,作为精装本的诗集出版发行——不仅能够再次取得稿酬,而且可以出售版权。至于《伊凡吉琳》这样的长篇佳作(作者对其市场效应信心满满),则直接出单行本。值得注意的是,朗费罗每次推出新诗集,总要煞费苦心,将先前的诗歌打乱次序,重新编排,并重新撰写序言,以致不明真相的读者以为是一部新诗集,乃慷慨为之付费。
朗费罗这种“回收利用”(recycle) 兼移花接木术,爱默生本人并不陌生。爱默生写作的第一步就通常是从自己的日记(或“矿藏”)中汲取素材,然后逐渐展开成为零星的段落,最后再通过特定的主题将上述段落连缀成文。由于讲座日程密集,又缺乏经纪人,所有行程安排、酒店旅馆乃至酬劳费用,通通需要他亲自打理,因此他的写作往往是见缝插针,忙里偷闲。这样的急就章一般而言难称佳构,然而它的好处是,作家本人在亲口诵读一遍之后,可以根据现场听众的反应进行增删修改,然后再讲,再改,如是循环。到《随笔集》定稿之际,一篇演讲稿往往要经过十遍、数十遍的反复打磨润饰,加上爱默生一贯谨严的工作态度,遂成传世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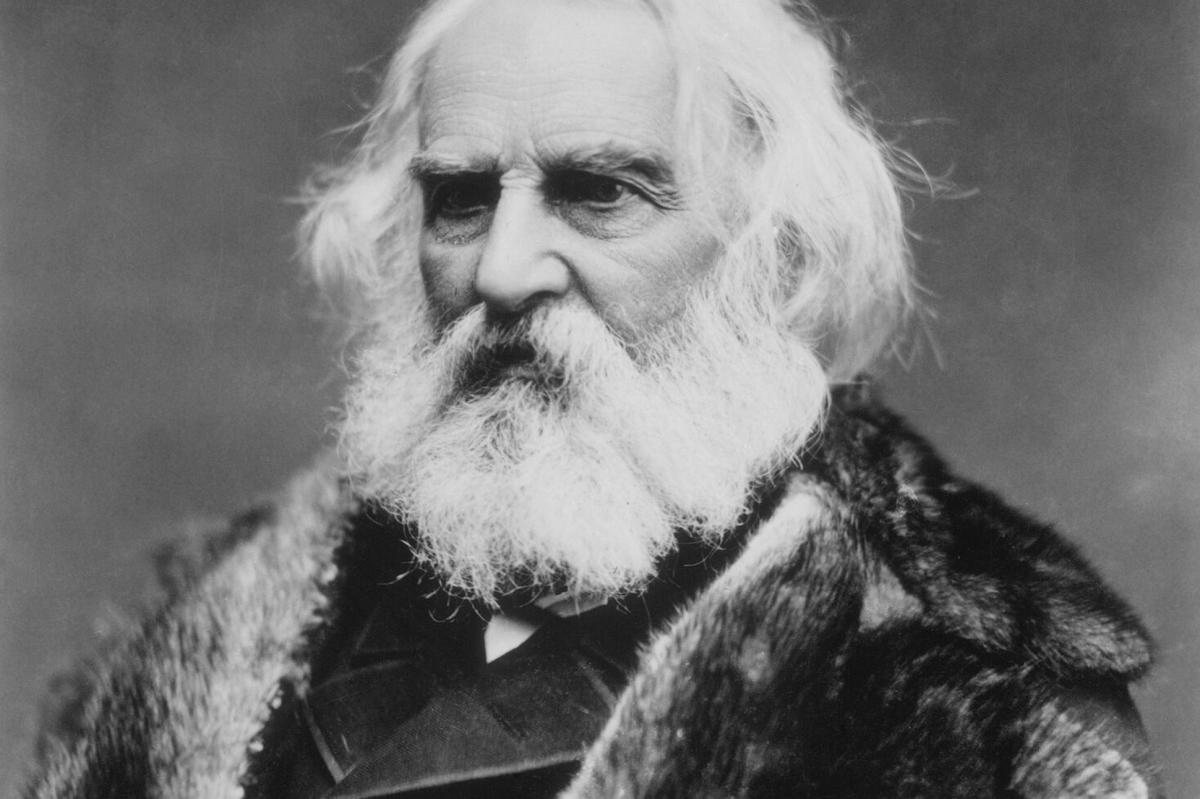
爱默生对待写作与出版一向高规格严要求,许多时候近乎苛刻。早在1840年代初《日晷》编辑发行之际,作为共同编辑的玛格丽特·富勒(1810-1850)和作为出版商的皮博迪小姐(Elizabeth Peabody,1804-1894)便对此不无微词。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奥尔科特等人的诗歌、梭罗的随笔以及富勒的论文,无一不经过他的精审校订。不仅于此,关于排版与标点,字体与字号,以及空行与留白,他也是再三沉吟,不到下厂开机的一刻,绝不肯善罢甘休。更有甚者,前一天已定稿的版面发现问题后可能被全盘推翻,另起炉灶——全然不计代价与后果。皮博迪小姐曾屡次警告他,刊物已陷于亏损,再也禁不起如此折腾,然而等到下一期刊物,他还是我行我素。而这样一种一丝不苟的态度也是他日后在文学市场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众所周知,爱默生对诗人钱宁极为赏识,赞赏他诗歌的灵性与天才,并誉之为美国新诗歌的代表人物。但与此同时,他对钱宁漫不经心的态度也提出了严厉批评。另一位天才诗人维里(Jones Very)也因为诗作中的拼写和标点错误遭人诟病,更受到爱默生严厉指责。对待旁人如此,对待自家的文字,爱默生的态度更为较真。作为英国浪漫派诗歌的终身爱好者和捍卫者,爱默生坚信诗人肩负神圣使命,其文字理应具备某种神性,不容亵渎。他曾引用法国作家蒙田的名言“切开这些字词,它们在流血”,形容鲜活的文字是文章的生命所系。“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后世评论家认为爱默生《随笔集》(第一、二卷)谋篇布局明显胜过《论自然》,其晚年随笔更是炉火纯青,臻于化境,正是他几十年如一日悉心锤炼的必然结果。
但在十九世纪中期的文学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既非“字斟句酌”的作者,亦非“盲目热情”的读者,而是“霸道的”书商(出版商、印刷商)。为帮助梭罗出版他的处女作,爱默生不惜多方奔走,殚精竭虑。梭罗作品在门罗(Monroe)和蒂克诺与菲尔兹(Ticknor & Fields)两家公司之间数度辗转,就是因为爱默生想为他争取一个相对公平的合约。在致老友弗内斯(W. H. Furness)的信中,爱默生宣称梭罗是“康科德的伟人”——《在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的销量一定会超过他本人的《随笔集》(第一卷)——并恳请老友说服出版社以最优惠的条款出版该书。此外,他还一再敦促出版家凯里(Matthew Carey)出版诗人钱宁的诗作。“钱宁是天才诗人,”爱默生说,与之相比,他本人只能算是“业余诗人”;并且建议,他本人的诗作可以作为附录收入钱宁诗集,以扩大后者知名度(后来由于清高的钱宁不肯“附骥尾”而作罢)。当获得凯里先生首肯后,爱默生激动地赞颂对方是希腊悲剧中的“降神机”(Deus ex machina)。另外,自第一次访英归来,爱默生便自告奋勇担任卡莱尔在美国的出版代理。此后,《旧衣新裁》《法国大革命》等作品版税源源不断汇往英国,令穷困潦倒的作家感念不已。作为回报,卡莱尔将爱默生早期的一些演讲随笔集结成书,并撰写序言,为之摇旗呐喊,令后者在英国市场声誉鹊起——而此举反过来又造成爱默生作品在美国本土市场销量激增。

可见,与爱默生此前对商业和市场持强烈的怀疑态度不同,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爱默生的态度产生了转变:由憎恶、怀疑到大唱赞歌。爱默生相信商业在旧大陆败坏人心,在新世界则可以解放人性(并为人类带来世界和平)。他在演讲中不止一次宣称,他尊重的不是财富,而是财富带来的自由和自立——或者像评论家所说,爱默生在“虚幻的理想主义和自利的实用主义”之间游刃有余,左右逢源,是因为爱默生将追求财富视为“富有浪漫想象的探险”。吉尔摩(Michael T. Gilmore)在《美国浪漫主义与市场》一书中更据此宣称爱默生是十九世纪文学市场的“直接受益者”。
对比一下1840年代后期与1850年代爱默生的演讲,不难发现从主题到内容,都有明显变化。从超验的理想主义者到唯物的实用主义者,爱默生的1847—1848英国巡回演讲对他的思想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与1833—1834年爱默生初次访英不同,这一次他是受卡莱尔、狄更斯等名流的邀请,这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了他的知名度,另一方面自然也不乏现实的经济考量。此外,与经济收入相比,英国的演讲之旅还增添了他的阅历,拓宽了他的视野。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地质学家莱尔(Charles Lyell),物理学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社会改革家欧文(Richard Owen)等。他不仅亲眼看到1848年欧洲革命背景之下英国的社会现实,更对英国学者注重社会实践的精神大为感佩。1850年代以后,在他的演讲稿中,宣扬激进革命的论调日渐式微,更多代之以平和的社会改良和道德改进——因此也有学者声称他的政治立场日益转向保守——正如亨利·亚当斯所说,“爱默生抨击社会一切陈规陋习,但行动上却谨守法度不逾矩”。梭罗在1850年代以后与他分道扬镳,渐行渐远,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他的“世俗成功学”多有不满。
爱默生在演讲中传布的关于“成功的流行观念”在新英格兰地区备受欢迎,显然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众所周知,与天主教徒相比,清教徒虔信上帝,但同时更注重“事功”(不似天主教徒以终日跪拜祈祷为最虔诚的崇奉上帝之道),由此转向经营之道。对此,托尼(R.H.Tawney)在《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中解释说,清教徒在自己的工作场所听到上帝要其劳动的召唤(Calling,天职),于是,他立即为自己设定了活力和秩序的原则,“这种原则使清教徒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商业竞争中都成为不可战胜的人。……受到自我检查、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的锻炼,他成为一个实践的苦行僧,他的胜利不是在修道院获得,而是在战场,在会计所,在市场”。或诚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中所言,正是清教徒勤勉节俭的生活方式和一丝不苟对待工作的态度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条件。韦伯心目中的代表人物是既不乏高远理想又富于实践精神的富兰克林——韦伯称之为“世俗禁欲主义”的代表。尽管“资本主义”一词要到南北战争之后才正式出现,但像富兰克林一样,爱默生也早已兼具一种超乎同时代人的“资本主义精神”——早在1830年代金融危机期间,波士顿地区六万名工人面临失业,忧心忡忡,而爱默生担心的却是“暴民哄抢银行,令富人的资产蒙受损失”。爱默生的理财顾问沃德早期也是爱默生“康科德文人小团体”的一名青年才俊,后娶富家女成为银行家继承人,爱默生对他的财富及商业成功由衷地感到钦佩——认为他代表了“世俗与理想相结合的美国未来的前景”——这是爱默生本人一贯的信念,也是他在市场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像梭罗、霍桑、梅尔维尔、惠特曼以及坡等浪漫派作家一样,在爱默生的演讲随笔中,对当时兴起的工商资本主义及其市场的抨击可谓比比皆是:比如他的名言“贸易是今日世界的主宰”以及“走出户外,美国俨然是个大市场”。正如另一位超验主义代表人物帕克(Theodore Parker)所说,“金钱是当今的主人,其余一切都是仆从”,这也是浪漫派作家的共性——正如他们的英国前辈华兹华斯、柯勒律治以及拜伦、济慈——痛诋出版商的贪婪,抱怨普罗大众的愚昧,更为自己的怀才不遇而嗟叹。如此怨天尤人,可以视为浪漫作家的故作姿态,或自我投射。爱伦·坡将与之对立的新英格兰文学刊物贬为文化“荒漠”,狄金森将出版痛斥为“拍卖思想”,戴维斯(Rebeca Harding Davis)则不甘于作“文学店主”,担心预付金制度会令她的写作“沾染铜臭”。但事实上他们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恰恰相反,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凡夫俗子,终日也须为生计而奔波。梭罗在瓦尔登湖的隐居,实际上是文学事业(enterprise)的一次冒险。霍桑为了与一帮“乱涂乱画的女人”争夺市场,被迫采取罗曼司(Romance)的叙事策略,并转移相当精力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梅尔维尔不甘心做一名专写海外奇谭的“类型作家”,尝试许多不同题材,可是过分急于求成,被出版社指摘为“粗制滥造”,也逐渐被读者和市场所抛弃。他的名言“钱仇我”(Dollars damn me)不仅是作家绝望地呐喊,也是物欲横流的美国社会现实的写照。与他们相比,惠特曼可谓擅长自我推销和自我包装的行家里手。为招徕读者,他擅自将爱默生的私信印在新版《草叶集》的扉页上,取得了上佳的广告效应。而爱默生本人,尽管在日记中不时抱怨“身价贬值”(depreciation),但从未真正放弃市场。据考证,即便在经济“大恐慌”(Panic)期间(1837-1841),他的听众平均每场仍多达400人,收入稳定且相当可观。一言以蔽之,以爱默生为首的美国19世纪中期浪漫派作家明知大众品位粗鄙,但面对冷酷无情的文学市场,也不得不放下身段,进行自我调节。
4
文学市场的兴起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产物。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将写作活动视同商品的生产活动——文人作家通过出卖劳动获取报酬,完成商品的交换。本雅明宣称作家在街头闲逛,只是一种表象——事实上他们在等待主顾,打算卖个好价钱——“像娼妓一样出卖自己的思想”。 而像波德莱尔一样不肯屈服于市场、采取“反社会”姿态的作家,则注定终身穷困潦倒。伊安·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也指出,十八世纪的阅读群体相当少,因为识字率不高,经济条件也相对贫乏,然而,“流通图书馆的出现,导致文学阅读群体显著增长”。这一现象首先归功于教育的普及以及经济发展——中产阶级越来越多投资于教育,购买书报,而流通图书馆业又极大促进了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同时,妇女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以后,闲暇越来越多,阅读乃成为一种消遣,也成为时尚。此外,书商在文学的商业化进程中功不可没,迟至十八世纪中期,“写作……已成为英国商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在新英格兰,伴随着十八世纪工商业的稳步发展,一种新的商业精神也逐步形成,“它产生于马萨诸塞贫瘠的土壤,鼓励胸怀大志之人抛弃不毛之地,以更加有益的方式发财致富……清教徒和扬基佬构成了新英格兰整体的两个部分……清教是旧世界的贡献,是由英国宗教改革严峻的理想主义创造的;扬基人是本土条件的产物,是由一种实用经济学创造的”。更重要的是,像在殖民地母国一样,在经济发展之后,殖民地人民也对文学文化产生出迫切的精神需求。与此同时,文学也从以往高高在上的贵族的玩物,一变而为大众市场“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商品”。昔日被视为“上帝在人间的立法者”的诗人作家,此时也摇身一变,成为商品的生产者。根据查瓦特(William Charvat)的研究,1820年代是分水岭,似乎突然之间,“欧文和库珀发现他们可以凭借写作谋生,因为读者愿意定期购买”。这一方面意味着作家们无须再仰仗恩主的脸色行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一个庞大而稳定的读者群已经形成——“他们或是自行购物,或是从流通图书馆借阅”。当然,除了作家与读者,书商在文学市场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820年之前,美国市场缺乏版权意识,盗版书横行,书商利润空间很小,也缺少推销图书的动力。但随着阅读人群的迅猛增加,“到1850年,超过90%的成年男性能够读写,美国号称拥有史上最为庞大的公众阅读群体”。越来越多的出版商,印刷商,书商加入到这一新兴市场中来,共同促进了文学市场的繁荣兴盛。
吉尔摩曾论断,“美国的浪漫时代也是市场的时代”。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因为运河和铁路“降低了运输费用,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以印刷行业为例,早期的印刷业具有明显的地域色彩——某几个印刷商可能包揽一个城市的印刷业务,其传播范围也极其有限。但随着交通运输方式的改进,这一行业乃逐步扩展至于全国范围。其次是由于读者群的扩大。托克维尔注意到在专制国家,阅读文学是少数人的特权,而在美国,“人数众多……民主思想与商业精神在文学中实现融合”。读者的口味不同,文学创作亦有高眉和低眉之分。比如1850年代被称为“女性化的五十年代”(feminine fifties)——因为女作家和通俗文学作品很流行——沃纳(Susan Warner)的《宽广的世界》(Wide, Wide World)面世半年就收获4500美元版税,而霍桑《红字》出版一年半仅得140美元。斯托夫人的流行小说,据说单本销量比梭罗、霍桑等人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显示出大众阅读口味的变化以及对文学市场的影响。

凯里是美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兼具广告和发行功能的印刷商”,他在市场取得巨大成功,成为爱默生等人仰仗的金主。书商与作者的关系微妙,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天敌”,但也不排除有时候存在某种“密切联系”。书商要赢利,否则他不愿冒险;而作家更多关注作品的艺术性——两者之间既有矛盾冲突,又有共同利益。梅尔维尔《泰比》有部分描述引起读者“不适”,于是出版商威利(Wiley)立刻推出“删节本”,以平息读者的愠怒。当该书在英国出版时,梅尔维尔授权出版商可“自行删除其中的暴力场景”。出版商普特南(George Haven Putnam)将双方关系定义为“信托关系”(fiduciary)——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例如菲尔兹所在公司大赚其钱,霍桑则收获文名,堪称是互惠互利的典范。可见,此时书商或出版商已成为文学市场的一支决定性力量。对作者来说,市场也许不可预期,但出版商或许早已成竹在胸。一个作家价值几何,市场与出版商一般都能作出正确评判。如何包装,如何打造,目的都是为市场利益的最大化。
伯克维奇 (Sacvan Bercovitch)在考察浪漫派作家与市场关系后曾做出论断:“浪漫派作家不得不根据市场的关切调整他们的写作策略。”以爱默生为例,他一方面抨击“物质主义以及市场制度带来的不公平”,并认为商业文化有损于“个人的自立”,但他在1850年代前后,尤其是第二次访欧归来后,却奋不顾身投向市场——从超验转向唯物,从高雅转向通俗。同样,梭罗尽管也坚信市场败坏人心,一味迎合观众更为可耻,但他与格里利的往来书信中却充斥金钱记录——正如查瓦特所言,此时此刻,“他不单单是艺术家,也是经济人(Economic man)”。
面对新兴的大众市场,作家心理极为矛盾——“因为他既要迎合又要教育他的读者”。但难能可贵的是,十九世纪中期的作家们尽管面对文学市场有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导致他们不能像前辈作家一样恃才傲物,率性而为,但他们也并未完全屈服于市场而放弃自我的艺术追求。梭罗拒绝《纽约论坛报》霍勒斯·格里利的高薪约稿(仿效卡莱尔书评,为爱默生撰写书评100页,稿酬50美元),因为对方提出要从爱默生演讲的未刊稿中撷取大量内容。霍桑由于之前小说涉及宗教的内容而引起道德人士反感,于是被迫采取“曲言式”的叙事策略,游走于现实与历史之间,并取得了很强的艺术效果。即便是出于竞选目的,为老同学皮尔斯总统(Franklin Pierce)撰写传记,他也是抱着一贯精益求精的态度,潜心创作。职是之故,尽管有人质疑其内容的真实性,但也不得不承认该书的艺术性不逊于“任何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著名文学评论家马西森(F. O. Matthiessen)宣称爱默生在“超验主义和富兰克林之间取得了最佳的平衡”,可谓是对爱默生与文学市场关系最中肯的评价。
富勒曾半开玩笑地说爱默生“最擅长衡量价值,以便于市场买卖”——他所结交的朋友,包括富勒在内,在文学市场价值几许,发展前景如何,他无不了如指掌。同时,爱默生在文学市场的表现也可圈可点——除了公共演讲,他在著述出版方面绝对堪称行家里手:他善于从平时的阅读思考中撷取素材,并将此素材加工整理,融入到演讲之中。此后,通过报刊杂志对讲座的报道和节选,上述内容能够进一步提升作者的知名度。最后,经过反复提炼打磨,他又将讲稿内容汇编成册,成为文学史上永久流传的经典——看似顺其自然,其实每一步都是精明算计的结果。帕灵顿在《美国思想史》中断言爱默生是清教主义的忠实传人,是“美国物质主义风尚的批评者”,这明显是对他的曲解。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在《美国哲学的绅士传统》一文中将爱默生与波士顿“绅士派”诗人朗费罗、洛威尔以及布莱恩特等人并列,无疑也是对他的误读。波士顿“绅士派”诗人代表了美国文化中高雅的一面,而爱默生刻意追求的却是它的通俗性,或雅俗共赏。有人据此宣称“文化偶像”爱默生毕生宣扬的是庸俗的成功学——是亨利·詹姆斯等高人雅士避之惟恐不及的美国文化中“粗鄙”与“褊狭”的一面,必须要从美国国民性中加以摒弃;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是美国实用主义思想的源头:它是清教徒-扬基佬的奇妙合体,也是盎格鲁-美利坚民族精神的化身。1980年代,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卡津(Alfred Kazin)在皇皇巨著《美国的进程》(An American Procession)中声称爱默生的这一通俗化转向在美国文学史上意义重大,十九世纪中期以后所有重要作家——从马克·吐温到德莱塞,从海明威到杰兹菲拉德——无不受其影响。由此,“美国文学,在美国革命之后,取得了真正的独立”。
(杨靖,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作者授权刊发,篇幅原因,本文为节选版,注释省略。原文《爱默生的商业演讲——兼论十九世纪中期美国文学市场》载《外国文学评论》2019年第3期)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原标题:偶像的诞生:市场“先知”爱默生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