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一生,也是遍历东亚都市的旅程。从故乡绍兴开始,他去往南京、东京、仙台、北京、厦门、广州、香港,1927年到达上海,在此度过人生的最后十年。最近《鲁迅的都市漫游》由新星出版社引进,这是一本由日本的鲁迅研究专家面向日本读者书写的鲁迅评传,属于岩波书店教养启蒙系列丛书的一册,具有跨文化、跨国家的视角。鲁迅的创作显现出东亚作家与欧洲世界的关系,鲁迅受到拜伦为代表的欧洲浪漫主义诗人影响,从中汲取了个性主义与反抗精神,展示出既接受又对抗的立场;而在阅读接受史上,鲁迅不仅为中国人阅读,也是东亚读者的共同经典。
在《鲁迅的都市漫游》的末尾,作者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文学议题——作为共同被东亚世界广泛阅读的作家,鲁迅是如何影响村上春树的,村上春树又如何继承了鲁迅?近代欧美思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东亚国家应当如何在保持主体的基础上思考和行动,鲁迅文学为之提供了答案;村上春树的文学将当代日本定位于东亚的时空中,其本人也成为东亚共同的现代文化以及后现代文化的原点。
鲁迅笔下的阿Q形象在日本也形成了形象系谱,阿Q代表着缺乏主体性、远离变革的庞大群体,以及那些最终没有能够参加变革的如同旧日幽灵般的人物,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以及村上春树都以阿Q的形象批评战后日本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追溯鲁迅在日本的接受史,早在1937年七卷本《大鲁迅全集》就由改造社出版,鲁迅那时已经是日本读书界不可忽略的名字,由佐藤春夫翻译的岩波文库版《鲁迅选集》(1935)也很有影响力。梳理鲁迅的接受史,也是重读大江健三郎(在日本战后的20世纪50年代)至村上春树(在现代向后现代过度的80年代)的日本文学史。

除了跨文化的视角,作者在书中对鲁迅各个时期的创作论述也颇具洞见,例如对“彷徨时期”的议论——自“呐喊时期”之后,鲁迅进入“彷徨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他创作出了《祝福》《在酒楼上》《肥皂》《伤逝》等更圆熟丰富的作品。与尖锐批判中国传统的《呐喊》集比,《彷徨》体现了深入的省察意识。在彷徨阶段,鲁迅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他虽身处彷徨,但却致力于深化自己的批判性省察。”
藤井省三,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研究生期间即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作为中日恢复邦交第一批中国政府奖学金学生赴复旦大学留学,就是在那个时期他得以前往鲁迅的故乡绍兴,在1995年和2010年他又一次次重访绍兴,也由此窥见了中国城乡的巨大变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鲁迅在《故乡》中所描绘的风景,那个于我留学时期所亲近的仿佛一直在安睡的小城风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绍兴逐渐趋向上海化,”藤井省三在书中写道。结束学业后,他历任东京大学助教、樱美林大学副教授、东京大学副教授、教授,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海外人文资深教授,专攻中国现代文学及鲁迅研究等。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书中摘选鲁迅“彷徨时期”与鲁迅与村上春树关系的两节,与读者共享。

藤井省三 著 潘世圣 译
新星出版社 2020年5月
“彷徨”时期
“彷徨”期鲁迅的心境
在“沙漠上似的”北京,流浪诗人爱罗先珂很快陷入消沉,鲁迅也迎来了自己的“彷徨”时期。短篇小说《故乡》(推定发表于1921年7月)结尾的那段话——“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恰好预示了鲁迅这一时期的心境。在这段日子,鲁迅关注“流浪的犹太人”的欧洲传说,并据此创作诗剧《过客》(1925年,收入《野草》),描写一位中年男子迎着来自西方的催促和呼唤,不停行走永世流浪。有趣的是,这一时期鲁迅还翻译了日本伊东干夫的诗作《我独自行走》——伊东干夫系当时居住在北京的日本人,具体情况不详。
除了永世流浪执着行走的主题之外,这一时期,鲁迅还特别关注“罪”的主题。他的《风筝》(1925年2月)、《父亲的病》(1926年11月)等作品,一再叙写欲对亲人赎罪而不得的痛苦心境。《伤逝》(1925年10月)更是表达了罪与死这两个主题的交织和博弈。涓生与子君因相爱而毅然同居,但结果却是涓生辜负爱情、子君悲伤离世,涓生背负罪孽,陷入痛悔自责。
1923年12月,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当时中国的女大学生热衷崇尚易卜生《玩偶之家》的主人公娜拉,年轻的知识女性们将娜拉视为自由恋爱和女性解放的象征。然而,面对这些憧憬浪漫的女大学生们,鲁迅却一再提醒娜拉出走后的命运将会非常坎坷。他呼吁青年女性们不要被激情和冲动弄昏头脑,不要轻易采取过激行动,而必须要用坚韧的努力去争取独立的经济权。有趣的是,鲁迅在演讲的最后又话题一转,谈到“情愿闯出去做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他再次提起那个奇异的传说,讲到那个“背着咒诅”,“永世不得休息”“始终狂走”的“流浪的犹太人”阿哈斯瓦尔。透过鲁迅的话,可以看到一种充满孤独感的领悟——自己已是罪人,只能永无停息地战斗下去。
对于现代性的深刻省察
1924—1925年,鲁迅相继发表了《祝福》《孤独者》《伤逝》等11篇小说。这些作品后来收入他的第二本小说集《彷徨》。《彷徨》卷头印有屈原(公元前340—前278,战国时期楚国宰相,后抑郁而死)《离骚》中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体现了鲁迅的心境。
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展现了对传统中国的尖锐批判,而接下来的《彷徨》却在深刻省察通过批判传统而获得的现代性。与《呐喊》相比,《彷徨》中的作品整体上篇幅较长,原因是鲁迅的创作心态发生了变化,他虽身处彷徨,但却致力于深化自己的批判性省察。在《彷徨》里,依旧可以看到鲁迅文学的固有主题,即在寂寞苦境中沉默思考,但表现主题的文体却比《呐喊》更加圆熟,叙述视角(譬如爱与死等)也更加丰富。
由于当时汉语中还没有指称女性的第三人称代词,所以直到《呐喊》,鲁迅使用的都是古典文学中的“伊”。而从《彷徨》的首篇《祝福》开始,鲁迅正式使用了《新青年》同人刘半农于1920年6月创制并提倡的“她”字。显然,在描写男女爱情时,“他”和“她”这对第三人称代词使用起来既清楚又方便。但起初的一段时期,由于第三人称代词的用法还不成熟,有的人甚至搞不清这些代词到底指称什么。

《祝福》:技巧圆熟的杰作
《祝福》是鲁迅进入“彷徨”时期后创作的第一篇小说。“祝福”是江南地区的一种民间习俗,即于除夕之夜,烹制鸡、鹅、猪等菜肴供于福神前祭祀,五更时分燃香点烛,答谢神明保佑,祈求来年幸福。在小说里,叙事者“我”于年末回到故乡鲁镇,住在身为地主的叔父家里。第二天,“我”在河边遇到了祥林嫂。这个曾在叔父家里做过佣人的女人如今已沦为乞丐。祥林嫂见到“我”,一再追问人死了以后究竟有没有灵魂,有没有地狱。第二天便是除夕了,可“我”却意外地听说祥林嫂已经死了……于是我的记忆苏醒了,从前关于祥林嫂的所见所闻一幕一幕地连成一片浮现在眼前。
1912年,大清帝国变成了中华民国,但在很多地方,传统的人身买卖婚姻、婆家将死了丈夫的儿媳卖给其他男人的野蛮风俗依然存在。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祥林嫂便饱受了这些野蛮制度的摧残。更有甚者,还有跟她一样为人作佣的妇女用封建迷信来折磨祥林嫂,告诉她女性再婚便是不贞,再婚女子死了也得落入地狱,被阎王爷锯成两半分给两个丈夫。“我”的叔父叔母虽为地主乡绅,但其儒教信仰中满是利己私心,他们只知一己家族的昌盛,不但不想去改变鄙俗迷信,反而唯儒教教条是从,在野蛮的迷信面前助纣为虐。
叙事者“我”是一个“识字的,又是出门”(祥林嫂语)了的新派人物,照小说的描写,应该是某大城市教育界中的人物。但就是这样一个新派人士,当痛苦不堪的祥林嫂向他提出疑惑时,他却仅以“我说不清”来敷衍,立即躲开走人,满脑子想着第二天离开鲁镇进城,去昔日的饭馆儿享用和老朋友一起吃过的当地名菜。小说通过“我”这个软弱的中产阶级分子,叙述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妇女的悲惨人生,同时非常巧妙地描绘出20世纪20年代弥漫中国乡村的闭塞氛围,堪称技巧圆熟的杰作。不过,“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他又是为怎样的目的回到故乡鲁镇的呢?
《在酒楼上》:归乡体验叙事
《在酒楼上》采用了叙事中的叙事形式,讲述“我”归乡后与老友重逢,老友向“我”讲述其归乡体验的故事。叙事者“我”从北方回江南省亲,顺路在家乡附近的S城停留,十年前他曾在这里做过一年教员。他去拜访昔日的同事,却不料他们都已先后离开了这里。于是“我”独自一人来到过去时常光顾的酒楼,坐在二楼,一边喝着绍兴老酒,一边眺望楼下荒园的雪景。没想到,就在这时候,“我”的老同学兼教员时期的同事吕纬甫走了进来。他也和“我”一样,离开S城,先去济南再去太原,眼下在一个同乡(大约是在地方任职的高级官员)家里教书,给孩子教教《诗经》和《孟子》等。两人一边喝酒,一边唠叨此行“还是为了无聊的事”“做了一件无聊事”。原来吕纬甫这次回乡一是为了给早年夭折的弟弟迁坟,二是为了给先前东边邻居的小姑娘送两朵剪绒花发钗……
小说中“我”的故乡离S城“不过三十里”,令人联想起《祝福》中的鲁镇;而“福兴楼”所在的县城则令人想起S城。那里的清炖鱼翅是《祝福》里的叙事者“我”所怀念的青春时代的味道。在小说里,“我”和老同学苦笑着说,两个人都是“飞了一个小圈子”后,又“飞回”了故乡。《在酒楼上》和《祝福》这两篇作品都描写了“我”的还乡,描绘了整个中国的沉闷和闭塞,同时弥漫着归乡者特有的怀恋青春的浓重乡愁。
《肥皂》:中产阶级中年夫妇的生活
《肥皂》写丈夫从外面买回来一块洋肥皂,结果引发了这对中年夫妻之间的小小波澜。主人公名叫四铭,妻子在家糊纸锭贴补家用,长子十余岁,正在读书,下面是八岁和四五岁的女儿。四铭曾是个开明派,戊戌变法(1898年)时主张开设洋学堂,提倡女子教育。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他却变了很多。他为学生呼吁解放和自由而恼火,为女学生剪发而愤然。给老婆买肥皂时左挑右选,让店员拆开包装纸确认里面的肥皂如何,惹得在旁边买东西的学生嘲笑他是“恶毒妇”(old fool)。四铭回到家立即命令儿子查清“恶毒妇”的意思。原本四铭买肥皂的起因是在街上遇到讨饭的孝女,旁边有两个光棍调戏她:“你只要去买两块肥皂来,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四铭听了这话不禁怦然心动,这才买回了肥皂。晚上,诗社的同人前来拜访,询问对征文题目的意见。四铭提议用“孝女行”作题目,并讲起白天遇到的讨饭姑娘。不料诗社的同人听罢居然兴奋不已,大笑起来:“咯支咯支,哈哈!”四铭老婆把刚刚小心收藏起来的肥皂拿出来扔在桌子上,一脸怒气,“咯支咯支,不要脸不要脸……”“只要再去买一块……”
在近代东亚,香味的革命始于肥皂。在东亚近代化、欧化及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身体行为的改造也是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个环节上,于男性而言,兵役和体育发挥了重要作用;于女性而言,香皂比香水和洋装更早出现,成为实践身体行为现代化的先导性要素。
《肥皂》以一块肥皂作为小道具,描写清末变法运动时期的开明派逐渐被时代淘汰,到了五四时期不仅在经济上走向式微,在思想上也趋向保守。除此之外,小说也呈现了一个朴素的中产阶级中年夫妇的家庭生活状态,其间隐约漂游着些许性感的色彩,构成了作品的多重意味。在叙事形式上,《肥皂》与《祝福》及《在酒楼上》有所不同,其主人公并非第一人称叙事者,而是一个第三人称的被叙事者。四铭虽没有归乡,但却于夜里独自一人“踱出院子去”,“来回的踱”。在这个意义上,《肥皂》中的四铭也是一个“彷徨”的主人公。
《伤逝》:遇挫的自由恋爱
《伤逝》末尾署:“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毕”,作品未经报纸杂志发表,直接收入《彷徨》,《鲁迅日记》中也没有任何记载。《伤逝》是一个年轻男人的手记,描写“他”(涓生)向“她”(子君)求爱。两个年轻人不顾父母的反对以及他人的好奇,毅然开始了同居生活。但到了最后,由于生活艰辛以及男性的心态发生变化,两人的爱情终于夭折。这是一个悲剧故事。受到自由恋爱、男女平等这一思想新潮的吸引和激励,一对青年男女毅然决然地结合在一起,但很快遭遇到经济上的挫折,涓生首先产生了动摇,并向子君坦白自己的爱情已经冷却。于是子君被父亲领走,再后来传来消息,子君已经离开人世……
围绕着《伤逝》,研究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人认为作品批判了中国社会的保守和传统,谴责了社会对年轻人勇敢实践自由恋爱行为的扼杀;也有人提出小说的主题在于批判涓生的轻薄以及敷衍的反省;还有人认为小说是鲁迅三兄弟私生活的告白,涉及鲁迅及小弟周建人婚姻的挫折、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失和,等等。例如有日本学者就指出了鲁迅的小说《伤逝》与周作人的随笔《伤逝》的关联:在鲁迅完成《伤逝》创作的九天前,周作人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随笔,题目就叫《伤逝》。随笔的内容是翻译和介绍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悼念弟弟的诗,另外还介绍了比亚茲莱的插图画。(清水贤一郎《另一个〈伤逝〉——关于周作人佚文的发现》,『しにか』1993年5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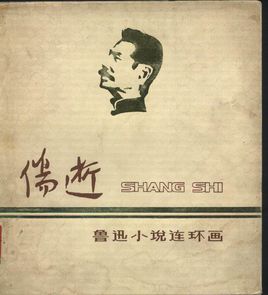
村上春树与鲁迅
后现代文化的原点
事实上,村上文学的主人公们一直都在重复着大大小小的追溯东亚历史记忆的冒险。在1979年发表的处女作《且听风吟》里,主人公“我”在杰氏酒吧(Jay’s Bar)向店长讲述叔父在“上海郊外”“于战争结束两天后踩上自己埋设的地雷”殒命。“是吗……有各式各样的人都死掉了。不过大家原本都是兄弟的”——那个温情地回应“我”的中年男人“杰”便是个中国人。在朝鲜战争(1950—1953)和越南战争(1960—1975)这个中美两国激烈冲突的时代,杰在日本的美军基地工作谋生。作者通过《寻羊冒险记》(1982年)中“我”及好友“鼠”与“满洲国”的亡灵对决的场面交代了杰的灰暗过去。在前一篇的冒险故事《1973年的弹子球》(1980年)中,“鼠”是那样痛苦而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杰”所生活的这个港口城市——“鼠也搞不清楚,为何他的存在会如此扰乱自己的心绪。”
这样,村上春树的“青春三部曲”便成为“我”及其分身“鼠”以及年长二十岁的中国人“杰”三人叙述的历史记忆。之后的《奇鸟行状录》三部(第一部1992年出版,1997年出版文库本)追溯诺门罕事件和“满洲国”记忆,《去中国的小船》《托尼瀑谷》等系列短篇小说则表现了对中国的赎罪意识以及对忘却历史的省察。至于《海边的卡夫卡》(2002年)、《天黑以后》(2004年)等作品,譬如在香港便被理解为“呼吁日本人反省内心潜藏的暴力的种子”。
村上接受的四大法则
另一方面,在华语圈的中国,我们可以发现村上接受的四大法则,即四种形态:第一,台湾→香港→上海→北京,以时针旋转的形式展开。第二,各地的“村上现象”均发生于高速成长的经济开始衰退的时期,台湾为1989年,上海则是1998年。第三,华语圈(韩国也同样)于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民主运动。第四,“森高羊低”法则。“村上热”于1989年由“100%纯情率直”(台湾版的引用)的“森”(《挪威的森林》)开始,但“羊”(《寻羊冒险记》)的翻译介绍却晚了很多,台湾是1995年,中国大陆是1997年(韩语翻译同样),并且“解说”也被省略,与“森”相比算是受到了冷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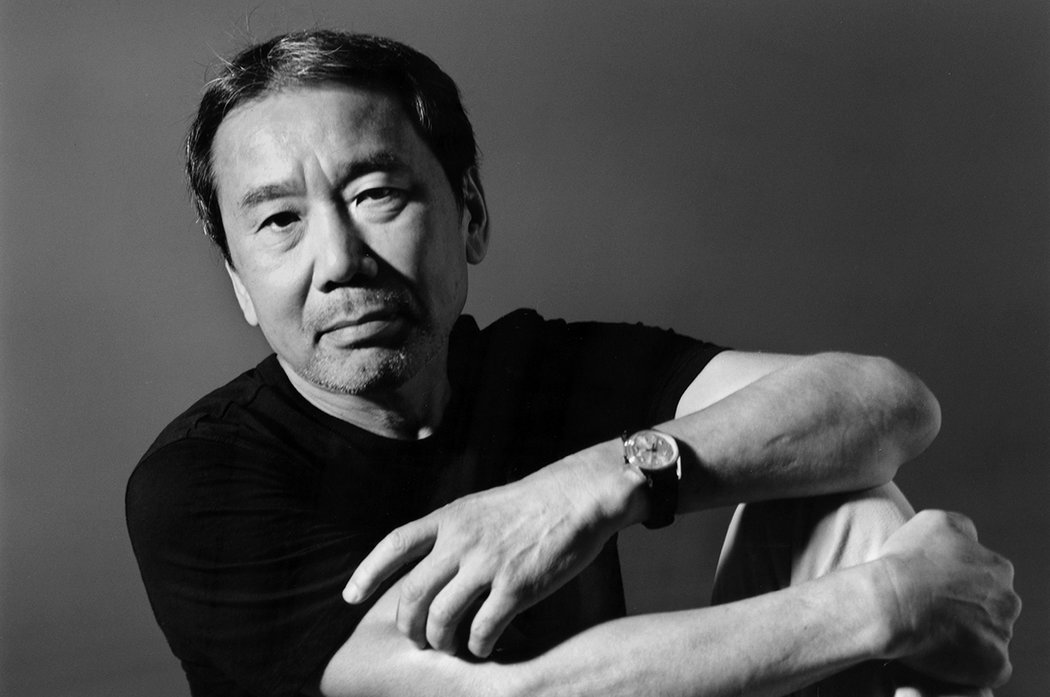
来自鲁迅的影响
说起来,村上春树在高中时代便爱读鲁迅作品,《且听风吟》开头一段有“所谓完美的文章是不存在的,正如完美的绝望并不存在一样”,而鲁迅在散文诗集《野草》中写过“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或许村上是受到了鲁迅的触发。村上与鲁迅有深刻的相通之处,尤其是阿Q形象更是村上从鲁迅那里所继承的重要主题。村上在《青年读者短篇小说指南》中指出,自己在尝试进行严肃的文艺批评时,接触到了《阿Q正传》(1922年),“作者出色地描写了那个与自己所创造的人物完全不同的阿Q形象,浮现出鲁迅自身的痛苦和哀愁。这种二重性深深浸润到作品的内部”。村上自己也写过以“Q氏”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没落的王国》(1982年),之后仍继续描写了Q氏的兄弟们。
在最新出版的作品《1Q84》Book3奇数章出场的女主人公、一个受人雇佣的杀手“青豆”有着奇异的姓氏,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常用来指代和尚——这个名字大概是那个无名无姓的“阿Q”的反转吧。青豆读“有关1930年代满洲铁路的书”,谈论女性护身术时会引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最重要的是,青豆在杀死那个家暴妻子的男人后,为了缓解杀人后的兴奋,在高级酒店的酒吧诱惑一个中年白领,在与他性交时居然嗫嗫私语:“我呀,只是喜欢你的秃头!”
怀有秃头自卑情结的阿Q调戏小尼姑,摸人家的头捏人家的脸,将自己所受的屈辱转嫁到弱者尼姑身上,对此小尼姑只能照例骂一声:“断子绝孙的阿Q!”而《1Q84》的主人公青豆接二连三地向那些DV男子们复仇,两相比较,令人忍不住猜想青豆简直就是《阿Q正传》中小尼姑的亡灵。

村上春树 著 施小炜 译
新经典·南海出版公司 2010年
此外,在Book3中,除青豆、天吾之外,还有另一位主人公,那就是原为律师的牛河。这位牛河,无论在容貌性格境遇还是姓名上,怎么看都像是阿Q的直系子孙。“牛河”二字反过来就是“河牛”,用日语罗马字拼写的话便是“Kagyu”,与阿Q的“Akyu”发音很像。这种在发音拼写上的小游戏,也算是村上式的幽默吧。
《阿Q正传》是一篇短篇小说,主人公是清朝“末代皇帝时期”“未庄”的一个以打短工为生的农民,名叫阿Q。阿Q经常被村子里的人嘲笑和欺辱,但他总会用自己的逻辑来对付,“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于是便产生了一种自我满足。后来风传旨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1911年)要来了,看到地主老财们惊惶万状的阿Q,不禁向往起革命来。不料未庄留日回国的地主少爷们立即组织起革命党,没给阿Q一点参加革命的机会。不久赵家被强盗抢劫,阿Q成了犯人,被抓到衙门受审,他自己糊里糊涂一无所知地被枪毙处死,而未庄的人们则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这一幕。
鲁迅以充满幽默的笔法描写了将自己的屈辱和失败转嫁给弱者以获得自我满足的“阿Q精神”,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了批判,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国家论——没有基层民众的改变便没有革命。鲁迅以严厉批判和感同身受的心绪刻画了阿Q这一形象所代表的中国人的国民性,但对鲁迅来说,所谓阿Q不仅仅是占中国人之多数的下层农民,还有正处于欧化途中的都市民众,乃至包括鲁迅自身在内正在致力于民族国家建设的那些中国人。
对中产社会的根本批判
据说罗曼·罗兰在阅读《阿Q正传》法文译本时曾流下眼泪,而村上大概也是通过阿Q这一形象深刻感受到时代转换时期的小市民之生存方式,并产生强烈共鸣的。1994年6月,为了创作《奇鸟行状录》第三部,村上奔赴诺门罕事件的现场进行采访。在回国后发表的游记中,他对日本战后所形成的“市民社会”,即中产社会进行了彻底批判。
我们将效率低下视为前近代的弊端,并认为它终将导致日本这一国家走向破产,我们一直努力去尝试打破它。但我们并不是将这种非效率性的责任作为自己内在的弊端进行追究,而是把它当作外部强加给我们的弊端,用类似外科手术那种单纯的物理手法进行排除。其结果是,我们的确建成了一个基于市民社会理念、具有良好效率的社会,高效率为社会带来极大的繁荣。……尽管如此,时至今日,在许多社会局面中,我们作为一种无名消耗品依旧在被安静平和地抹杀着……(《边境!边境!》,新潮社,2000年)
从作为传统帝国的清中国到近代民族国家的中华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当中国迎来蜕变之际,总有很多人不愿主动参加变革,还有很多人欲参加而不能。鲁迅满怀激愤和同情,将这些人凝练并塑造成阿Q这一形象,并对新时代的国民性进行了探索。而在日本,村上春树认为,尽管日本人饱尝了侵略所带来的战败苦果,但他们并没有去深入拷问“自己内在的非效率性”,而是一头闯入后现代社会,“作为一种无名消耗品依旧在被安静平和地抹杀着”。村上笔下的Q氏形象便是上述日本人的一种表征,村上显然在以此探求一种内省的市民形象结构。
书摘选自《鲁迅的都市漫游》,由新星出版社授权刊载,选摘时有删节。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