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人,事情总会对我产生影响。密切关注周围发生的事情是我生存的一种手段: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需要这样做,我需要把我的所见所闻写下来。我夜以继日地练习观察,发展出了已故作家纳丁·戈迪默所说的所有作家都有的“超乎寻常的观察力”,甚至可以变成“一种可怕的疏离”。这并没有让我受欢迎。一位朋友对我说,“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忍受一直这么警觉。”另一个说,“我不想成为你所看的东西的一部分。”第三个说,“你那可怕的眼睛一直在观察。”
不过,在性情和经济需要的驱使下,我还是找到了这个习惯的用武之地,并设法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可以谋生的作家。
步入中年的我,在一天上午晃进了一个法庭,我坐下来,全神贯注地听。一天的时间在5分钟内就过去了。我迷迷糊糊出现在大街上,我很感动,深知这就是我一生一直在无知地练习的东西。一个新的世界裂开,我径直走了进去。我静静地坐着。我看,我听,我写,我想,“我生来就是为了这个。”
但现在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我用来集中注意力、用来锻炼我唯一的技能的设备,已经开始磨损。一两年前,渐渐地,我发现越来越难听到人们在法庭上说的话。我慌了——我是不是要放弃工作了?我去做了一个测试,年轻的听力学家说,这种听力损失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是正常的。正常?难道我们都是带着沮丧和焦虑的心情到处走动吗?
他把我带到一个后面的房间,给我看了一排在桌子上摆成一条曲线的助听器。一边是老式的那种看起来像一包粉色泡泡糖的助听器,另一边是一个微小的、没有重量的铁丝和一种不配称之为金属物质的装置。
我说:“我的一个朋友刚买了助听器。他花了一万块钱。我希望我支付的费用比这少得多。”“他的听力损失有多严重?”“他告诉我,在他戴上助听器之前,他已经忘记了鸟儿会唱歌。”“哦,”听力学家说,“你大概需要花一半的钱。”

我花了五千块钱买了一个带音量按钮的精致小钩子,把它们塞进耳朵里,然后匆匆离开。天啊,斯旺斯顿大街上的车流声! 有轨电车的鸣叫!我又可以和我的孙子们一起看《神烦警探》(Brooklyn 99),几乎可以跟上这部剧快速的对话节奏,虽然他们的笑声还是比我多一倍。我只能完全听得懂庄严的、句法复杂的霍尔特警监:这是我对他产生巨大迷恋的另一个原因。

但在法庭上我还是听不见。意志力和听力学家的艺术无法战胜那些建筑中无望的声音系统,无论是高大的维多利亚式大厅,还是现代休息室般的空间,都被笨重的红木所堵塞,闷闷的声音耷拉着,消失在地毯中。
在我放弃并悲壮地蹒跚回家的那天,我瞥见最高法院的外门上贴着牌子。那是一张“对1、2、3、4、6、8、9、10、11、12、13、15号法庭进行声学处理工程”的文物许可证。
太晚了,我已经放弃了。
如果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能如此准确地引用那个牌子上写的字,那是因为我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这就是作家注意事情的方式:你发现了你无法想象有任何用处的细节,你把它们记录下来。当时间追赶上来,你正在写的东西中出现了一点空隙,它们就会从黑暗中跳出来,新鲜而闪亮。你抓住它们,把它们擦亮,然后塞进你的作品。
大家都告诉我,我们这一代人都在做白内障手术。和助听器一样,它的价格贵得让人唏嘘不已。但我已经有一段时间看什么都觉得暗淡无光,毫无特色,所以我就去做了。当我跟一个医生朋友提起这笔费用时,她说:“呵呵,你的钱都够给一整个马场的人做白内障手术了。”但相信我,我很感激不用看到浮游物像虫翼一样飘过我的视野。再次享受色彩、质感和距离的盛宴让人兴奋不已,即使我的眼睛恢复得比广告上说的要慢得多,其中一只眼睛还半闭了好几个月,以至于在我下一本书的宣传照中,我看起来又笨又阴险,就像一个年迈的海盗。
然后是大火之夏。然后是新冠病毒。一切都放缓,停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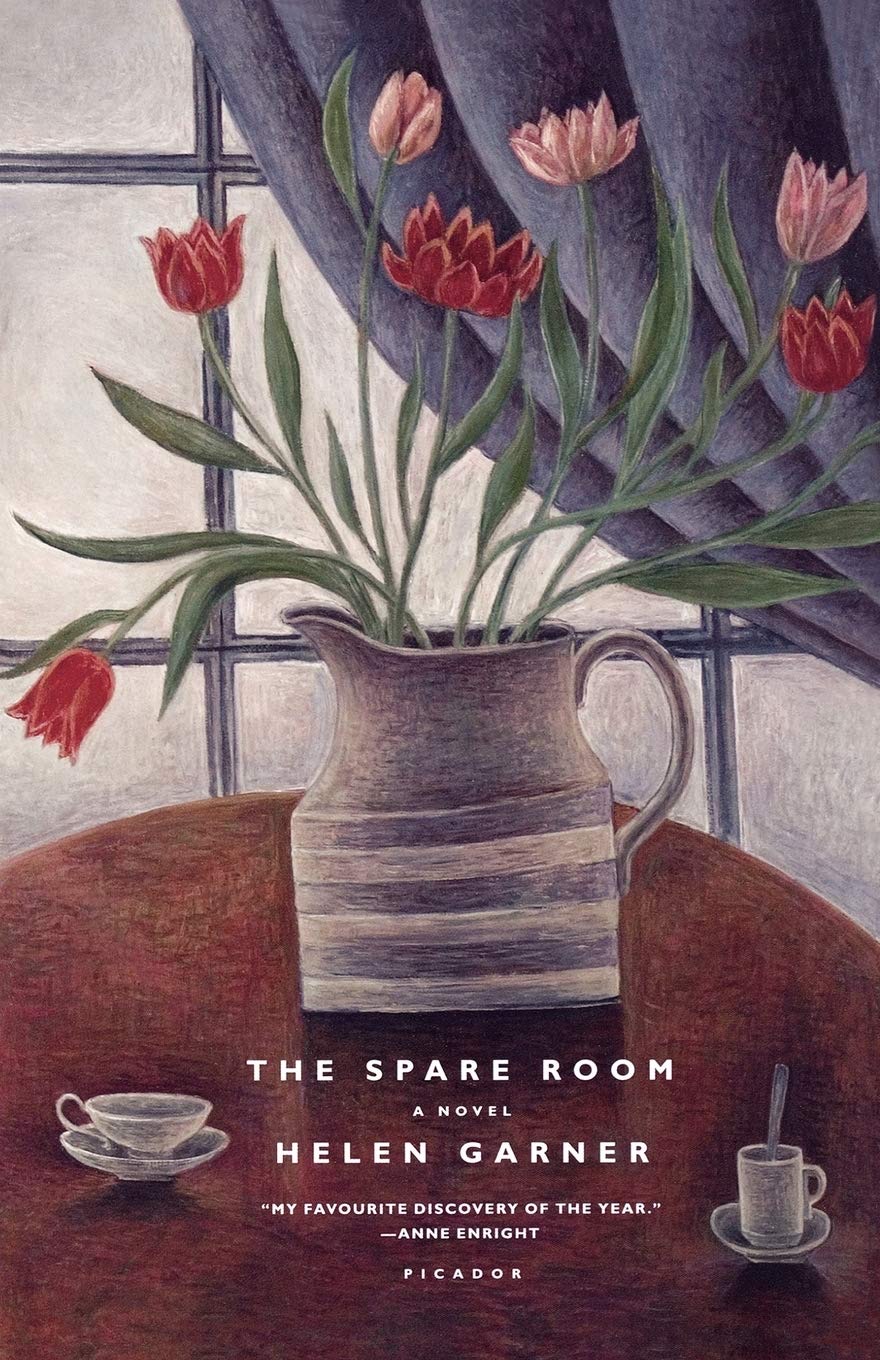
我是幸运的。我有工作要做:将我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第二卷日记剪裁归档出版。隔离期间,我不能跨城到平时藏身的出租办公室去。于是我走进家中的房间,并关上了门。
就像我安静的屋外世界一样,时间把自己里外颠倒。40年的日常工作习惯灰飞烟灭,新的习惯从灰烬中萌生。我没有早睡,也没有吃完早饭就直接开始工作,而是在沙发上一直沉浸到凌晨一点,津津有味地欣赏着野性十足的犹太人单口喜剧和女侦探的旧案调查。我八点醒来,让家丁出去,快走40分钟,在垫子上做普拉提,然后整理邮件。到了中午,我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在一摞旧笔记本的包围下,我会一直工作7个小时。我从不疲倦,从不需要小睡,饿了才吃,喝了一杯又一杯的水。我犯关节炎的部位——手腕、腰部、左脚——一点都不疼。我一直在想,是因为我很快乐吗?窗外的世界正在一发不可收拾地走向地狱,我这个年龄的女人还有资格快乐吗?
我开始疑惑,为什么和“关注(attention)”搭配的动词是“付出(pay)”?关注是一种债务?一种责任?一种税收?还是一种精力的付出?这句短语中似乎涉及到了工作,或者说是牺牲。如果我们付出了,又能换回什么呢?
当我翻阅笔记本时,我简直不敢相信,30年前我注意到的一些事情有多么渺小。我的天,我简直是注意力的女王!我花1.19澳元买了两块排骨。我熨烫桌布。一个从未听过多利·帕顿的歌的成年男子。一个修女说她的脸色“和这些胡萝卜一样红”。我朋友的金鞋。一些闻起来像蘑菇的花园泥土。一个煮熟的鸡蛋。一把3B铅笔。一根夹在医生头发上的圣诞装饰品碎片。当我再次遇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它们显得太珍贵了,像是具有意义的小炸弹。虽然当我把它们写下来的时候,我认为它们不过是一段段叙事之间的碎片和片段,是我每天用来练习的原材料。
我唯一能提供给这个世界的就是我的注意力。有时在凌晨两点,我觉得这不算多,远远不够,几乎不算什么。但现在,重读我关注和随机保存的记录,我开始发现,我做的比我知道的要多。我想我甚至可以大胆地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翻译:李思璟)
来源:卫报
原标题:Is a woman my age allowed to be happy when the world is going to hell in a handbasket?
最新更新时间:08/29 10:08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