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戴维斯(William Davies)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负责人之一。他的新书《这不正常:自由主义英国的崩溃》(This Is Not Normal: The Collapse of Liberal Britain)聚焦当前这一历史性时刻,对2016年至今英国公共生活中的若干基本规范提出了一系列批评。
用你的话说,在2016年英国公投至2020年脱欧这段时间里,“自由民主制最可靠的基石趋于崩解。”这些基石是什么?其衰落过程如何?
广义上的自由主义——尤其是自由民主制——坚持认为,某些东西是处于政治之外的,即无论发生什么意识形态或道德分歧,某些特定的制度应岿然不动。这包括宪法性规范、法制和对规范的某种默然尊重,也包括承认可信的事实和数据。
至少对英国而言,2016年的冲击在于,我们发现若有可观的政治利益可图,公共生活中某些看似不涉及政治的、永恒的方面就可能会被政治化或弃若敝屣。退欧公投过程中的诸多案例已为人们所熟知:脱欧后每周省3.5亿英镑之论、不明不白的政府开支以及对Facebook的利用。2019年又有一波打破成规的浪潮,其高峰是议会休会之争的官司一路打到了最高法院。
这引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也许可以说可能性总归存在,但以往对自由主义规范的尊崇要稳固得多。然而,媒体格局的变迁——尤其要考虑2006年至2016年间社交媒体的异军突起——意味着反自由主义的力量在组织、协作和策略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
第二,其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它在民主竞争中胜出的理由在于,绝大多数人(在美国也一样)相信自由主义的现状不过是幌子,背后则是只顾私利的派系,政客们都是一丘之貉。如此一来,整个体制便需要一场爆破。而人们之所以相信这些,恰在于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现状的确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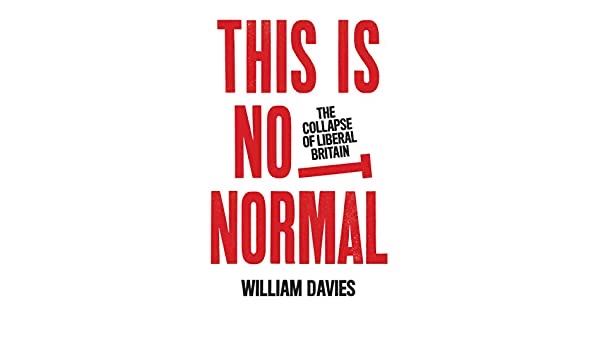
你专门指出,“不正常的政治”始于2019年,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有无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回归“常态”?
我在书中考察了2016年以来的一系列变化,当中也谈到了特蕾莎·梅领导权的最终崩溃。起初人们认为梅是同情退欧的,身为一名作风硬派的内政大臣,她坚信应保卫“人民”,拒斥威胁及外来者。书中有一篇短论讨论了她意识形态里的这个方面,我追溯到了她在内政部的经历。
然而,她对2016年以来兴起的反建制、反自由主义政治的风潮也多有保留。她提出过一些不错的批评,如“无根公民(citizens of nowhere)”,同时也在谋求一种将经济繁荣放在主权之上的脱欧计划,至少在退欧支持者的想象里是如此,她算不上头脑发昏,除开那场毫无必要且注定失利的选举。
2019年的情况是,在退欧党的崛起以及约翰逊上台的背景下,托利党(即保守党)面临要么溃败、要么接受法拉奇主义(Farageism,即退欧党魁首奈杰尔·法拉奇的一系列思想及主张——译注)的两难局面。保守党显然选择了后者。但这样一来,保守党也就无异于宣称自己已经打破习惯、不按规则出牌了,如今它更演变成了一个只聚焦文化战争这个单一议题的党。
约翰逊为表明这一点可谓绞尽脑汁,同时也斩获了不少利益。这种做法对于打选战效果非凡,但对于治国理政而言则纯属胡来。问题是,即便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重返“常态”,选战和更为广义的政治冲突里的那一套玩法也已经在迈向乱局的过程中扎下了根,准确一点说就是靠宣传攻势取胜。约翰逊或保守党在可见的未来不太可能放弃这一路线,譬如他们现在就试图废除选举管理委员会(Electoral Commission)。
依照你的解释,如今的自由主义已沦为一种“伦理劝诫或文化认同”,失去了对普世正当性的主张。此说只针对英国吗?还是说这一现象已经波及到了整个西方乃至于全世界?
我认为问题是全球性的,多边机制的衰落即是明证,而特朗普的上台更加速了这一进程。欧盟也面临同样的危机,虽然当前的疫情已经令情况大有不同。坚守这些机制、高举欧盟旗帜的人依旧存在,但鉴于同样的理由,这些人也不再如自由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保有独立的、超越文化边界的裁判者权威。
事态的发展表明(其方式是我在撰写书中文章时始料未及的),自由主义的未来目前只仰赖一个问题:是否有能力在健康危机面前平等地衡量生命的价值。考虑到气候变迁,解决这一问题对自由主义而言始终是当务之急,但新冠疫情让我们对它的紧迫性及鲜活性有了新的认识。

你可能会认为(我在书的后记里也有讨论),英国自由主义在2020年春天的几个月里得到了一丝喘息之机,其间不少公众共识的基石——专业能力、统计、公共管理和BBC——在政治上重新取得了公信力和尊重。2016年以来的诸多乱象一时有所收敛。但每当约翰逊或其亲信遇上麻烦,他们仍会故技重施,玩一些扭曲信息、制造乱局的把戏,或可称之为“新非常态(new abnormal)”。
你自称新书为“实时社会学(real-time sociology)”,旨在研究高速运转的新闻周期(news cycle,即新闻节目或出版物的更新周期,如日报为每24小时一期——译注)之下的结构与条件。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何在?
自由主义者在理解我所讨论的时段(即2016年至今)时所面临的困难之一,是他们有关世界的政治预设和观念都不起作用了。以往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人们会投票支持高经济增长率、共识和社会和平。但假如他们不这么做了怎么办?如果他们想要推倒重来,乃至于还有充分的理据,那该怎么办?这与2008年经济危机时的情形有诸多相似之处,当时自由主义经济学赖以解释现实的基本原理也失效了。
社会学所提供的乃是某种对更广泛、更长期趋势的意识,藉此我们可以对危机的意义有一定的把握,我希望自己的作品也能做到这一点。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它认为变迁和冲突乃是资本主义的常态特征。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的研究路径和思维方式都有马克思主义的影子。至少在我看来,此类工作的重要性在于指明乱局并非像表面上那般混乱和不可理喻,非理性背后有其自身的深层次理据和逻辑。
批判理论(甚至精神分析)也与此类似,它与启蒙运动的原初冲动有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关联,那就是把世界看成是可理解的(comprehensible),同时又不拘泥于教条。对我而言,这就是社会学所能做的,它面对动荡局势的贡献也在于此。从某些方面看,这意味着接下自由主义者以及自由主义诸制度不再有能力去完成的使命:在显见的、被视作理所当然的规则失效的情况下,重新确立“游戏玩法”或因果链条。
这本书以建立“法律与经济重建者联盟”的呼吁结束。谁属于这一联盟?我们如何实现它?
许多思想家——尤其是包括自由左派在内的左翼(碰巧还有某些早期的新自由主义者)——都试图勾勒出经济与政治世界的构造方式。换言之,经济与政治世界乃是一系列成文或不成文的有关参与和行动的规则的产物。以前我对合作运动(co-operative movement)和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的“真实乌托邦(real utopias)”特别感兴趣——其主张是,各种制度不单有资本主义性质,它们也有一定的独立性并存在于原教旨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带。
另一些激进派如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则致力于指出,经济生活中有许多方面看似不言自明、天经地义,实则并不自然乃至于是不可接受的。另一目前值得关注的思潮来自方兴未艾的“法律与政治经济学”领域,如凯瑟琳·皮斯托(Katherina Pistor)等人的论著。
多年来,我一直在想,假如持激进立场的律师能够通力合作、共同设计出一幅新的经济蓝图,情况将会怎样?早先的新自由主义者就这么做过,但我也留意到合作社对此也有需要,构思及组建一家实行民主化管理的企业是万分困难的。鼓吹或倡导某个东西和从技术上去构建及维系它完全是两回事,这也是长期以来困扰着新型所有制与控制模式的问题。
话说回来,目前很明确的一点是,“旧常态”已经不可接受,理由很明显也很充分。但没有人能过一种毫无常态可言的生活,某些右翼自由至上主义者、异想天开的领导学大师和那些把“企业家才能(entrepreneurship)”当成万灵药的人就喜欢做诸如此类的白日梦。
我们应当追求一种更好的常态。为此,我们既要与技术专家结成联盟——这些人熟谙宪法设计、模板以及可行的组织形态——也要有政治上的紧迫感,以构建更可靠的集体安全和风险分担机制。某种意义上讲,这意味着一种不同的企业家才能观,它固然意味着创造全新的经济形态,但也对创新有更为广阔的想象。不妨用“社会企业家”和“社会企业”来指代之。这与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不相干,关键在于,面对迫在眉睫的存在性危机,我们要如何去推动日常生活的规范与实践的转型?
(翻译:林达)
来源:新人文主义者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