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于1925年2月在《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前不久对一位朋友说,“或许我的书很烂,但我不这么认为。” 如果说他的前半句话是随便说说的话,那么这后半句话则绝对是太保守了。那时,菲茨杰拉德已经知道他取得了何等的成就。在那六个月前,他对斯克里布纳出版(Scribner’s)的编辑麦克斯韦·珀金斯(Maxwell Perkins)说,他正在撰写的作品将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国小说”。珀金斯的反应丝毫没有动摇他的自信。他称这本书为“奇迹”,并补充道:“就纯粹的写作而言,这是惊人的。”
在最终定稿为这本长达九章、共计4.8万字的小说前,菲茨杰拉德的手稿经历了多次修改。这部作品直到现在仍然年年热销。书中的故事起初设定在1885年,以天主教为主题。在修改的过程中,关于盖茨比那卑微的中西部出身的材料被改编并用于服务“赦罪”的主题。即便在菲茨杰拉德最终定稿之后,他还推敲了多个标题,包括“Trimalchio in West Egg”,“On the Road to West Egg”,“The High-Bouncing Lover”,“Gold-Hatted Gatsby”和“Under the Red, White, and Blue”。(译注:Trimalchio是罗马小说《Satyricon》中的人物,他一个傲慢自大的前奴隶,通过大多数人都唾弃的方式获取了大量财富;West Egg,即西卵,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长岛上的虚构之所;High-Bouncing Lover,Gold-Hatted均出自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半自传小说的主人公Thomas Parke D'Invilliers的诗《Then Wear the Gold Hat》;红白蓝是美国国旗的颜色。)
菲茨杰拉德意识到了自己的善变、不谙世事和智慧上的局限,并因此意识到自己永远不会写出“客观的巨著”。他拥抱了小说中对“形式”和“艺术”的突出体现。源于福楼拜和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集中体现在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和威拉·凯瑟(Willa Cather)的方法论强化了他创作的渴望。正如他麦克斯韦·珀金斯所说,他要写出“非凡、美丽、简单且构造复杂”的东西。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源于由此产生的清晰概念。菲茨杰拉德找到了几乎所有小说家梦寐以求的东西:一种结构——富有戏剧性和寓言色彩,能够描写社会和心理学,集体力量和个人命运,且对上述题材没有任何限制,同时构成了那个时代的肖像,且又是一个具有典型主题的悲剧。但是麦克斯韦·珀金斯说得似乎没错,这部小说是语言上的集大成者,是一种呼唤,但带有地域色彩。麦克斯韦·珀金斯指出,书中华丽的词藻“让场景熠熠生辉”。就算《了不起的盖茨比》不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美国小说,它至少也是文笔最出色的美国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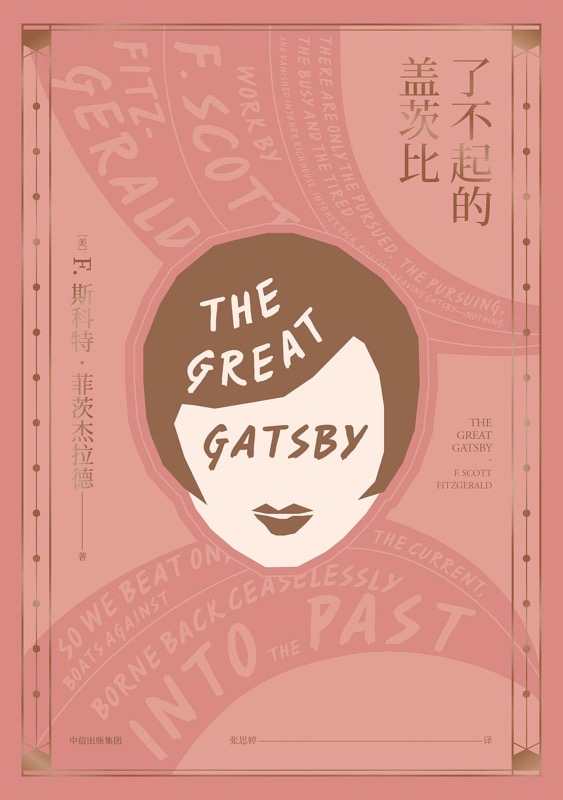
[美]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著 张思婷 译
中信出版社 2017-2
菲茨杰拉德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导师克里斯蒂安·高斯(Christian Gauss)指出,他经常描绘“窗户被灯光点亮”的场景。对这本狂想曲般的、视效丰富的书来说,这样的评论实在扫兴。从这本书的最开头,菲茨杰拉德就用这样的场面狂轰滥炸:“树木抽出繁盛的枝叶与光芒,”白色的宫殿在长岛海峡沿岸闪闪发光,草坪围绕日晷生长开去,燎遍花园,随后,他又把我们带到房子被“明亮的藤蔓”覆盖的一侧,然后,的确,这里出现了一排“折射出金色光芒”的法式窗户。

当然,所有这些自然的和人造的辉煌,以及反复出现的对于生命和光芒的描写,都是在为有史以来最令人沮丧的故事之一铺陈背景。1922年,29岁的耶鲁大学毕业生尼克·卡拉威在纽约担任债券推销员,他开车前往时髦的东卵与他的表亲黛西·费伊以及她粗鲁的丈夫——来自芝加哥的汤姆·布坎南共进晚餐。在那里,他遇到了黛西的朋友,高尔夫球手乔丹·贝克。乔丹询问尼克,是否认识他在西卵的邻居盖茨比,这个名字似乎使黛西感到震惊。用餐时,乔丹悄悄告诉尼克,“汤姆在纽约有情妇。”不久之后的一个下午,汤姆向尼克介绍了这名女子,默特尔·威尔逊,她丈夫乔治拥有一家汽车维修店。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尼克与盖茨比结为朋友。尼克通过乔丹得知,盖茨比早在五年前就爱上了黛西。盖茨比在战争期间获得了英勇勋章,随后赚了数百万美元,关于他是如何挣到这笔钱的谣言传得满城风雨。后来,他购买了在西卵的豪华别墅(拥有爬满常春藤的塔楼,大理石游泳池,以及40多英亩的草坪),以期黛西会参加他日常举办的豪华派对。尼克和盖茨比成了好朋友,尽管盖茨比告诉他的几乎所有事情都被证明是胡说八道。在以尼克为中间人的情况下,黛西和盖茨比重燃恋情。一个闷热的夏末之日里,一行人在汤姆家、默特尔家的车库以及纽约广场酒店几次会面后,戴西开车撞死了默特尔;汤姆告诉默特尔的丈夫,这辆车属于盖茨比。随后,乔治开枪打死盖茨比,并开枪自尽。此后不久,尼克回到了中西部,他的幻想破灭了。
菲茨杰拉德收到麦克斯韦·珀金斯的来信时,感觉自己“挣了一百万”。不久之后,这本“不算太坏”的书受到了他在普林斯顿的朋友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以及T·S·艾略特的赞赏。艾略特说他把《了不起的盖茨比》读了三遍,并认为这是自亨利·詹姆斯以来美国小说迈出的第一步。到第二年年底,乔治·库克(George Cukor)导演了基于该书的舞台剧,基于该书的电影也于随后问世。

《了不起的盖茨比》似乎不可避免地登上了今日的神坛。然而,菲茨杰拉德如今的盛誉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其死后确立起来的。这本被约翰·厄普代克认为其创作过程“非常幸运”的书,也曾经历了一段黯然失色的时光。1932年时,菲茨杰拉德向麦克斯韦·珀金斯抱怨说:“新的一代人都不读它。”现代图书馆在反复游说之下同意再版,却也停止印刷。菲茨杰拉德于1940年去世,享年44岁,他最后的一笔版权费支票面值仅为13.13美元。
这些只是格雷尔·马库斯(Greil Marcus)在他的短篇研究《在国旗下》(Under the Red White and Blue)中告诉我们的部分事实。他认为该小说是一面“文化之镜”,且它“以其自身的方式存在着”。这是正确的,但我们尚不清楚为什么优先考虑一个事项的代价必须是牺牲另一个优先事项。格雷尔·马库斯是评论家和历史学家,他以在书中建立复杂的谱系关系而闻名,这尤其体现在他的著作《隐形的共和国》(Invisible Republic)之中。该书提到了鲍勃·迪与 The Band 合作的专辑《The Basement Tapes》。格雷尔·马库斯的另一部作品《口红印》(Lipstick Traces)也是如此,这本书关注的主题先锋派和朋克。他并不那么愿意直视文化制品本身。
有时,格雷尔·的作品更像是一座特洛伊木马,其内涵隐约像是对巴兹·卢尔曼(Baz Luhrmann)2013年翻拍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电影的致敬。他说,巴兹·卢尔曼似乎并不对被菲茨杰拉德的原著感到“恐惧”,他让这整个故事“完整了起来”,“当电影最终结束时,那种完整性揭示出,原来这部电影正是原著一直在寻找的东西。”——这也许是书中最古怪的片段了。
格雷尔·马库斯认为,《白鲸》那历经沉浮的声誉才是一切的“起点”——在表达这一观点时,他并不带有丝毫的讽刺或嘲弄。不久之后,一个特别的框架体系浮出水面。在讲到乐队合唱团时,他引用了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他对菲茨杰拉德的看法并不广泛地为人所知晓),因为以实玛利(Ishmael)关于葬礼队列的描述使格雷尔·马库斯想起了乐队合唱团的歌曲《The Weight》的开头,而埃德蒙·威尔逊并非菲茨杰拉德的顾问和执行者。由于埃德蒙·威尔逊发表了关于美国内战的文学研究《爱国的戈尔》(Patriotic Gore),《电视指南》杂志(TV Guide)于次年收录了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基于《白鲸》翻拍的电影。[译注:《白鲸》讲述了裴廓德号捕鲸船船长亚哈带领全体船员,追捕一条叫做莫比·迪克的大白鲸的历险过程。裴廓德号出航时聘雇了来自纽约的以实玛利(Ishmael)。整个故事几乎是以实玛利为第一人称来描述,本书第一章第一句是:“叫我以实玛利(Call me Ishmael)。”这是文学史上最为著名的开场白之一。]
格雷尔·马库斯关于《白鲸》的评论有些极端。那句“Call me Ishmael”真的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吗?至少他在文字上下了功夫。《在国旗下》一书中,题为“阅读其书”(Reading the Book)的一章提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著名读者:上《周六夜现场》节目的安迪·考夫曼(Andy Kaufman),还有把该书改编成了一场长达六小时的演出的戏剧公司Elevator Repair Service。马库斯在脚注中说,乔治·威尔逊是所有角色中“最不冷静的”,这暗示了这本书受欢迎的关键所在。除此之外,他几乎没有提到他和其他人为什么会喜欢这本书。在抨击阿诺德·本内特(Arnold Bennett)的一本传记时,我经常想起弗兰克·科莫德(Frank Kermode)的主张——阿诺德·本内特的《Riceyman Steps》是“ 一本通俗的书,但并不是一本值得推荐的书”。

也许格雷尔·马库斯认为,传统的方法无法容下这本书的魔力,也无法说明其在文化中的地位。但他偏爱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的发挥,而非一个直接的演绎,这背后还有其他的相关因素,这个因素或许有些恼人——这本小说本身并不是在描摹纤毫毕现的近景。菲茨杰拉德并没有实事求是,例如,汤姆的女儿不能是3岁;并非他的所有散文和英雄史诗都对小说有利。他在一封信中承认,他缺乏“坚定的艺术才华”,因而他无法删去“放在上下文中并不通畅的精美片段”。就连小说中传为佳话的尾句——(“我们便这样扬著船帆迂回前进,逆水行舟,而浪潮奔流不歇,又不停地将我们推向过去。”)也带有修辞性,它是神来之笔。
***
《了不起的盖茨比》旨在实现一种特殊的个人突破。与菲茨杰拉德的早期小说《人间天堂》(1920年)和《美丽与毁灭》(1922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给评论家提供的远不止是对他浪漫气质的折射。菲茨杰拉德没有描述事物在他眼里的样子,他转而仔细研究了这种思维方式的陷阱。麦克斯韦·珀金斯说,他们请来了“一个讲故事的人,这个人比起演员,更像是一个旁观者”,他创造出了“可以透视的距离”。但是,整本小说是如何透视尼克的?
存在若干个菲茨杰拉德可能参考的模板。在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和《吉姆爷》中,旁观者马洛是那个叙事者。尽管他的证词没有受到明显怀疑,但他的话远非确凿。当叙述本身没有得到支持,而叙述者本人是作为可靠的证人、一个稳定、清醒的核心出现时(“我一生只喝醉过两次”),关于可靠性的问题就不那么容易出现了。
我们对尼克世界观的感觉主要来自于小说的前500个字——既是叙述性的序言,也是信条。他称自己是一个对比自己更困苦的人怀有深刻但有限的同情的人。因此,我们不禁要问,菲茨杰拉德是否故意造成这种反差——尼克在开场白中声称他“倾向于保留所有判断”;他又坦白称,他开车驶离汤姆的家时感到“有点恶心”。
类似的歧义也笼罩在尼克的解释中——他从东卵回来时,他感到自己不想再“经历深入纷乱人心的洞察”(no more riotous excursions with privileged glimpses into the human heart),只有盖茨比是他的例外。但是,还有谁允许尼克窥探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呢?尼克在小说中复述了盖茨比口中自己的过去。尼克说:“他的内心处于长期的骚动中。”用尼克的话说,正是让尼克“获得了关于这本书的标题的灵感的那个人”造成了尼克的上述感受。
除非尼克是容易犯错或虚伪的人,否则很难解释他为何会觉得,盖茨比是一个可怜的人物,而汤姆却是邪恶的。他说,盖茨比“最后没事”,而汤姆构成了“肮脏的尘土”的一部分,而“肮脏的尘土”是“随(盖茨比的)梦而来的”。然而,他们的相似之处令人震惊。这两个人都是薄情的花花公子,他们都被并非自己赚得的财富所定义。汤姆有坚硬的外表和柔软的心(在默特尔死后,他哭得像个婴儿),盖茨比却有柔软的外表和坚硬的心。汤姆的傲慢是姿态的问题,但盖茨比拥有更深层次的权利,他感到自己生于错误的家庭,注定要有更大的事业。尼克感觉到汤姆“想让我喜欢他”,盖茨比说:“不论如何,您对我有什么看法?” 如果汤姆在耶鲁大学的足球生涯之后的一切都是“反高潮”,那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与戴西的短暂缠绵后的盖茨比。
汤姆和黛西的主要形象都是“淡漠的人”,但盖茨比似乎一点不比他们来得更富同情心。他的世界是由腐败和狡猾来定义的,尽管他与黛西的关系让他们自己都觉得造作(“在她的心中,她从未爱过除我以外的任何人!”)。他们俩的关系和默特尔与汤姆的外遇一样,荒谬且充满不切实际的想法。尽管盖茨比显然夸大了他与牛津大学的联系,但当盖茨比透露自己曾当过五个月的军官时,尼克还是表现出了赞赏。因此,汤姆放弃了驳斥他。汤姆本来要说的是,盖茨比唯一熟悉的那个牛津,是新墨西哥的牛津。然而,对汤姆向默特尔撒谎,并告诉她黛西是一个不相信离婚的天主教徒一事,尼克感到“震惊”。尼克对自恋的厌恶似乎并没有延伸到自恋的关键属性:虚假。他讨厌的那个人比他所迷恋的那个人真实得多。

但是尼克也是个明眼人。他意识到,对盖茨比而言重要的不是黛西,而是关于她的想法,正如海湾对岸汤姆的码头上发出的绿光所显示的那样。尼克说,当绿光代表的不再是令人无法企及的东西,令盖茨比“着魔的东西少了一个”。在小说的结尾出现了另一个绿色的标志:“当年为荷兰水手的眼睛放出异彩的这个古岛。” 尼克说,发现美洲大陆是历史上人类最后一次面对“与其神奇的能力相称”的事情。意思是,绿光不同于“新世界的一片清新碧绿的地方”,它是其激发的奇迹站不住脚的托辞。
尼克是矛盾的,善变的还是矛盾的?这是小说设计的一部分吗?他带着敬意坚称自己“相信那绿色的灯光”,从而结束了对盖茨比的分析。但是到那时,我们都知道,这只是一个灯泡。
菲茨杰拉德本人认为他未能使这本书完美。他特别感到遗憾的是,他没有提供黛西和盖茨比之间的“感情关系的描述(也没有任何相关的感觉或信息)”。他认为这是个问题,他认为或许存在值得描述的关系,这一事实表明了真正的问题。一个根深蒂固的浪漫主义者往往拥有创造浪漫角色的不寻常天赋,但他可能无法对他们的魅力免疫。马洛在《吉姆爷》中对和他一起进晚餐的人说:“他动摇了我。我承认。”他承认,“感兴趣”是个弱点,他对于纪念吉姆的渴望就是一个例子。尼克没有澄清自己的任何问题。
因此,菲茨杰拉德并没有完全摆脱他的困境。正如他所说,如果这部小说在早写“十年”,那么它也会有他早期著作中标志性的问题。在编辑的过程中,他告诉珀金斯,盖茨比“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最终,菲茨杰拉德完成了关于盖茨比的创作。
***
近年来,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已成为可靠的坐标点。美国政治评论员乔治·威尔(George Will)称特朗普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盖茨比”,他精明地指出菲茨杰拉德隐去了的、宏伟之下的空洞。但对于厌恶特朗普的菲茨杰拉德爱好者,更适合拿来与特朗普比较的是汤姆·布坎南,一个放纵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少爷,一个称赞关于“有色人种帝国的崛起”的书是“精品书”的人,一个拒绝承认自己继承了财富和地位的人——我们可以因此讨厌他。
盖茨比在精神和专业上虚构的自我发明有种吸引力。对盖茨比抱有幻想比对特朗普抱有幻想容易,因为特朗普没有属于他的尼克——一个愿意从自己的角度同情地、并用自己的话介绍他的人。
尽管如此,菲茨杰拉德的妥协——他对于自己的评论的抑制——不应因为盖茨比邪教的各种罪行而被责怪。这本小说包含了足够多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以至于“盖茨比式的人”永远不会成为一种赞美,而他举办的晚会也会被认为是纯粹的地狱。除去格雷尔·马库斯所说的,本书中没有人是哪怕有一点点冷静的。
盖茨比的追求对菲茨杰拉德和其读者来说都是神圣的。汤姆从某种意义上辜负了盖茨比这一想法——粗俗的1920年代杀死了美国梦之类的想法,对小说的效果至关重要。因此,虽然曾几何时人们没有意识到这本书的惊人之处这件事看起来很奇怪,但我们应该对自己的合理性和沾沾自喜的态度保持谨慎。如果它现在是权威的,甚至是无处不在的,那么这可能不仅仅是对我们的智慧和良好品位的证明。
本文作者Leo Robson是《新政治家》首席小说评论家。
(翻译:王宁远)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