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下午1时,瑞典文学院将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美国作家、诗人露易丝·格丽克( Louise Gluck)。瑞典文学院的授奖辞称她精准的诗意语言所营造的朴素之美,让个体的存在获得普遍性。格丽克诗集《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月光的合金》2016年由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诺奖文学奖评审团主席Anders Olsson在宣布奖项时表示,作家本人得知这个消息觉得十分惊讶。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
露易丝·格丽克,美国诗人、散文家,1943年生于纽约,在纽约长岛长大,目前在耶鲁大学驻校写作。她在美国已经赢得了许多重要奖项,包括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她以自传性诗歌出名,目前已经出版有12本诗集,家庭生活、亲密关系是她写作的主题和重点,同时也着重创伤、欲望以及自然书写,并以书写孤独、苦涩和寂寞的坦诚态度著称,读者遍及美国以及全球。至此,诺贝尔文学奖已经有16位女性文学奖得主。
露易丝·格丽克其人
01 四岁开始读诗,“我是个写得很慢的人”

在诗歌随笔集《证据与理论》中,露易丝·格丽克说,诗人这个词必须谨慎使用,它不是一个可以写在护照上的名词。她在回忆成长经历时写道,格言说,诗人的智力或职业的标志是对语言的激情,这种激情被认为是对语言最小沟通单元——对词语的发狂反应,诗人被认为是不能充分理解血红色这类词语的人,但她的经历并不是这样。从四岁起,她就开始读诗,偏爱简单的词汇,对诗中存在的上下文的多种可能性感到着迷。她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的诗歌,后来扩展至布莱克、叶芝、济慈和艾略特,那时的她已经感受到诗歌传统的神奇之处,她最早的写于五六岁时的诗是这样的:
如果猫咪喜欢煎牛骨/而小狗把牛奶吸干净/如果大象在镇上散步/都披着精致的丝绸/如果知更鸟滑行/它们滑下,哇哇大叫/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那么人们会在何处?
格丽克回忆道,在她出生的环境里,任何一个家庭成员都有权将其他人的句子补充完整,像这个家庭的大多数人一样,她有强烈的说话欲望,但这欲望经常受到挫折,她很早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意识,如果不能精确、清晰地说出观点,说话就没有意义。在女子普遍无法接受好的教育的时代,她的母亲进入了韦尔斯利学院,并在婚后成为了家务总管式的道德领袖;而她的父亲是来自匈牙利的移民后代,他想要成为一个作家,但是被认为缺乏某些品性,比如对被拒绝的恐惧的忍耐力。
在成长阶段,格丽克曾尝试了包括绘画在内的其他艺术媒介,认为自己也有些天赋,但与诗歌相比,视觉艺术对她来说不够亲切,因为写作更适合小心谨慎的性格,文本的编辑之处可以保留,而画家的涂改一旦完成就不可修复。此外,她作为一个读者,也体验到了诗歌说话的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对读者而言像是知心好友,一种更像是被窃听的沉思,而她更偏好预设着或者渴望着一个倾听者的诗歌。
或许正因其学习视觉艺术的经历,有评论家认为,她为当代世界带来了过去的那种诗歌与画面互相交织的理念,她的获奖作品《野鸢尾》就清楚地体现了她诗歌中的视觉色彩。这个作品分为三个部分,架构在一个花园之中,想象着三种声音——花朵、园丁诗人以及全知全能的上帝。

在耶鲁大学格丽克的诗歌研讨班上,所有人每星期都要提交一首诗,并且阅读评论其他人的诗作,格丽克也不例外。但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研讨课上,只会集中讨论三首诗歌。2014年,她在接受《华盛顿广场书评》采访时表示,一个人在五分钟的时间内可以说很多,但新的观点需要反复推敲,她认为自己写诗的过程也是如此,顿悟和灵感不断,而唯有去凝视、思考这些刹那之光,事情才会变得有趣。她的写作方式受其老师、诗人Stanley Kunitz影响。
“我可以从一首诗中窥见它的力量和新鲜感、一种令我珍视的东西,但在某些地方,它又变得枯萎、凝滞——他(Stanley Kunitz)总是能正确地指出这些地方并把稿件退还给我。他都说了些什么呢?不是‘回到图纸板上去’。它更多地与劳作相关——‘拿着铁铲回到田野里去’、‘回去修高速路’。我想,这是我所相信的那种献身,因为我是个写得很慢的人。”
作为一位诗歌领域的教育者,格丽克对教学非常有热情,和年轻的诗人在一起探讨诗歌为她的写作提供了能量,她调侃自己是德古拉,渴望年轻人的血液。这种教学热情和她年轻时的一段经历有关。她曾经在阅读Peter Streckfus的作品时感到歉疚,因为她觉得自己从中窃取了灵感,为此她专门打电话向Streckfus致歉。但Streckfus对这件事的想法和他截然相反,他说:“我觉得这很棒。这就是写作者应该做的——我们处于对话之中。”格丽克坦言,自己从年轻一代诗人那里获得了很多启发。
02 古典主义的姿态与对“自白派”的超越
柳向阳是露易丝·格丽克在国内的主要译者,他翻译的格丽克诗集《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月光的合金》出版于四年之前,此后也翻译过这位作家的诗论与散文。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柳向阳评价诺奖得主格丽克“作为当代诗人是剑走偏锋的”。他认为其诗歌生涯有两个明显要点:一是继承古希腊传统,一是超越“自白派”传统。
“她主要是回到古典,研究古希腊。当代诗人里有人会写一点点古希腊的东西,但是像她这样做是很少的,”柳向阳称。格丽克被称为具有“古典主义的姿态”,因为她经常对于希腊和罗马神话进行重新改写,例如冥后珀耳塞福涅、德墨忒尔的故事。在《野鸢尾》之后的首部作品《Meadowlands》里,格丽克也使用了《奥德赛》里俄狄浦斯和佩内洛浦的声音来书写当代婚姻幻灭的故事,从当代生活出发,她写出了《奥德赛》式的的困境:家庭生活中的妥协、亲密关系里的残酷之处以及日常生活的琐碎与沮丧。
在早期作品中,格丽克关注失败恋情的后果、灾难性的家庭冲突以及存在主义绝望感,包括《野鸢尾》在内的作品都带领读者通向她最为深沉亲密的情感,而她较晚完成的作品则持续探索着自我的痛苦。正因为她持续而有效地书写失望、拒绝、失败和孤独,评论者也经常将其诗歌的气质形容为灰暗凄凉。也有评论家认为她关注的焦点就在于背叛、道德、爱和与之相伴的失落感,她就是“那个堕落世界的中心”。
在超越“自白派”方面,柳向阳与我们分享了对她个人经历的一些了解。因为有厌食症和失眠,格丽克瘦得很厉害,需要心理治疗,她中学没有上完就辍学了。在柳向阳翻译的《证据与理论》一书第一篇中,格丽克为自己厌食症的悲剧下了一个定义:“厌食症的悲剧在于,目的并非自我摧残,但结果却经常如此,厌食症建立了一个室内的标志,打算用于展示对需要、饥饿的蔑视,显得完备自足。”

格丽克把疾病变成了写作的底料,有人于是称她为“后自白派”——“自白派”的诗人,比如西尔维娅·普拉斯、安·赛克斯顿,都自杀了,人生是死路一条。柳向阳说,“格丽克最早也是沿着‘自白派’的道路来走的,但后来她战胜了疾病,方法就是借古希腊神话来写自己,从而超越他们。具体的技巧比较多,最典型的就是心理学的方法,因为她自己接触了长期的专业心理治疗。”
除了译者的身份,柳向阳自己也写诗,“一看她的诗歌,我觉得很好,所以在2006年到2016年期间一有时间就在译路易斯·格丽克,当时我也在译杰克·吉尔伯特的诗。”在回忆翻译格丽克诗集的契机时,他说,“她在美国很有名,但国内没有人在译,吉尔伯特在美国也不出名,诗选也都不选他。露易丝·格丽克的《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是我和好朋友范静哗一起翻译的。”
格丽克获奖让这位译者感到意外和吃惊,“但我觉得诺奖总归是有眼力,我们也需要往伟大传统回归,回到纯文学,回到诗歌。我觉得(诺奖)老在外面(关注)那些太通俗的东西,应该回来了。诺贝尔奖应该是理想主义的,而纯文学最能代表我们内心。”他接着说,“我一直认为村上春树、阿多尼斯是不会获奖的。”
获奖诗人的两部中译本诗集包含在世纪文景推出的“沉默的经典”诗歌译丛中,该系列的策划人昆鸟表示,这两本书已经集齐了格丽克当时已有的全部诗集,可以说全面展现了诗人不同时期的风格变化。他认为,格丽克前期的创作既有自白派的影子,也有狄金森的感受方式,但或许不如狄金森利落通透,到了后期,她才开始展现出大师气象,诗风沉实开阔。“后来变得没那么炸了,很蕴藉,像玉石,有光泽、坚实、深厚。我更喜欢她《野鸢尾》之后的作品,看似平淡,但力道很足,越来越老道。厉害人。”昆鸟说。
众议2020诺奖
01 诺奖垂青诗歌:诗人是冷门选择还是安全选择?
作为一位小说家和格丽克的读者,赵松认为,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露易丝·格丽克,是给予那种低调绵延而又极具灵魂映射属性的诗歌和“为一种使命而生,去见证那些伟大的秘密”的诗人的“高光认证”。
而“高光”与否在同为诗人的王寅看来是存疑的。首先,他曾关注过露易丝·格丽克的作品,却并没留下太深的印象。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王寅表示,格丽克获奖并不令他感到意外。他说,作为一名已经在诗歌道路上发展几十年,积累了大量作品的诗人,格丽克获奖自然是当之无愧,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诗最突出的。事实上,仅在美国文学界,与格丽克同等资历的诗人也大有人在,譬如战后一代著名女诗人乔丽·格雷厄姆、2019年普利策诗歌奖得主弗罗斯特·甘德、曾连续三界获得“桂冠诗人”的罗伯特·品斯基等,这些都是王寅心目中值得推崇的优秀诗人。

假如不算201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迪伦,距离上一次诗人获得这一奖项已经过去了10年(2011年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获奖),这让王寅觉得今年诺奖颁给诗人是件好事,“因为这能让我们更多地去关注诗歌,或关注一些不太知名、不被大众熟知的诗人,从这一点看,诺奖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同时,王寅也注意到,国外诗人对诺奖的关注热度并不高,不像中国如此看重。近年来,为策划“诗歌来到美术馆”项目,王寅曾接触过来自不同国家背景的诗人,其中也有诺奖的热门人选,他们普遍对此泰然处之。“可能在他们眼里(诺奖)就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奖,它的历史很久,但它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实际上是一直受到质疑的,”王寅说,“如果哪一天中国的作家也心态这么好,可能会产出更好的创作。”
在他看来,诺奖没有那么神奇,得了诺奖不代表名垂青史,也不会因为诺奖就改变一个文学体裁的走向和命运,因此,人们没有必要为诺奖如何评选、是否公正等问题争论不休。假如诺奖是一个公正客观的文学奖,那么只需要看文学作品是不是足够好,与性别、种族、语言都没有关系;假如诺奖需要平衡种种因素,那它是否以欧美为中心也并不重要,因为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达到完美的平衡。
诗人、《诗歌与人》主编黄礼孩在2005年设立了“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他昨晚在社交媒体上称,自己曾有打算将2019年的该奖项颁给露易丝·格丽克,并通过译者柳向阳联系了她,但彼时诗人已有76岁高龄,来中国领奖有些困难,且该奖项此前不久曾颁发给另一位美国女诗人丽塔·达夫,所以“犹豫了一下,没有因为她来不了中国而坚定地颁奖给她”。如今她捧得诺奖,黄礼孩一方面为她感到高兴和祝贺,一方面也“为自己错过她而感到遗憾”。
02 文学世界中心之争:美国文学势头正盛?
露易丝·格丽克获诺奖,也是自2016年鲍勃·迪伦之后美国诗人再一次捧得诺奖桂冠。在鲍勃·迪伦之前一位获得诺奖的美国作家是托妮·莫里森(1993年),其间相隔足有23年。黄礼孩也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的这一观察,“当今美国的好诗人比较多,今年给露易丝·格丽克既意外又正常,评委也有自己的偏好,但继鲍勃·迪伦之后很快又有美国诗人获奖,从中我们看到瑞典人对美国文化的倾向,也看到在全球语境中,美国文化处于某种优势中。”
事实上,自2008年起,美国作家获得诺奖的希望开始走低,时任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的Horace Engdahl认为,美国的作家都“对他们自己大众文化的潮流太敏感。”他称,“美国太孤立隔绝了。他们翻译得不够,也不真正参与到文学的对话中来……当然了,所有的大型文化中都有好的著作,但你不得不承认,文学世界的中心仍然是欧洲,不是美国。”
讽刺的是,1930年,第一位获诺奖的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就曾提出让欧洲世界非常熟悉的本国文学批评,他认为,“美国还没能够产生出一种文明来满足人类的深层需求,小说家、画家、雕塑家都在非常孤独、充满困扰地工作”,美国文学是“一块未开垦的边缘地区”。
多年以后,美国“边缘地区”的文学形象情况依旧。从2014年起,另一重磅文学奖项布克奖的评选面向美国作家作品开放,这一新闻引发了评论家们对于“美国文学污染”的担忧。英国小说家菲利普·亨舍尔认为,美国小说总是向着全世界喊话,而非根植于地方性。他在一篇题为《这是布克奖的终结》的文章中写道:“这些美国作家无法只书写一个异域,而不将这个异域放到美国这样令人舒适安心的语境中来,所以一个本地人一直在本地生活而不是晚年移居辛辛那提(美国的一个城市)的小说不再有了。”
在此之后的2016年,布克奖由美国作家保罗·比蒂捧得——他也是史上第一位赢得该奖项的美国作家,2017年的布克奖又由美国作家乔治·桑德斯摘得,不少作家站出来批评布克奖“含美量”过高。2018年3月,包括阿特伍德、伊恩·麦克尤恩、扎迪·史密斯在内的多位作家向布克奖发出呼吁,让美国作家从奖项竞选中退出。在更早的时候,30家英国出版商联名签署公开信,呼吁布克奖撤回允许美国作家参评的决定,声称如果不这样做,文学在未来将面临同质化的风险,评选规则或许意在让布克奖更加国际化,却使得奖项的国际化程度降低,让其他作家成为了牺牲品。但媒体评论区也有读者表示,“美国作家统领了全球,是因为事实上美国作家的小说写得最好……你不能因为你要输了,你就更改规则,除非你是特朗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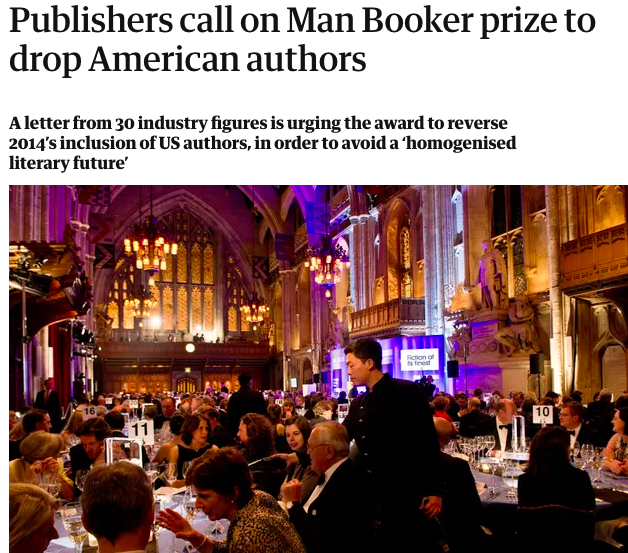
从今年的情况来看,欧洲作家和出版商的担心也许不无道理——2020年布克奖短名单的六位入围者中,有5位来自美国或持有美国身份。
在此前一个简短的线上采访中,评审团主席Anders Olsson在被问及新冠如何影响到诺奖评审工作时表示,一切照旧,唯一不同的就是开会和交流的方式改变了,就像世界上其他正在经历疫情的人们一样,但不变的是“对文学品质的关注”,他说,“每一年我们都会对到底何为文学品质进行激烈的探讨,但最终关心的还是文学的普遍性和全球性,也依靠那些可以从全球范围内提名的专家。” 全球化这个线索,也与露易丝·格丽克得奖的结果遥相呼应。
事实上,2019年诺奖文学奖评审团主席Anders Olsson在开奖前就揭示了评奖规则的变化,声称当年的奖项将会“开拓我们的视野”,扭转这个奖项长久以来的“欧洲中心主义”与“男性主导”的颁奖倾向。最终结果是,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获得2018年的奖项,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摘得2019年的奖项。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