妮可·克劳斯以其对人类复杂性的深入探究和精心考察而闻名,人称“作家中的作家”。她的作品(之前已发表四部小说)各有侧重,但关注度都很高。直白而不乏梦幻感,充满感性但有时又冷静超然,其语言一贯清丽明快,理路却复杂难解,富有挑战性且令人着迷。
她的首部小说集《成为一个男人》(To Be A Man)也对得起这样的好评。读她的书就好比与一个睿智的友人彻夜长谈。
克劳斯的背景本身就很奇妙。她一开始是诗人,曾与晚年的约瑟夫·布罗茨基有过密切的合作,在转向纯文学之前于伦敦著名的考陶尔德艺术学院获得艺术史硕士学位。 她有英美犹太人血统,在纽约长大,游历甚广,荣誉无数,其散文也因此而具备了一种权威般的强度(authoritative intensity)。简单来说就是她的作品很鲜活。小说集的一部分曾发表在《纽约客》以及其它一些地方。不过,既然是以作品集的形式重逢,我们也大可将这些故事视作一个系列来读。其焦点常常汇聚在这名天资异于常人的犹太裔女性所遭逢的诸多困境上。
《瑞士》(Switzerland)的第一句话即表现出典型的克劳斯式魅力:“我上次见到索拉娅已是三十年前。”此话于无声处宣告了我们将会像一架无人机一样,轻盈地穿过广阔的时空,迅即又降落到我们原本就希望了解的诸多人生里。
我们确实这么想,也已经这么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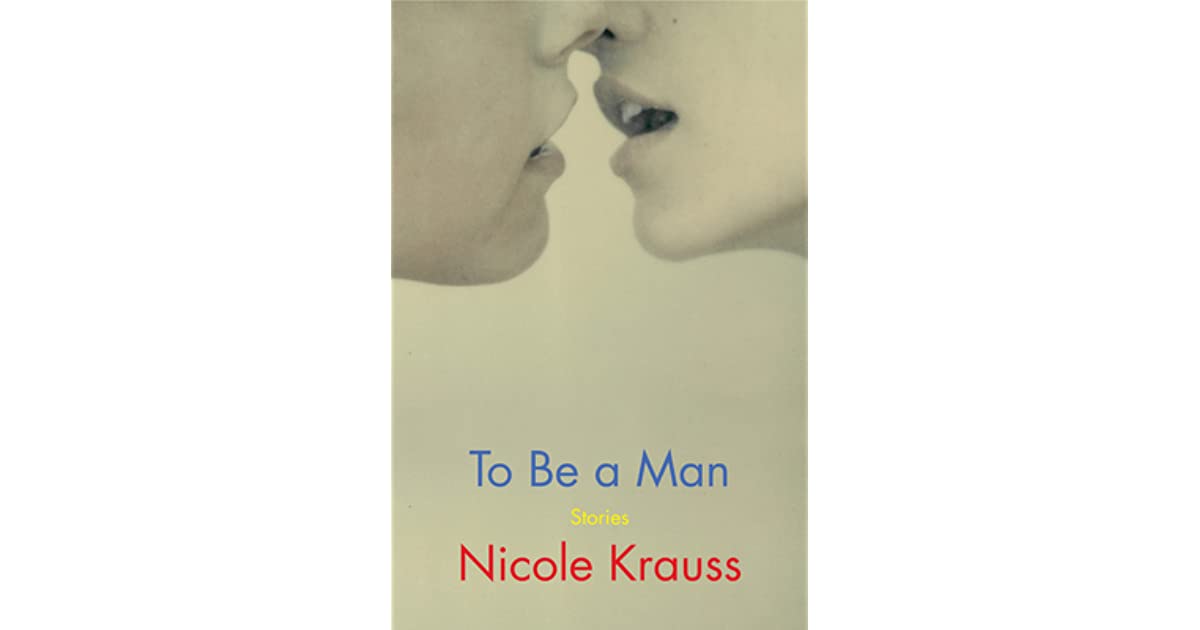
在《瑞士》里,一个中年女人回忆了自己如何目睹了漂亮室友的性生活,当时她们身在日内瓦的一所针对不服管教的女孩的寄宿制学校。克劳斯笔下的所有叙事者皆有一种冷酷、精准且几乎不带任何情感的腔调,这通常源自不堪回首的历史。“我们是欧洲犹太人……这意味着祸乱频仍的过往,且未来还将重演……我们连说一丁点德语都是不被允许的,那是我们外婆的母语,她全家都被纳粹杀害了。”
克劳斯不屈不挠地继续着对内心的探究,只言片语都会给人一种从心底用力拉出来的感觉。索拉娅因看不惯前男友的平庸而与之决裂时,目击此事的叙事者当即就意识到自己“内心突然解离(disassociation)了,伴随着因意识到曾经亲密无间的人其实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所带来的恐惧”。
以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漫不经心口吻,克劳斯凸显了社会光鲜表面之下的残酷现实,而这是年轻女性每天都要直面的。“瑞士的”叙事者回忆称,有一次她正透过窗户朝商店里面看去,一名衣着体面的男子从后面接近。“我只用一只手就能把你撕成两半,”他低声说完这句话后就消失了。克劳斯笔下的女性经常会遭逢这样的威胁。当索拉娅危险地卷入与一名有虐待狂倾向的老男人的关系后,叙事者感到“为她担忧。也许就是担心她本人”。“(索拉娅)在这场游戏里走得太远了,而据我所知这向来不仅仅是游戏,它还关乎权力与恐惧,关乎拒绝去面对一个人生来就与之朝夕相处的诸多脆弱性。”
犹太性自然免不了是考察对象——通常有亲身的见证。在《楼顶上的祖沙》(Zusya on the Roof)里,一名幸运地从绝症中痊愈的老教授坚信自己是被“召回”的,负有赋予其新生的孙辈以一种不受犹太性困扰的新生活之使命。“在大千世界的某一处,总会有出生及成长不受前人拘束的小孩……他能否享有选择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机会?”以及:“就因为我是个犹太人……其余一切的空间都被挤压殆尽。”
再来看一看另一对经历相似的夫妻所共享的文化传统:“二人皆来自数目多少相近的大屠杀幸存者群体,也都在以色列有一些亲戚……都在与异教通婚者或被判不合格者将被处以死刑的戒律下长大,而这就意味着两个人都是同一种骄傲、狭隘、狂热、焦虑、令人安慰而又吞噬一切的部落主义的产物。”
克劳斯的视野遍及全球,但又保持了相当的低调,她对各种现代制度的冷酷刻画也是一样。以《末日》(End Days)为例,在野火泛滥的加利福尼亚,年轻的花匠诺娅帮助她出生于以色列的父亲和维也纳出身的母亲达成了一场原教旨的犹太式离婚。仪式上,“母亲一直在找话说。她是会感到在斩首仪式上也有必要找话说的那种人。”
与小说集标题同名的《成为一个男人》由一名年轻的离异母亲担当叙事者,她回忆了某个以色列友人面临的军事上的煎熬(配有一张令人难忘的门阶上的小孩鞋子照片)。这位母亲陷入了沉思,为什么人们会告诉她这样的故事?她的答案神似一位艺术家的宣言。“大概她看上去比较像一个正在纠缠某种问题的人,其问题既广阔无边又转瞬即逝,永远无法直面,只能间或触及。”
《与埃沙迪相见》(Seeing Ershadi)则主打虚幻风,讲述了一名舞者和她的朋友同时迷上某位伊朗演员的故事,这似乎略微消解掉了克劳斯作品里常有的那种奇特的迫切感。“我觉得自己本来可以留住埃沙迪的……我要是问了他有关专一的事,那将会怎样?我想要的又到底是什么……当他的目光最终落到我身上的时候?”埃沙迪之于这位女性的意义于此徐徐展开,(与这部小说集里的其它故事一样)读者不由得心烦意乱,难以忘怀。
(翻译:林达)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