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有网友近日发现,韩国曾经以“大木匠”(Daemokjang)之名为传统木结构建筑艺术申遗,其中没有提及中国的榫卯,但使用的技术与榫卯极为相似。据此,一些网民怒骂“中国的传统文化再次被韩国剽窃”。
在《深圳商报》的相关报道中,北京建筑大学历史建筑保护系讲师齐莹并不认为“大木匠”抄袭了中国木构技艺。齐莹表示,唐朝时东亚文化交流让韩国、日本的官式木构建筑对中国技艺有所借鉴,但他们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也演变出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这是值得尊重的。这样的解释或许可以暂时平息争论,不过榫卯技术只是中韩之间矛盾的一个缩影。此前,两国网民之间有着关于端午节、中国结等一系列传统文化相关的“争夺战”。

谁的文明成就剽窃了谁,这类讨论其实深受“民族国家”框架的束缚。现在的中国和韩国看起来是严格区隔的两个民族国家,但就在一百多年前,在传统的东亚文明中,两者并没有泾渭分明的边界。19世纪之前,中国和民族国家标准有很大的出入,其自我认知更接近于世界中心、中央之国和“天下”。《分身:新日本论》作者李永晶看到,传统中华王朝是东亚世界秩序和安全的提供者,是一种普遍文明的中心。中央之国不需要名字,中国就是传统东亚世界体系,朝鲜也是这个世界体系和传统文明中的一员。近代以来,这一秩序经历了巨大的变迁,中国经过甲午中日战争,失去了它的最后一个朝贡国朝鲜,天下中心地位不再。抗日战争更是构成了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历史条件。
在中国的自我意识从世界政治层面跌落回地方层面,从一个“世界国家”(a world country)变成“世界一国”(one country in the world)。在同一时间,朝鲜民族也在历经外国统治、外来势力干涉的历史中生存了下来,在历史悲情的渲染下,民族主义不断建构和发展起来,成为了社会认同的粘合剂。二战后,韩国经美国扶植走上社会转型和高速发展道路,成为经济强国,加之受冷战意识形态影响,认为自己拥有社会制度上的优势,相对而言中国更为贫穷落后。在这种情况下,韩国需要塑造和自己身份、地位相匹配的历史。为了摆脱一直以来深受的来自中国的影响,提升文化独立性,彰显文化优越性,自然也会在历史问题上进行选择性的叙述。
由此可见,在传统中华帝国主导的东亚世界秩序中,中国以“提高野蛮国家的文明程度”为己任,朝鲜也没有排斥围绕礼制建立的“天下”秩序,扮演着朝贡国的角色,并不存在谁剽窃了谁的文明一说。但在民族主义思潮的波澜之中,我们对历史的运用就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样貌。不仅仅中国和韩国之间发生着关于传统文化归属权的争夺战,实际上,在世界各个地方,民族主义都深刻影响着人们对历史的叙述。在《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作者、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 (Margaret MacMillan)看来,“民族主义思潮几乎已经和法西斯主义一样具有强大的力量。”麦克米伦认为,民族主义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得非常晚,但是它却能带来强大的激情和仇恨,在其驱使之下,人们会为自己编织高贵而遥远的起源,并且选择性地讲述历史;历史也可以创造集体记忆,帮助民族共同体建立自己的国家。或许,读过此书之后,我们将对民族主义情绪有更多的反思。

《历史和民族主义》

文 | [加]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 译 | 孙唯瀚
人们有许多方式将自己的身份与他人区分开来,至少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民族国家一直是最吸引人的划定群体界限的方式之一。这种方式让人们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大家庭中的一员,或者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话来说,属于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民族主义思潮几乎已经和法西斯主义一样具有强大的力量。民族主义不仅造就了德国和意大利,摧毁了奥匈帝国,还在后来分裂了南斯拉夫。为了他们的“民族”,许许多多的人遭受痛苦和死亡,同时也伤害和杀害他人。
历史可以为民族主义提供更多的动力。它创造集体记忆,以此来帮助民族共同体建立自己的国家。无论是对民族伟大成就的集体纪念,还是对失败的共同缅怀,这些都孕育并支撑了民族国家的发展。一个民族可以被追溯的历史越久远,这个民族似乎就越稳固,越持久,它所主张建立的民族国家也就越有价值。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欧内斯特·勒南曾写过一部关于民族主义的早期经典著作,驳斥了其他所有的民族存在的理由,比如血统、地理、语言或宗教等。“一个民族,”他写道,“就是一群团结在一起的人,他们因为过去曾作出的牺牲,或将来要作出的奉献而聚集在一起。”但他的一位批评者却反驳说:“一个民族,是一群因对过去的错误看法,以及对邻国的仇恨而团结在一起的人。”在勒南看来,民族的存在是建立在其成员同意之上的,“民族的存在应该是每天都举行全民公决,需要持续得到其每一个成员的认可,这正如个体的存在是他不断延续自己的生命一样”。对许多民族主义者来说,似乎并不存在所谓自愿同意这种事。当你出生在一个民族之中,则无法自愿选择是否属于这个民族,即使有历史因素的介入,你也无法改变自己的族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法国宣称拥有莱茵兰(莱茵河左岸地带)时,他们强调的一个理由是,尽管那里的人说德语,但他们实际上是法国人。虽然他们之前很不幸地落入德国人的统治之下,但他们在本质上仍然是法国人,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对葡萄酒的热爱、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以及他们对生活乐趣的追求上体现出来。

勒南试图解释的实际上是一种新现象,因为民族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确实出现得非常晚。许多世纪以来,大多数欧洲人都不认为自己是英国人(也不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或威尔士人)、法国人或德国人,而习惯认为自己属于某个特定家庭、宗族、地区、宗教或行会。有时他们会以他们的领主来划分自己的身份界限,无论标准是当地的男爵还是君王。后来,当他们开始称自己为德国人或法国人的时候,他们不仅认为这个身份是一种政治差异,更看重其文化上对不同民族的区分。而且他们确实不会像现代民族运动通常主张的,认为国家有权在一块特定的领土上统治自己。
过去那些界定自己身份的办法一直延续到现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国际联盟的委员会试图确定欧洲中心各国的边界时,他们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人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捷克人还是斯洛伐克人,是立陶宛人还是波兰人。若是回答这些问题,人们往往说自己是天主教徒或东正教徒,是商人或农民,甚至只是这个或那个村子的人。意大利社会学家达尼洛·多尔奇在20世纪50年代曾惊讶地发现,西西里岛腹地竟然有一些人从未听说过意大利这个名字。虽然从理论上讲,他们好几代人都早已经是意大利人了。然而,随着民族主义日益成为欧洲人界定自己身份的方式,这些西西里岛的居民成了少数被民族主义浪潮遗忘的人。促进民族主义浪潮快速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包括通信速度的加快、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化的发展,其中最重要因素的就是,将自己视为某个民族的一分子是正确且恰当的,同时一个民族也应该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现代国家。这些因素推动民族主义浪潮在19世纪撼动欧洲大陆,到20世纪则开始席卷全球各地。
对那些所有永存不朽的民族来说,它们都不是由命运或神创造的,更不是由历史学家创造的,而是因为人类活动而产生的。这一切都始于19世纪。那时学者们开始研究各种语言,把它们分成不同的语族,并试图确定这些语言可以追溯到多久以前的历史。他们发现了一些可以解释语言变化的规律,至少可以令语言学家们自己满意的是,他们能够确定几百年前的文本是用德语或法语等语言的早期形式写成的。像格林兄弟这样的民族志学者,他们收集了许多德国民间故事,旨在证明德意志民族在中世纪时就存在了。历史学家孜孜不倦地复原这些古老的故事,并且把他们认为对本民族重要的历史拼凑起来,仿佛这个民族的历史自古以来就从未间断过。考古学家声称他们已经发现证据,可以证明这些民族曾经生活在哪里,以及他们在大迁移浪潮中迁徙到了哪里。
上述这些研究日积月累的结果,就是对民族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创造了一个不真实但有影响力的历史解释。不可否认的是,从哥特人到斯拉夫人,不同的民族都曾进入并遍布欧洲,他们与欧洲已有的民族发生了融合。这种观点把欧洲的历史比作抢椅子游戏。像是在中世纪的某个时间点,游戏的音乐戛然而止,正在嬉戏的各个民族要立刻坐到他们的椅子上,一个椅子给了法国人,一个给了德国人,还有一个留给了波兰人。于是,历史在此刻把他们定格为了“民族”。例如,德国历史学家可以描述一个古老的德意志民族,他们的祖先在罗马帝国之前就快乐地生活在他们的森林里,而在某个时刻,可能在公元1世纪,这个族群正式成为可以被识别的“德意志民族”。于是就有了一个危险的问题,究竟哪里才是真正属于德意志民族的土地呢?或者哪些土地又属于其他“民族”呢?究竟是德意志民族现在居住的地方,还是他们最初在历史上出现时居住的地方,还是两者都是?
如果学者们当初能够预料到他们所做的研究最终会导致什么结果,他们还会继续其对历史的推测吗?他们该如何看待,自己的研究最终导致了意大利和德国的血腥战争?他们该如何解释,民族主义的激情和仇恨分裂了古老而又多民族的奥匈帝国?他们该如何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老国家竞相利用历史理由对同一块领土提出主权要求?他们又该如何面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依靠宣扬民族和种族问题而建立的恐怖政权,以及他们总是对其他国家的土地拥有惊人的需求?
矛盾的是,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言,“民族主义是一个现代概念,但它却为自己发明出了许多子虚乌有的历史和传统”。那些曾经助长过,并仍在为民族主义提供支持的历史,基本上都是从已经存在的事实中衍生出来的,而不是凭空捏造新的事实。这些历史往往包含着许多真实的过去,但它们倾向于证实某个民族自古以来的存在,并对这个民族在未来将继续存在保持乐观的预期。历史也有助于创造胜利或失败的象征,例如滑铁卢战役、敦刻尔克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葛底斯堡战役,或者对加拿大人来说,维米岭战役。这些历史突出了过去领导人的功绩,例如查理·马特在图尔击败摩尔人;伊丽莎白一世在普利茅斯高地面对西班牙舰队;霍雷肖·纳尔逊在特拉法加击败法国舰队;乔治·华盛顿拒绝对樱桃树事件说谎。民族主义也经常利用宗教身份认同来为自己张目,想想那些模仿殉道者或十字架上的基督的战争纪念碑,或者像为了11月11日而精心策划的仪式。

如今人们以为的许多历史悠久的象征和仪式往往是近些年才被发明出来的,因为每一代人都会通过回顾历史,从中找到满足自己当前需要的东西。1953年,世界各地的电视观众都满怀敬畏地观看了一场古老的加冕典礼:女王乘坐镀金的四轮马车穿过伦敦,庄严的队伍进入威斯敏斯特教堂,还有那些音乐、华丽的装饰、坎特伯雷大主教身着的华丽长袍,以及精心策划的加冕仪式。当时我还在加拿大上小学,是在一本小册子上读到这一切的。但我们大多数人所不知道的是,我们满怀敬意观看到的这些仪式,绝大部分都是19世纪才产生的。而再早之前的加冕典礼实际上十分草率,有时甚至令人尴尬。1820年,当身材肥硕的乔治四世加冕时,与他关系不合的王后卡罗琳竟被禁止参加典礼。在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的加冕典礼上,不仅神职人员频频出错,坎特伯雷大主教为女王准备的戒指也出现问题,因为它对女王纤细的手指来说太大了。直到19世纪末,随着英国变得越来越强盛,作为国家象征的君主也变得更加重要,君主加冕仪式变得越来越隆重浩大,也经过了更加认真的演练,还加入很多新的仪式,例如,来自威尔士的激进派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发现,如果能在古老的卡那封城堡内为后来的爱德华八世举行册封威尔士王子的仪式,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在众多的民族象征之中,科索沃战役是最著名的之一。这场战役发生在1389年,塞尔维亚军队在科索沃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军队击败。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传说中,这既是一场世俗的失败,也是一场宗教上的失败,然而这场失败却蕴含着民族复兴的希望。对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来说,这场战役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悲剧。信奉基督教的塞尔维亚人的失利,是因为被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人背叛。战争开始的前一晚,塞尔维亚的领袖拉扎尔大公似乎受到上帝的感召,被上帝应许将会拥有天堂的王国,或者可以统治人间的王国。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选择了前者,但这个选择背后预示着,塞尔维亚民族总有一天会在人间迎来复兴。这到底算是宗教上的救赎还是世俗层面的救赎呢?后来拉扎尔被一位塞尔维亚同胞出卖战死沙场,但他的人民依然忠于他们的信仰,始终铭记这次失败以及上帝曾对他们的应许,并且在此后四百年间不断致力于复兴塞尔维亚民族。
这个故事的问题是,它不仅过于简单,而且部分内容并不能被当时简略的记录所支持。拉扎尔大公并不是所有塞尔维亚人的统治者,当初斯特芬·杜尚建立的塞尔维亚帝国走向没落的时候,拉扎尔大公只是争夺权力的几位大公之一。当时有一些大公已经同奥斯曼人讲和,并受封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的从属,他们因此派遣军队去攻打拉扎尔大公。目前的史料尚不明确,这场战役对塞尔维亚人来说是否真的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失败。但当时的一些记录显示,塞尔维亚人在这场战役中获得了胜利。当然战争的结果也可能是一场平局,因为此后双方都有一段时间没有再向对方挑起战争。而未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彻底征服的塞尔维亚帝国,也在科索沃战役后又继续存在了好几十年。
拉扎尔的遗孀和东正教僧侣开始把去世的拉扎尔大公塑造成为了塞尔维亚人而殉难的伟人。但奇怪的是,与此同时拉扎尔的儿子成了土耳其人的从属,并且为他们而战。几个世纪以来,拉扎尔和科索沃战役更多地象征着塞尔维亚人作为东正教徒的身份,同时表明塞尔维亚只是一个拥有共同语言的民族,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塞尔维亚民族国家。这个故事与许多其他塞尔维亚的文化一起在修道院中流传着,也在世代相传的伟大史诗中一直流传至今。直到19世纪,随着整个欧洲民族主义的觉醒,这个故事才开始受人瞩目,不断动员和鼓舞塞尔维亚人争取独立,反抗衰落且无能的奥斯曼帝国。

19世纪上半叶,塞尔维亚人用历史来激励自己,第一次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实现自治,然后取得完全独立。19世纪早期极具影响力的塞尔维亚学者吴克·卡拉季奇将现代塞尔维亚书写语言标准化,并且收集了许多塞尔维亚史诗。但他也留下了一个颇为有害的说法,他认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因为与塞尔维亚人说几乎相同的语言,所以他们应该也是塞尔维亚人。政治家伊利亚·加拉沙宁也为塑造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做了很多努力,他不仅为新独立的塞尔维亚建立国家组织结构,还利用历史将他的塞尔维亚同胞引向他们曾经被上帝应许的命运。塞尔维亚帝国过去曾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摧毁,但现在是时候重建了。他在一份直到20世纪初才被解密的文件中表示,“我们是伟大祖先真正的继承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并不是什么新思潮,也不是什么革命,而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神话在现代开花的结果。要再次强调的是,这种大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危险的想法,因为它将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都视为曾经塞尔维亚帝国的一部分。
挑战这种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历史观很容易,但要动摇坚信这些想法的人的信念却很难。在20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南斯拉夫解体的过程中,那些古老的历史神话再次浮出水面。塞尔维亚人再次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孤军奋战。1986年,塞尔维亚科学院发布了一份备忘录,以警告塞尔维亚人,他们从1804年第一次反抗奥斯曼帝国以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将要付诸东流。克罗地亚人恐吓在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则迫使塞尔维亚人逃离科索沃。1989年,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前往科索沃纪念科索沃战役六百周年,并在纪念仪式上宣布:“科索沃的英雄主义不允许我们忘记,我们曾经是多么勇敢和有尊严,我们是为数不多的勇于参与战斗并且不会被打倒的民族。”与此同时,在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也在回顾他们的过往,认为他们需要一个大克罗地亚的历史,其中也包含了无数塞尔维亚人的历史。历史并没有摧毁南斯拉夫或导致解体后的恐怖,但诸如米洛舍维奇、克罗地亚的弗拉尼奥·图季曼等政客却巧妙地操纵了历史,他们不仅利用历史动员他们的追随者们,还威胁那些不愿效忠于他们的人。
用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来说,巴尔干半岛拥有的历史比它们所能消化的还要多。一些新出现的民族会担心他们没有足够的历史。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尽管犹太人与巴勒斯坦有着多年的纠葛,但它还是一个新国家。随着来自欧洲各地的移民以及20世纪50年代越来越多的中东移民,以色列若要继续生存下去,非常有必要建立强大的民族认同。但对以色列来说,很难构建一个共同的风俗和文化。对一个来自埃及的犹太人和一个来自波兰的犹太人来说,他们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即便是宗教也不能提供足够的基础,因为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坚决不信犹太教。尽管希伯来语正在复兴,但它还没有形成以色列的民族文学。这使得历史就像一种粘合剂,从而具有特殊的意义。以色列正是在其《独立宣言》中,向历史寻求其存在的正当性。在历史上,这片土地是犹太人出生的地方:“在被暴力驱逐出以色列故土后,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对故土忠心耿耿,始终不渝地希望返回故土,在那里重新获得政治自由,从没有停止过为此祈祷。”离现在更近的历史也成了犹太人故事的一部分。犹太人早已努力设法大规模回归故土:“这些犹太人使荒地变成良田,复活希伯来语,兴建城市与村庄,并创建了一个具有自身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的社会。他们希望和平,但也做好了保卫自身的准备。他们为该地区所有居民带来了进步的佳音,并决心获得政治上的独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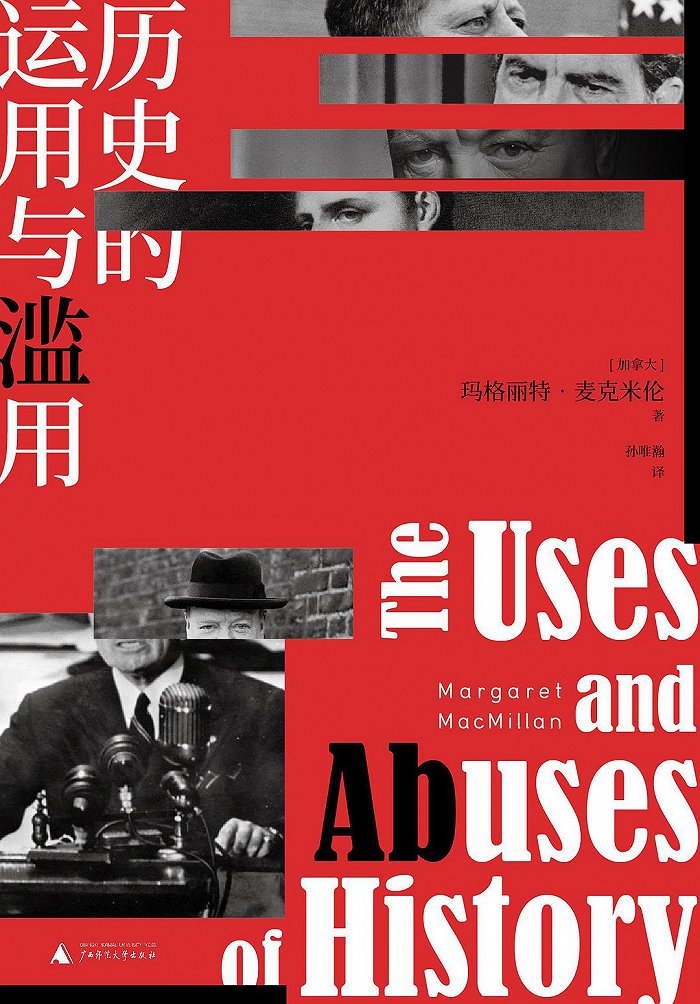
[加]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 著 孙唯瀚 译
一頁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03
1953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了国家教育法和建立大屠杀纪念馆的法案,以纪念大屠杀事件。该法案的作者是教育和文化部长本-锡安·迪努尔,早在以色列独立之前,他就积极参加犹太复国主义的教育和政治活动。他的历史观植根于建立以色列的自主意识的需要。他在议会宣称:“一个民族的自我,只存在于它是否拥有历史记忆,以及这个民族是否知道如何将其过去的经验整合成一个单独的实体。”对迪努尔和他的支持者来说(许多左派和右派都不这么认为),这意味着要教导以色列人,无论过去还是未来,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都永远存在。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流散中,以色列民族幸存了下来,并且一直致力于回到失去的故土。因此,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以色列国家不仅是历史的继承者,还是这段历史的高潮。迪努尔的观点受到很多批评,例如,他在定义犹太人特征的时候排除了宗教因素,而且对犹太人历史的看法过于简单化。但是,他的观点在以色列的学校里很有影响力。一项对1900年至1984年间使用的教科书的研究发现,随着时间推移,犹太人的历史被越来越多地从以色列建国的角度来叙述。在流散的犹太人中,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就是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这是一项“最强烈、最古老”的运动。
民族主义还远未走到尽头,新的民族还在不断出现。这些新的民族也发现,历史对界定自己的身份来说非常重要。20世纪60年代,年轻的德国学者沃尔夫冈·福伊尔施泰因(Wolfgang Feurstein)偶然发现了一群人,他们居住在黑海南岸靠近土耳其特拉布宗港的一个偏远山谷里。和大多数土耳其人一样,这个被称为拉孜的族群中大约有25万人是穆斯林,但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习俗和神话。(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土耳其官方的解释是拉孜人和其他土耳其人一样,祖先是从中亚迁徙到小亚的游牧民族,拉孜语是土耳其语的一种方言。但福伊尔施泰因认为拉孜语与土耳其语所属的阿尔泰语系毫无关系,而是南高加索格鲁吉亚语的近亲。经过研究,他认为拉孜人的远祖原居格鲁吉亚滨海地区,一千多年前被入侵的阿拉伯人驱赶到安纳托利亚,栖居于黑海南岸陡峭险峻的山地,在奥斯曼苏丹控制这个地区之前,他们一直信奉基督教,后来改宗伊斯兰教。)在这位年轻的德国学者看来,他们在过去一定曾是基督徒。于是他开始研究这群被历史遗留下来的人。为了帮助他们记录属于自己的故事,福伊尔施泰因给他们设计了一种书写语言。这些拉孜人开始对自己的过去和文化产生兴趣,而土耳其当局也开始担心起来,因为在面对诸如库尔德人等其他少数民族的要求方面,他们已经遇到了很多麻烦。福伊尔施泰因因此被逮捕、殴打,并被驱逐出境。但即便是在土耳其境外,他也一直想方设法把拉孜故事和诗歌的文本送回土耳其境内如今正在地下运营的非官方学校。随着拉孜人对自己和过去的认识不断发展,他们正在成为一个民族。1999年,第一个拉孜人的政党成立,该党旨在推动在土耳其内部建立一个“拉兹斯坦”。他们的宣言要求扶植并推广拉孜的语言和文化,并鼓励从拉孜人的视角研究历史。如果我没预料错的话,他们终有一天会利用这段历史,向土耳其政府提出一份要求赔偿的法案。
本文书摘部分整理自《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一书第五章,内容有删改,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