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终结的感觉》出版,我65岁。当时距我上一部小说出版已有六年,那是我写过的最长的作品,而《终结的感觉》是我最短的一部。
随着年岁增长,很多事情都在改变着你,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写作上。你会对时间和记忆有更多思考:思考时间对记忆的影响,以及记忆对时间的影响;也会比年轻时对记忆这回事生出更多怀疑:你意识到它是一种更贴近想象的行为,并不像从脑海中还原经历本身那么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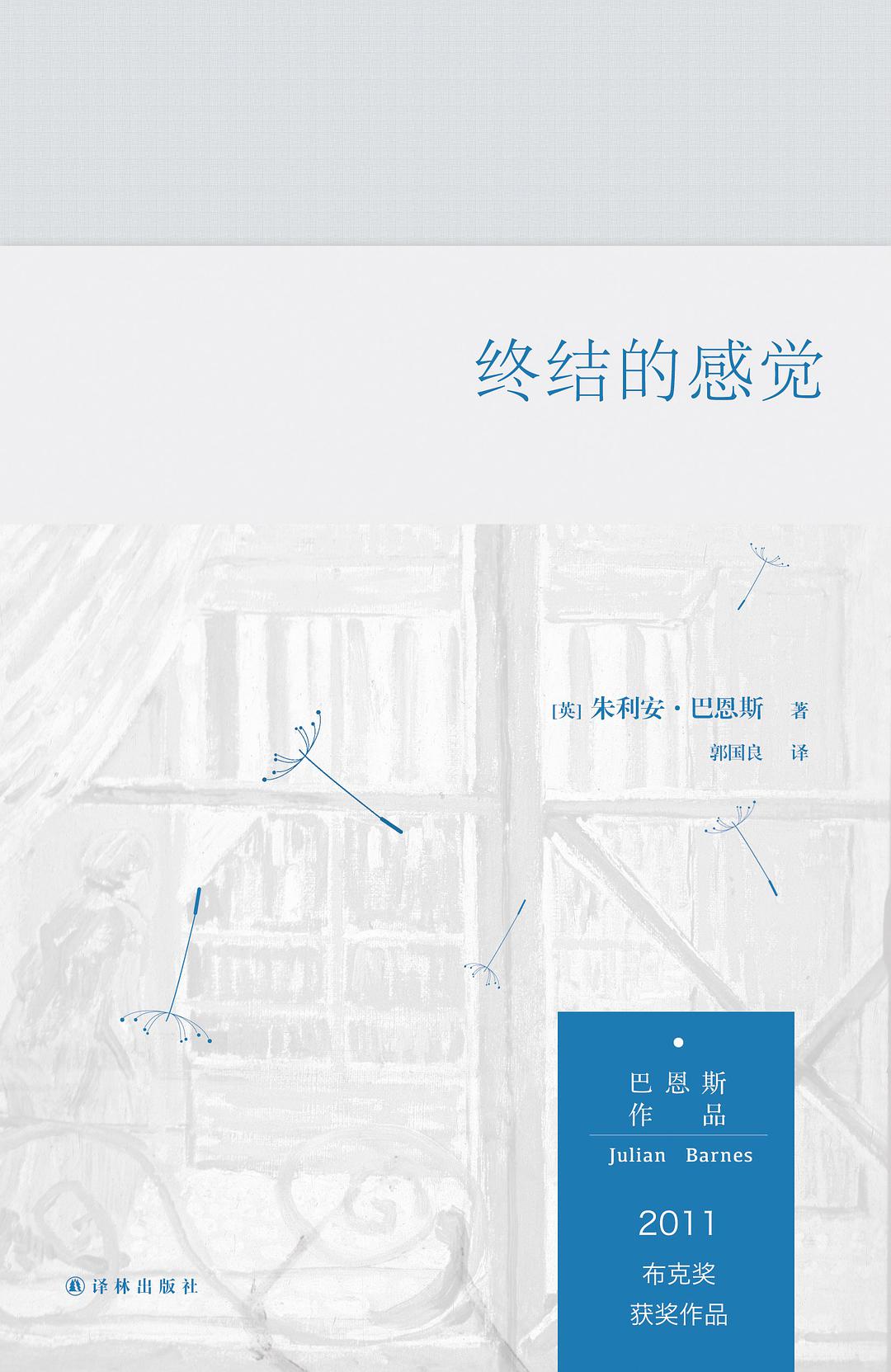
[英] 朱利安·巴恩斯 著 郭国良 译
译林出版社 2012-7
幸运的话,你会在写作中体验到两个变化。一个是,你对自己穿越时间的能力更加自信。说到这一点,不得不提到爱丽丝·门罗——你可以读完她一个30页左右的故事,然后不经意地发觉,一个人物仿佛已在其间走完了他(她)的一生。你会好奇她是如何做到的。在我的小说里,开篇大约写个50页左右,然后中间直接间断40年,再接着写100多页。放在年轻的时候,我应该不会冒这个险。
另一个变化便是认识到不必把所有东西都堆砌进去,其他艺术领域亦是如此。一些画家,到了晚年会任由画布或木材显露出它们自身的纹理。比如朱塞佩·威尔第,他在晚年时期的歌剧创作就谨慎许多。正如他所言,“我学会了在什么时候不加入音乐。”我想,我也学会了在什么时候不加入不必要的句子——这并不是出于体力下降的原因(尽管这也是客观事实),更主要的是认识到了我往往可以通过更短的篇幅来表现更多的东西,同时留出一些空间待读者自己去填补。

每当我写完一部小说,我就会把创作的开端、过程和其中的痛苦通通抛在脑后,因为它们对当下的我不再具有意义。我知道,我早期写过一个念书时关系很好但后来断了联系的朋友的名字,结果直到50岁上下我才发现,他早在二十五年前就自杀了。这本小说的一个主要线索也并非死亡本身,而是那种长期的、阴森的不可知性。我还知道,我希望这部小说是一部思想与精神层面并行的作品。有这么两种模式,正如它有两种速度:在第一部分,是记忆的速度,或反速度,而篇幅相对更长的第二部分将在 “真实”的时间内演进。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敲定这一书名的困难。我最开始想把它命名为《动乱》(Unrest)——因为那是小说的最后一个词。后来一个朋友提出,如果跑去水石书店问店员“你们这有‘动乱’吗”,很可能听上去像是在打听书店劳资关系的情况。所以我果断放弃了。最后,我想出了《终结的感觉》,也征求了朋友们的意见。大多数人都觉得不错,不过有一个人指出,弗兰克·克默德有一部经典的文学批评作品用的也是这个题目(此处指英文原名,中译名为《结尾的意义》)。我从来没听说过,更不用说读过这个作品了(现在也还没有)。我有些不以为然,一心想着,书名又没有版权,他已经占着这个名字将近50年了,现在也该轮到我用了。后来有一些书评出来,纷纷指出我的小说是在与克默德的书 “对话”——有人认为我阐述了他的想法,有人把它解读成了一种友好的反驳。看见了没,这就是互文性。啊——行吧,就当是这本小说给我的一个教训罢。

(翻译:张璟萱)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