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39岁的作家蕾拉·斯利玛尼生于摩洛哥首都拉巴特,17岁时搬到了巴黎。她的第一部小说《食人魔花园》就是2014年在法国出版的,小说讲述了一个性爱成瘾的(nymphomaniac)30来岁母亲的忧郁故事。2016年,她凭借第二部小说《温柔之歌》成为了获得法国文学最高荣誉龚古尔奖的首位摩洛哥女性,在这部小说里,保姆在照料过程中杀死了一个婴儿以及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2017年,她又被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总统任命为特使,负责推广法国的语言和文化。
2020年,斯利玛尼推出了非虚构作品《性与谎言》(Sex and Lies),其中包含了若干有关摩洛哥女性的私人生活的亲身见证。最近即将出版的《他者之国》(The Country of Others)则是以斯利玛尼的家庭史为蓝本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该书的背景设定在1940年代后期至1950年代,聚焦自家母系祖辈在摩洛哥去殖民化时期的经历。目前斯利玛尼与丈夫以及两个孩子居住在巴黎。
为什么会想到写自己的家庭史?
蕾拉·斯利玛尼:得了龚古尔奖以后,我想写一些不太好驾驭的东西,对一个已经肩负了一些赞誉的艺术家来说,很重要的是去做一些有可能失败的事情。我小时候就读过不少传奇故事(sagas,尤指古代挪威或冰岛讲述冒险经历和英雄业绩的长篇故事——译注),我想这个三部曲的构想应该会很有趣。跟随某个角色去经历他的生与死,以及见证社会的变迁,对我来说是一桩乐事。但这本书也来自某种挫败,我在摩洛哥长大,读过很多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的作品,于是就想到,“我对这些东西已经懂得很多了,但对自己的国家却知之甚少。”西方的人们只会把我们看成穆斯林,因此发出这样的声音就很关键——“我们有着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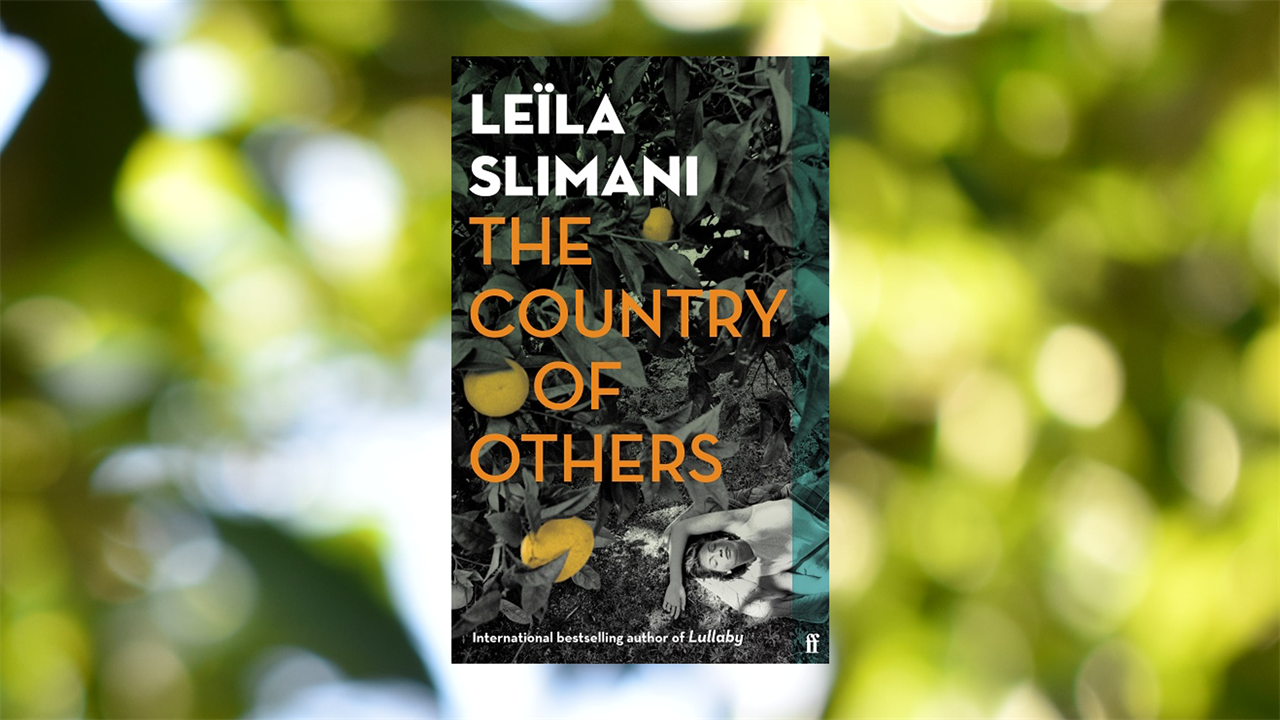
你之前是否想过以别人的家庭为蓝本来创作传奇故事?
蕾拉·斯利玛尼:没有。从一开始我就很清楚,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祖辈的,小时候我的祖母和我讲了许许多多关于她自己以及她的婚姻的故事。我始终把祖辈看作某部小说里的角色。我祖父的腹部有一道自上而下的伤疤,有一天我问他:“这道疤痕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以前打仗的时候,我曾经在德国和一只老虎对峙过。”我14岁以前都一直对这个故事深信不疑!这十分幸运,我的祖辈并没有把实情告诉我。

这样你就能放飞自己去讲故事了?
蕾拉·斯利玛尼:正是。而这也让我明白了一点——假如我想要自由,想要那种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那讲故事就是必需的。我是那种很容易产生挫败感的人,因为我什么地方都想去,什么书都想读,各种各样的激情都想了解,除非你是作家,不然这些念头就没有什么实现的可能。当了作家以后,你就可以在别的时代生活,可以坠入爱河,甚至还能把某个人杀了!你可以为所欲为,这真是太棒了。
《他者之国》的设定和结构和《温柔之歌》以及《食人魔花园》有所不同,你是否认为自己正在回归自己熟悉的主题?
蕾拉·斯利玛尼:我一直在写女性、霸权和暴力。我念兹在兹的是自由:我们如何可能既保持自由,又以妻子或母亲的身份与他人保持连接——同时尽力去做一个独立的个体?我还写过不少幻想破灭的情形。我的第一本书《食人魔花园》是关于性的幻灭,《温柔之歌》是关于母性的幻灭,我最近的一本书则关乎流亡者与移民的幻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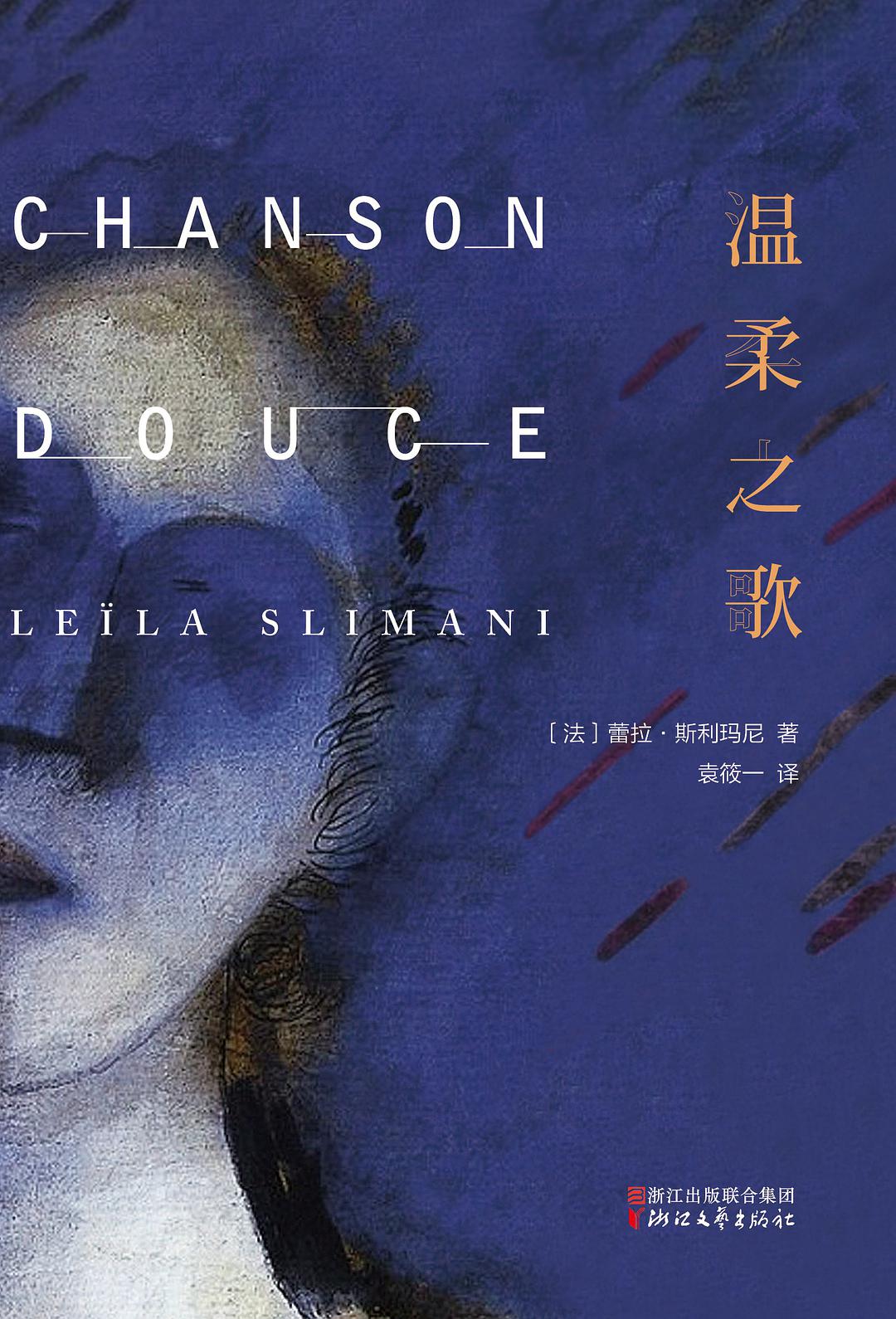
[法国]蕾拉·斯利玛尼 著 袁筱一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 2017-8
你的书里几乎都是肺腑之言,谈到性也没有任何掩饰。在你看来,以这种粗犷而直白的方式来描绘你的家庭成员,是否会遇到困难?
蕾拉·斯利玛尼:从我开始写书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不再是我的祖辈,而是玛蒂尔德和阿米恩。因此,我在刻画性爱感受和暴力场景时也不受任何拘束,这反正不是现实。你试图追寻真相,但这种真相不是你在法官面前追求的那一型——它是关于情感与可靠性(credibility)的真相。
是否有一条贯穿三部曲的主线?它和女性生活在三代人之间的变迁有关吗?
蕾拉·斯利玛尼:是的。第二部分会讲到我母亲那一代(她是个外科医生)以及她的兄弟和我的父亲(在政府做经济学家),时间大约是1960年代末。这代人想要改变摩洛哥,希望来一场革命,但最终却变成了资产阶级。这本书将会谈及你对自己的失望。最后一部关于移民。时间设定在1999年,也就是我到法国的那一年。它会谈到伊斯兰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兴起以及我对此的感受,身为一个摩洛哥裔法国人,我遭到了有着相同背景的伊斯兰主义者的背叛,同时也受西方的种族主义者的不齿,他们对我的观感与我的自我定位截然不同。
你一向不喜欢在访谈里提到宗教。依你看,小说是否给了你一个用自己的话来表达自身感受的机会?
蕾拉·斯利玛尼:确实如此。每当人们问到我的身份认同,我就会倍感沮丧,因为三言两语根本说不清我是谁,也道不出当中的复杂性。所以我才觉得我需要写至少三本书!当摩洛哥人告诉我说你只是个操着法语的资产阶级时,我想告诉他们:“读一读我的书,你就能明白情况远比这复杂。”

[法国]蕾拉·斯利玛尼 著 袁筱一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 2018-3
你刚才提到了失望。你认为人类应当如何去承受生活中的失望?
蕾拉·斯利玛尼:我小时候第一次感到失望,是因为我意识到生活和电影里的不一样,生活就是生活而已,它是无聊的。我会读书学习,也许会结婚,生孩子,去超市购物。对我来说,我有一个选择:杀了我自己或者做一个作家,过我现在所拥有的这种生活。我不想过我父母或者普通人的生活。
假如你不是作家,你会如何去承受失望?
蕾拉·斯利玛尼:我会变成一个特别刻薄的女人。可能还会酗酒!我会对所有人出言不逊。我会做一个十足的混账!
你现在正在读些什么?有哪些枕边书?
蕾拉·斯利玛尼:汤姆·莱斯(Tom Reiss)的《东方主义者》(Orientalist)。我还在读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的《智血》。她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三部曲里第三本书的灵感就来源于她。
最近读过的最精彩的一本书是什么?
蕾拉·斯利玛尼:亚历珊卓·玛札诺-列斯内维奇(Alexandria Marzano-Lesnevich)的《撕开的真相》。这本书很不好读,也是用了一番心思的。它揭示了人类灵魂的含混性,我们的信念和情感之间有时会出现鸿沟。
你最敬佩的当代作家有哪些?
蕾拉·斯利玛尼: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扎迪·史密斯和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契。我尤其佩服米歇尔·维勒贝克,我不同意他的世界观,但我还是认为他是伟大的作家。我很喜欢桑德罗·维罗尼斯的《蜂鸟》,这是一部真正的佳作,趣味盎然、动人心弦并且发人深省,我读罢后哭得像一个小女孩。
(翻译:林达)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