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为我们的家庭住处之前,我们位于奥德省的房子乃是一处把废旧毛织品转化为再生毛的回收工厂。它建于1900年左右,地处河畔,一度拥有两个开放式的大平层。成捆的羊毛先通过绞车被送上没有封顶的顶楼,然后经过地板门进入一楼,由一堆胡乱摆放的新式机器来处理,这些机器的动力仅由一座小火炉提供。厂里经常很吵闹,即便在冬天也很热,夏天的温度则高得令人难以忍受。化学物质产生的酸雾浓厚到了令路过的小孩双眼感到刺痛的地步。每天下班后,十几个男女工人会下到凉爽宜人的地窖里,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一桶桶葡萄酒。房屋本身是劳动场所,但也是人类关系的空间,紧张、怨恨与友谊在此相互交织、难解难分,对完成工作而言,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身体、机器、火炉与河流。
法国城市的工业化相对较晚,这间建筑的工厂生命也因此而结束于1950年代,以水泥浇筑的砖瓦结构逐渐倾圮,久而久之变成了一堆钢铁架子,直到1980年代我的表兄弟来了这里才有了改观。余下的只有一捆捆已经在墙上留下墨印的账本,以及渗透进地板和房梁的羊毛油脂,在夏季高温下不断流出。料理这些厚重的黑色油脂费了我们很大功夫:地板每年要重新粉刷一遍,地毯也需要熨烫,小孩子的脚每天要仔细洗个两遍。但麻烦每年还是会重演一次,一代人辛勤劳动的副产品使得另一代人的日常家务更趋繁重。
扬·卢卡森(Jan Lucassen)的新作《工作的历史》(The Story of Work)旨在让我们仔细关注这一悄无声息却连绵不绝的过程:人类过往的工作后果渗透进当下,将我们与自己的祖先以及他人连接在一起。他提出,工作的社会性(sociality)具有基础意义。而这也点明了为什么工作不仅对作为个体的我们是重要的,对作为集体——即人们,乃至于人类——的我们也是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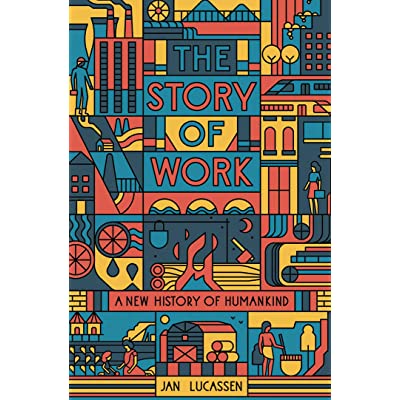
这一主题使卢卡森颇为宏大的副标题变得不无理据了——“人类新史”,千万不要被这个雄心勃勃的宣示所迷惑。这部工作史其实没有唯一的线索可言。卢卡森扎实的经验研究于无声处让关乎工作的宏大意识形态与理论各归其位。在他的故事里,工作对我们没有补偿作用,驱使我们的也不是因工作而得解放的承诺;工作既不单单是无尽的阶级斗争,也不是德性高超的市场发动机。卢卡森所谓要写一部人类工作史的提法,其实没有那么雄心勃勃,而是谦虚有余的。他无非是想证明:我们正是通过工作才让彼此联系在一起。
我们需要通过工作来维持生存,这是人类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我们需要吃喝、住处、照料晚辈、有条件的话尽量不要过得太苦。但工作随着时间推移而发展出的不同形态,也赋予了我们的个体以及集体生活以意义。工作是一个关乎人类合作的故事,我们正是通过工作才认识到了什么是公平和正当。工作随时代而发展,而卢卡森则对这一进化给出了有说服力且全面的解释。但它也是一种存在性的经验:我们可能会用手来工作,但工作也总是发生在我们的脑子里。工作乃是我们在共同生活中所拥有的最为经久不衰的道德指标,尽管卢卡森本人的表述还没有这么强。
既如此,工作本身以及有关工作的政治和道德问题,在疫情期间变得如此之突出,也就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及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在新冠疫情袭来之前已经有急剧的增长。但在区区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平时颇为低调私密的、针对临终者及病人的照料类劳动,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为了公众的关注焦点。谁是真正在做事的人,就此变得一览无遗:卫生工作者——很多人是黑人和棕种人,还有不少人是移民——他们取消了休假,并且工作量翻倍;女性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去到照护机构的床前;交通工人载着这些换班的工人,驾驶着近乎于空荡的巴士和火车来往于一线。这些人已经达到自己的极限,在众目睽睽之下服务着集体的利益。


2020年夏天,英国政府催促所有人赶紧打开家门出来工作,希望能重振经济,其传递的信息是,我们也可以通过“回到工作岗位上”(事实上很多人在家工作的强度比坐办公室还要大得多)以及消费源自他人工作的产品,来为集体利益添砖加瓦。与当时许多人的直觉相一致,实际的情况是,政府是为了某个社会与经济模式的利益才要求我们返工的,这一模式不仅不关心我们的最佳利益,甚至连我们的基本需求也无法满足。富人们可以仰赖Zoom软件,可以不断订购做工精致的外卖。其他人则没有多少选择可言,只能被迫出门、在外用餐以及在外面解决各种麻烦。还有千百万人失去了生命。集体努力落到了这般下场,和我们当初的预期可谓大相径庭。
过了一年,又有人开始抱怨赋闲在家的工人太沉迷自家的菜园子,或者被宠坏了的大学毕业生太矫情,不愿意认真学搬砖,政府频频拉响此类警铃,其实质无非是帮助自家人耍弄一些低级花招,而非为集体利益做实事。
部长和官员们不仅破坏了封城的规则:他们工作时的紧张焦虑程度也经常和我们不在一个频道。自雇者(self-employed)和此前做过小生意的业主如今忙于零工经济,以维持已经是他们共同所有的房产。疫情之下,人们在工作方式上的差异并不公正,当然也并不平等,这是众所周知的。

通常来讲,工作这条共同主线的能见度不算高。工作占据了我们的绝大部分生活,以至于我们一般无暇顾及深藏其中的道德故事与历史结构。但我们对工作所怀有的强烈的矛盾情感,向来距离表面不远。“坦白说,”卢卡森引用了一段1960年代以来即处于失业状态的英国矿工的话,“我恨工作。当然我也可以千真万确地说,我爱工作。”他仇恨的乃是遵照当权者制定的游戏规则去工作,而他热爱的则是与他人一起工作及其带来的社群感、目的感与地位感。下班后在凉爽的地窖里享用一桶桶美酒,不仅是劳动的回报,也是工作本身的某个重要维度的象征性表达。
用卢卡森的话来说,“纵向服从”与“横向合作”之间的平衡总是脆弱而不易维持的。但他也认为,从总体上看,工作史当中约有80%的时间是关乎对等性(reciprocity)的,关乎人们为了相互的利益而为他人服务。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无情而麻木的自上而下式管理甚至于对不受其直接影响者也存在着羞辱性:因为它直接违反了潜藏在工作史当中的深刻规律。
卢卡森花了很多笔墨来充实他的论述。这是一项全球性的、史诗一般的历史学研究,旨在深挖劳动史这一庞然大物,力求以坚实的概念框架将其呈现出来。而这本书也实践了他大加推崇的对等性。“人类似乎能想出无穷尽的办法来组织手里的工作,”他写道。这本书的道德之美,恰在于它对组织方式的多样性给予了用心的尊重。
他的故事开门见山,谈到了狩猎-采集者社会以及对等性的诞生。诚然,这是一个竞争与生存的故事,鲍里斯·约翰逊首相近来提出了“位于包装袋上层的玉米片都是靠挤压下面更小的玉米片才上位的”这一有关自然选择的愚蠢类比,但早在一千年以前人们就已经理解了为相互的利益而工作所带来的进化优势。“自吹自擂之人、大人物”及其“膜拜活动”,都出现在集体工作开始产出剩余产品之后。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出现之前,曾有过巧取豪夺剩余产品的现象,其方式之一,便是某些自封为王的神庙和小国首领会表现得俨然自己对财富已经拥有某种权利一样。不平等的历史即发端于此。
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500年之间,如同许多人会记起的教室墙上的各类教学挂图一般,不同种类的工作开始分流并被重新分配——“我们不妨称之为一种伪装起来的对等性,”卢卡森说。但如果“横向合作”总是能很好地推进工作,“纵向服从”取得优势也就为时不远了。一旦把战俘作为奴隶来使唤变得比处决他们更加划算,战争就成为了关键。一个颇有些苦涩的讽刺是,在世界尚未摆脱这种格局,亦没有完全清算其余毒的情况下,现今“世上最稀松平常的事”——即工资劳动以及它从我们这里买走的自主性——就开始萌芽了,与之同步兴起的还有全球性的“不自由劳动”市场。
工作史中的个别篇章继续渗透进当下,并带来了更为有害的后果。卢卡森提到了贝宁的奥鲁阿尔·柯索拉(Oluale Kossola)的事例,此人1860年代被抓,然后在强迫之下沦为了种植园的奴隶,1920年代后期他曾对访问自己的黑人文艺复兴作家、人类学家和电影制片人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表示:“一名白人男子四下打量……然后开始挑选……最后花130元钱买走了一个奴隶。”

卢卡森提醒我们,不自由“绝不是显而易见的,人们也很难接受它就是生活的真相”。实际上,在工作史当中并没有多少事情是不言自明或者很容易就能判断是非的。卢卡森从事研究时所秉持的全球性与历史性视野,意味着许多习以为常的、有关工作史的欧洲中心主义预设需要仔细加以检验。货币化的社会在工作发展成如今我们熟知的样貌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但在公元400年至1000年间的印度和欧洲,以货币和交换为中心的经济形态这一工资劳动的必要条件,其实并不稳定,它来得快去得也快。
所谓随工业化而到来的“西方与其它地区”之间的“大分流”之论,不过是无稽之谈,工作经济的分流与合流始终就没有断绝过。19世纪行将结束时,欧亚大草原上仍旧存在着奴隶制,而不自由的劳动则广见于20世纪并且延续至今。哪怕是一些进步派的工作理论,也并没有取得其创始者所希望的成果。另一颇为辛辣的讽刺则是,“20世纪里一切自由劳动的大规模倒退,几乎都发生在打着工人天堂这类旗号的地方。”
有时,透过如此细致的阅读来了解工作的衍生和分化,其本身似乎也是一种艰苦的工作。但我认为,卢卡森坚持广度与细节并重的原因在于,他希望我们能理解:为了摆脱强迫劳动而经历了多么漫长而艰苦的斗争,为了追求以一种富有意义的、能增进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认识的方式来展开工作的权利,我们曾付出过漫长而艰巨的努力。纵观整个工作史,并没有什么模式是理所当然、势所必至的,而这也意味着未来工作的面貌并不一定要和现在一样。
在书的结尾处,卢卡森谈到了一个新近的现象,即西方白人男性的养家糊口主角地位丧失了,他们原本有权获得有意义的工作并因之而享有自主性,但这一点也趋于式微。袋中玉米片的新一轮“洗牌”所带来的政治后果是极度不对称的,人们想必会好奇:要是女性也像这样,提出各种关乎地位、工作和资格的抱怨,且这些抱怨得到认真关注的程度能达到男性的一半,那情况将会怎样?卢卡森开篇即提到过,女性总是比男性工作得更卖力。但历史上的实情似乎并不总是这样,尽管他花了很大的功夫来论证这一说法,也参考了一些有关女性劳动的重要历史学成果,如艾玛·格里芬(Emma Griffin)对19世纪的研究。
繁重的劳动屡屡被家庭这一建制所掩盖。一般而言,为小孩洗脚与保养地毯之类的上流社会诉求并无关系,而是为了避免死亡和疾病。正如我们所有人在后来所发现的,你没有办法简单地用吸尘器把病毒吸走,喷消毒液也不一定能完全清除它:在诸多残酷的障碍面前维持生存这项事业,乃是漫长且劳神费力的,它无聊且有如梦魇一般。就工资劳动带来的能动性和独立性而言,受益最大的无疑是女性。但这种不断地鼓励女性“埋头苦干”的文化也含有深刻的荒谬性,说得好像女性就从来没有苦干过似的——而所谓“集体”利益的说辞经常也只是有利于男性的。
扬·卢卡森的书处处皆在表明,如果真的要在政治上重视工作的公平性,那必将触动一些深层次的神经,正如最近工党所意识到的一般。但如果不去聚焦女性的工作,我们对人类工作史的叙述就依旧具有片面性。
黑死病爆发后,全欧洲皆在对人口流动施加各种各样的限制,以防止人们利用劳动力短缺来谋取好处。一个很著名的事例是,工人理解并且也赞赏随着工资劳动的兴起而日益增长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但他们并没有拥有这两样东西。女性也得到了好处,目前我们或许应当把这部分故事多讲给自己女儿听一听。民族主义移民政策所带来的短期民粹主义好处,固然一时可以安抚曾经负责养家糊口的男性的不满及其机会主义式的“自吹自擂”,但卢卡森提醒我们,这当中其实潜藏着一段远为宏大、并且可能也更具力量的人类历史。我们将继续工作,要阻止我们寻求集体的意义、能动性和尊严乃是不可能的,用前文提到的那位英国矿工的话来讲,要让我们不热爱工作也是不可能的——无论这需要我们付出何等代价。
本文作者Lyndsey Stonebridge系伯明翰大学人文与人类权利教授。
(翻译:林达)
来源:新政治家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