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在她的新书《十二凯撒》(Twelve Caesars)里对埃拉伽巴路斯(Elagabalus)的生活展开了引人入胜的考察,这个男人的行为之出格,据称远甚于卡利古拉和尼禄。埃拉伽巴路斯又名赫里奥伽巴路斯(Heliogabalus),只做了很短时间的罗马皇帝,在尚未成年的时候就被禁卫军暗杀了。但在玛丽·比尔德的脑海里——且不说心里——他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每当记者问起当今的政客令她联想起哪位古代皇帝时,她总是提起埃拉伽巴路斯的名字。面对那些习惯于简单粗暴类比的人,比尔德不时会打破他们的舒适区,她表示听说过这小子(指埃拉伽巴路斯)的人几乎为零。如果进展还不错的话,接下来她就会让这些大感困惑与不解的人去看《赫里奥伽巴路斯的玫瑰》,这幅画创作于1888年,作者是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Lawrence Alma-Tadema),画中的这位皇帝在聚会上施展计谋,试图以堆积如山的玫瑰花瓣让来客窒息而死。“一旦你看懂了那个故事,你就能更好地理解什么是暴政,”她一如既往地带着一种颇为享受的语气说道,“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哪怕是皇帝的慷慨也可能会要你的命。”

实话实话,我以前也没听说过埃拉伽巴路斯,也没有读过比尔德的书,更尴尬的是,书里提到的几乎所有人我都不怎么知道。但出乎我意料的是,这居然一点也不要紧。《十二凯撒》非常有吸引力,且不仅是因为作者本人笔法的风趣性。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很长,它降生时的世界状况,已经与作者构思它的那段时日相去甚远。从本质上讲,它的核心关切是从凯撒到图密善的罗马皇帝形象多个世纪以来对文化有何影响,在当下显得十分应景,正好应和了英国当前与雕像的复杂关系(指推翻过去殖民者、暴君等雕像的运动)。
在剑桥家中的花园里,夏末的阳光让比尔德显得神采奕奕。她有个很著名的观点——认为学生不该推倒罗德斯的雕像(指牛津大学立有殖民主义者塞西尔·罗德斯的雕像,该校学生曾发起活动,要求将此雕像从奥里尔学院撤去,以示对其种族主义过往的抵制)。不过,这对她来说也不是原则性的问题,并不适用于一切地点的一切雕像。“我十分乐见某些雕像的倒塌,总是有已经倒掉的雕像,也总会有雕像被推倒。那种认为不能移动任何东西的想法是疯狂的。但我有所保留的一点是,受人瞻仰并不是雕像所要实现的唯一功能。《十二凯撒》就谈到了有关权力形象的一些更为重大的问题。雕像也可以教导我们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它可以告诉我们君主是什么,也可以告诉我们他不是什么。这些都属于争论的一部分。”

进一步讲,一座雕像的意义可能会一再发生变化。例如,德比郡的查茨沃斯庄园里有一座安东尼奥·卡诺瓦(Antonio Canova)1804年受委托创作的拿破仑母亲莱蒂齐亚·波拿巴(Letizia Bonaparte)雕像(拿破仑过世后,它被卖给了查茨沃斯庄园的主人德文郡公爵)。卡诺瓦参照的原型是一座古典的女性雕像,当时被广泛认作(但后来被证明为误认)阿格里皮娜(Agrippina)。哪个阿格里皮娜呢?是奥古斯都的外孙女、广受敬重的罗马统帅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之妻大阿格里皮娜吗?抑或是毒杀克劳狄皇帝的恶后、暴君尼禄之母——或许也是爱人——小阿格里皮娜?如比尔德所言,无论将这座雕像与哪个阿格里皮娜相联系,都会对“母亲夫人(Madame Mère,拿破仑母亲的外号)”产生政治上的影响,继而牵连到她的儿子。不过,待到雕像在查茨沃斯庄园安放妥当后,一切含沙射影的东西就都消失了。一件一度面临争议的艺术品——它曾向帝国权力与王朝提出尖锐的问题——以前是,现在也不过是一位著名艺术家的得意之作。它的大理石曲面与褶皱也许是巧夺天工的,但也多少给人一种乏味感,一切深层的意涵都被剥去了。
从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到《嬉春》系列电影,再到古代钱币以及阿斯特克斯的系列冒险漫画,罗马皇帝的形象几乎无处不在,比尔德何以认为它对包括臣民、公民和统治者在内的人类均有深远的影响呢?或者这本就是个愚蠢的问题?她摇了摇头。“对此没有简单的答案,部分原因在于它的历史性。中世纪早期欧洲君主认定自己将成为罗马皇帝的后继者,其由来即在于此。这是一种统治者谈论权力的方式,但保持着安全的距离。比起谈及你的曾曾祖父在200年前施行的暴政,讨论皇帝要轻松愉悦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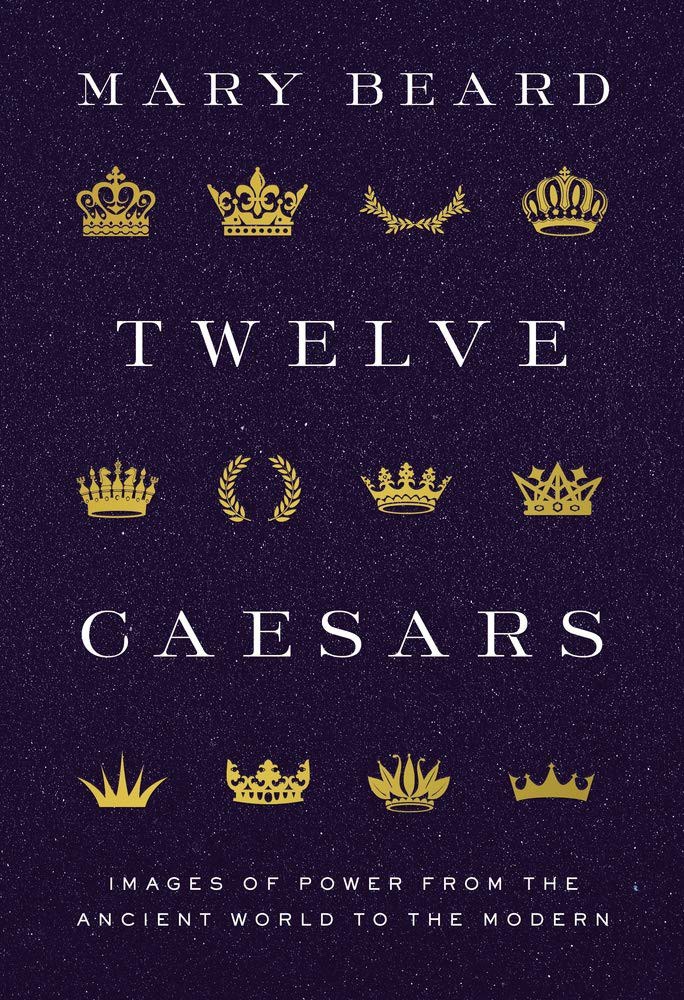
“但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古罗马历史学家,首次提出了十二凯撒的概念,某种意义上也是比尔德新书的精神先驱)也不容忽视,他的观点富有教益,包括一切琐碎的、不无八卦性质的细节。如果你说某个人杀掉了95个元老院成员,那会有些难懂。但如果你说他用笔尖摁死了一群苍蝇(据说图密善干过这种事),那就好理解多了。这就像玫瑰花瓣一样:想起它们,你彷佛就在那场晚宴的现场。”

比尔德与丈夫目前住在一栋很大的维多利亚式房子里,打个车可以去剑桥的市中心,她的丈夫是一名专攻拜占庭艺术的历史学家。这栋房子坐落在两条隧道之间:第一条隧道位于前门,上面满是紫藤萝;第二条则由书架、书本和玻璃构成——它其实更像一条走廊而非隧道——连通房屋与花园,比尔德就在花园里做研究。她告诉我,这种空间几乎是千载难逢的:当她安全地呆在里面时,便不太会受到干扰。她轻描淡写地提到了自己的工作量,而我所感受到的唯有一股斯达汉诺夫式的(前苏联顿涅茨克矿区采煤工人斯达汉诺夫于1935年8月30日创造了一班工作时间内以风镐采煤102吨的记录,超过定额13倍,此事迹在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得到广泛传播,形成了斯达汉诺夫运动——译注)冲劲。当我们聊到她这本书所依托的讲座时(2011年在华盛顿开设),她爽快地承认说,一旦决定要写某个主题,她在接下来的一年之内就不再去想它了,此后一直到下笔才会开始构思观点。我想,在另一种生活里,她大概会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

[英] 玛丽·比尔德 著 王晨 译
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8年
然而,另一种生活与她的距离也并没有那么远。身为剑桥大学的古典学教授,比尔德明年就将退休,她在这所大学执教已有40余年。她退休后打算做些什么呢?多上电视吗?“是的,”她说,“但你必须现实一点。电视机前的观众总有一天会对我感到厌倦的。”(BBC二台的下一季《文化透视》于9月24日开播。)但即便如此,她还是打算能做多久就坚持多久。在她看来,自己登上荧屏总归是有益无害的:“身为一个无可否认地老去的年迈女性……人们可能会说一切都不曾改变(对年迈女性而言)。众所周知,他们无非喜欢用我们这种人来装点门面。然而对女孩们来讲,能见到不同类型的女性乃是意义非凡的。”
她是否也曾在某个时刻感到自己有必要妥协,扩充一下衣橱,打几针肉毒?(她2010年在詹妮丝·哈德洛的鼓动下开始上电视,哈德洛当时是BBC二台的负责人,曾在休假时读过比尔德有关庞贝城的著作。)“我想要是我早一点上电视,也许就会做这些事了。但后来某一刻你又会想:我没法把自己弄得特别赏心悦目,还是不要做这些事来羞辱自己了。至少我在电视上看到的还是我自己。我在某种意义上掌控着局面,尽管结果是时好时坏的。”
但这种坚持做自己的决心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出名以后,比尔德便不得不忍受一些社交媒体上的恶毒攻击,其恶意之强在我看来几乎前所未见。面对这等抨击,她如何能保持笑脸和理智?“要做好心理建设,不断暗示自己:我脸皮奇厚无比,刀枪不入。”不过哪怕到现在她也很难做到这些。“当你真正被人批斗……你就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了。你眼睁睁看着一条条的推文纷涌而来,每隔10秒就辱骂你一轮。你明白自己应该赶快关掉它,但这是不可能的。你被反复地锤击,遭到各种敲打。这是一场共谋的袭击,但其实施者也是一个个独立个体——面对这些你几乎是束手无策的。”
她对待互联网“喷子”的态度——2013年时,她和某位喷子交上了朋友,和他共进午餐,后来还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信——与对待暴君的态度截然不同,对于后者,她抱有相当程度的(可能有些大胆的)同情心。“同情君主和当今的风气格格不入,”她说,“但这肯定是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之一:惊悚到可以把人吓尿床。你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缺陷的人……你就是个男人而已。”
在疫情期间,比尔德在家中参与《文化透视》节目。她很乐意做这样的事。她感到这十分重要。但她如今也认为,这个时代的艺术界在谈到资金问题时,常会诉诸一种她不太赞成的论证。“人们常说艺术让我们感觉更好了,对此我完全同意,但我觉得这种思路归根结底是有危险的。我们需要艺术的真正理由,乃在于我们需要理解自己所经历的究竟是什么。我不会停留于此然后介入诸如我们更加需要什么之类的问题:要疫苗还是艺术?这个等式是错误的。人们走出危机的方式,是从中吸取教训。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其原因何在?如果我们想要深究瘟疫和流行病,那诸如《伊利亚特》这样的西方文学作品正好就是以瘟疫开头的!艺术具有根本性,也是我们必须为之而奋斗的。”

不过推送与拉拢这两个动作也在同时发生。政府在考虑裁员,这可能会波及到别的领域,首当其冲的便是博物馆。从政治上讲,重视馆藏的传统已经发生了改变,承诺将文物归还给它的第一故乡成为主流。“如果未经周全的考虑就这样做,同样会有危险,我认为过于追求速度以至于弄得像膝跳反应一样,也是成问题的。”比尔德是大英博物馆的受托人之一,她希望这样的争论能够服务于更远大的目的。“一想起心爱的文物即将离你而去,难免会联想到前期的投入,哀伤和痛苦也随之而来。未来50年里博物馆将会有怎样的命运?我们也许会让文物四处流动,而非让四方的人们前来参观。装满一飞机的文物也许好过装满一飞机的人。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去卢浮宫。这是高度特权化的。或许我们应当让伟大的艺术作品走向人们。”
她的学生状况如何?疫情对其有怎样的影响?“我为他们感到惋惜。大学几乎就等于深夜醉酒以后跟人谈天说地。要批评他们并不难:哎,这些人真是不懂珍惜。但那正是他们该做的事情。”在教学过程中,她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熟识的学生更可能出现此类情况(真正受苦的是新生)。那学校里的氛围又怎么样?我们对诸如不给发言平台以及取消文化这类东西已经耳熟能详了。“有不少夸大成分。但也绝非空穴来风。”她曾经听闻有学生不愿意读奥维德的《变形记》,理由是这部作品美化强奸。“我在70年代的课堂上教授它的时候,主旨还是陶醉(ravishment),而不是强奸。性别暴力被掩盖了,但后来的几代人发现了它,这很重要。但我想说的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还是应该阅读它。奥维德这样的天才诗人对强奸问题是不至于坐视不理的。”
对于跨性别者权利,她的感受也类似:这些事情是必须加以讨论的,无论有多么艰难。剑桥大学的纽纳姆学院只招女生,她曾在那里完成本科学业,目前担任研究员。“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学生说自己是什么性别,那就是什么性别。如果有人说自己是女性,那就是女性。但这一切经常容易与一样绝大多数人并不会花时间去思考的东西相混同,那就是关于性和性别的哲学(philosophy of sex and gender)。与许多高层次理论类似,它对我的日常生活并无多大影响。我们完全可能既对一些跨性别者的遭遇表示愤慨,又感到这当中还存在着有待解决的哲学争论。”她认为生理性别是存在的——而某种老式的厌女心态也在卷土重来:女性会被扣上诸如“巫师”之类的帽子。“这是一场可怕的零和游戏。我太难过了。好人会被两面夹击,受双重伤害。不过如果你有学者身份的话,那你还是得谈论那些必须付诸公论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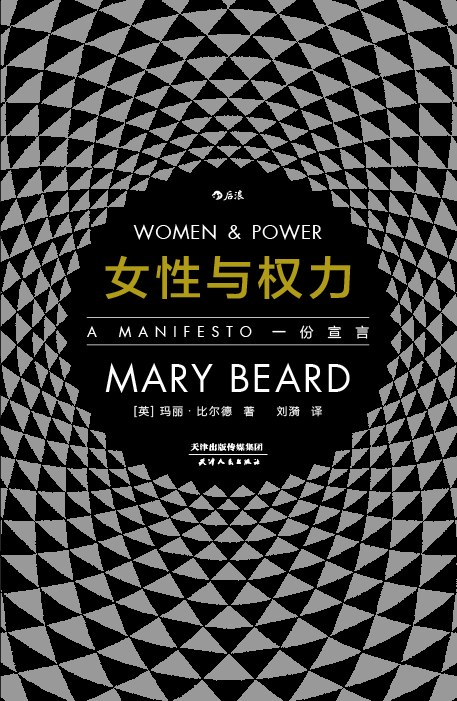
[英] 玛丽·比尔德 著 刘漪 译
后浪丨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9年
眼下令她颇受震撼的是,她年轻时支持的那种女权主义或许有些幼稚。“我当时想,只要托儿所、儿童保育、避孕、堕胎和同工同酬这些问题得到解决,那我们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但情况并不是这样。”即便我们有了以上所有东西,我们还是要为一些尚未拥有的权利而斗争:“真正重要的是头脑里的观念,一些习以为常的预设依旧根深蒂固。”在什鲁斯伯里,也就是她长大的地方,女权主义对她而言很大程度上只停留于理念层面;年少时阅读西蒙娜·德·波伏娃和杰梅茵·格里尔(Germaine Greer),固然能有智识上的快感,但这些书似乎没有产生什么实践上的应用。她的母亲是小学校长,没有上过大学,希望女儿能拥有一些自己不曾有过的机会:“我不认为有人会说工程学不适合女性。”
但当她走向世界,却发现性别歧视无处不在。有一段时间,她在剑桥大学教书时是系所里唯一的女性。“这种局面会彻底把你边缘化,但它也让我的内心愈发坚定了。我在和这些男性打交道的时候非常自信。本科的时候我还照顾过其中一些人。我发明了一整套言辞技巧,例如在这些人喋喋不休之后称他们为‘男孩子们’。‘再叫得大声一点,男孩子们!’我会这么说。我能反击回去。”
“但一个人的被排斥感也来自日积月累的琐碎小事。情况并不是有个人坐在那里然后说:你在这里不受欢迎,亲爱的。我们开会时会准备一些咖啡托盘。会议结束后,男孩子们就自己走了。而我和秘书则留在那里洗杯子。渐渐地,我开始(直言不讳地)说,‘劳驾,谁能过来取一下托盘?’”她与其余的女性也保持着团结。在攻读硕士期间,她参加了一个提高性别意识的小组。“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买了一副窥镜(specula,这种词只有古典学家才会用),这样大家就能坐下来用镜子找到自己的子宫颈。”
她想念大学生活吗?在我看来,这段经历在大大小小的方面塑造了她。“那是一次重要的转变,”她对此表示同意,“我快满67岁了,眼下的问题是:我还能有10年或15年的健康生活吗?在此之后一切都会走下坡路。死亡对你而言是肉眼可见的。正如我的某位朋友所说,60岁以后染上的疾病大都会要你的命。但我还是乐见它的到来,为更年轻的人让位是至关重要的。”那她是否算是学术意义上的卧床不起者(bed-blocker)?她笑了。“我这不是已经退休走人了。我很享受做学问,但也有其它一些事情是我可以做的。”
本文作者Rachel Cooke是一位记者、作家。
(翻译:林达)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