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5月的一个晚上,C·P·斯诺,一位受欢迎的小说家和前科学家,在他的母校剑桥大学的一场贵族和学生聚会上发表了演讲,题为《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斯诺认为,文学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之间存在着相互不理解的鸿沟。
“非科学家总对科学家有个根深蒂固的印象,认为他们是浅薄的乐观主义者,不了解人类的状况,”斯诺说,“另一方面,科学家认为文学家和知识分子缺乏远见,对他们的同胞特别不关心。这在深层意义上来说是反智的,急于把艺术和思想都限制在存在主义时刻。”
斯诺对他的演讲并不抱太大期望。“我感觉只有一些有限的圈子可能会听进去,”他说,“然后效果很快就会消失。”事实并非如此。斯诺触及了一处文化断层,至今仍在产生影响。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在2018年的作品《当下的启蒙》中写道,“斯诺的论点似乎有先见之明。对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的蔑视,在精英知识和艺术文化中有着悠久的传统。”

是的,在过去的文化中,对科学的蔑视常常出没于晦涩的艺术沙龙中。华兹华斯在他的诗作《逆转战局》(The Tables Turned)中感叹道,“我们为解剖而谋杀。”这是真的:科学的冰冷手术刀切开人类尊严的心脏,这一形象如今仍然伴随着我们。在某些圈子里,政治风潮影响个人信仰,愚昧的人问道,“弗兰肯斯坦博士以为他是谁,创造没人知道会对我们身体带来什么影响的疫苗?”
但在如今的艺术舞台上,科学成为一种常规。小说写的是遗传学家,歌剧的主角是物理学家,而计算机科学家创作绘画作品。艺术家可以用批判的眼光看待科学,但艺术和科学,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意识状态,来自一种文化,而不是两种。
这就是斯诺一直以来的目的。在《两种文化》50周年纪念版中发表的一篇关于斯诺的生活和文化的文章中,剑桥大学思想史和英国文学教授斯蒂芬·科利尼写道,斯诺通过个人视角夸大了两种文化之间差距,这个巨大分歧源于他对科学的热爱和对文学矫饰的憎恶。

在20世纪30年代的工业化英国长大的斯诺,“认为在传统精英推动世界陷入经济萧条和另一场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科学是巨大的希望,”科里尼写道。斯诺喜欢H·G·威尔斯,因此反感那些对《世界大战》的作者不屑一顾的评论家。“年轻的斯诺对‘文学知识分子’产生了反感,特别是他认为他们抱有的势利和怀旧的社会态度,这种反感永远不会离开他,”科利尼写道。

[英]C·P·斯诺 著 纪树立 译
三联书店 1994-2
不管是什么心理因素造成了斯诺对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分裂看法,科利尼将二者视为平等的。他继续讲道,大学可以缩小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差距。课程设置应该要求在两方面都有设计,教育文化不应该把一门学科置于另一门学科之上。
“幸运的话,”斯诺写道,“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教育我们的优秀人才,让他们在艺术和科学方面都不会忽视想象力的体验……”我想我们应该慷慨地忽略斯诺用到了“优秀人才”这个词,好像“不优秀的人”就不值得接受科学和人文之间的交叉教育。20世纪50年代剑桥大学的思维方式有其局限性。
不过,“想象力的体验”是一个有趣的词,代表了科学和艺术在人类头脑中的交汇点。1970年,与毕加索一起生活了10年的画家弗朗索瓦·吉洛嫁给了小儿麻痹症疫苗的先驱乔纳斯·索尔克。当这位艺术家被问及她与这位科学家有什么共同点时,她回答说,“我们之所以般配,主要是因为尽管我们专注于不同的领域,但我们有相同的内在动力,即探索未知事物的动力。发现使人能够从未知中获得一些已知的东西。这是他所拥有的能力,也是我最爱他的地方。”
诚然,艺术家努力创造激发主观反应的作品,而科学家努力创造消除主观反应的解释。但他们的动力是由相同的事物驱动的。“科学和艺术都是创造力、想象力以及执行力的产物,”古生物学家和插图画家、史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主任柯克·约翰逊说,“你有了新的想法,测试这些想法,并执行它们。”
就像科学家一样,贝多芬提出了一个假设,可以创作一首交响乐来表达一个宏大的哲学概念:生命是一场与命运的普罗米修斯式斗争。作曲家想“传达一种凶猛的、不可避免的东西:一种自然的力量,一种无情的命运的鼓声”,扬·斯瓦福德在他2014年的传记《贝多芬传:磨难与辉煌》中写道。贝多芬对音乐段落进行了试验,借鉴了以前的一些草稿,直到基于四个简单音符的正确设计开始成形。斯瓦福德写道,创造和保持适当的张力是一项严密的工作,“这是音乐中最难做到的事情之一,必须经过数月,有时甚至数年的努力,一个一个音符写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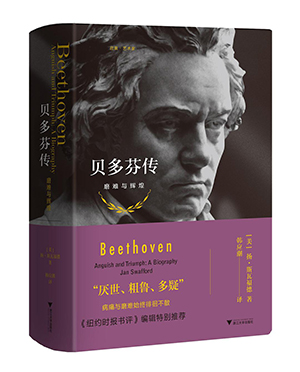
扬·斯瓦福德 著 韩应潮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 2020-2
科学界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是DNA的分子结构,是科学家们经过多年的努力,一个原子一个原子写出来的。它也有四个构成单元:A、G、T、C,即有机分子的原始结构——核苷酸。科学家们必须弄清楚DNA的结构,才能确定它是如何运作的,是如何塑造生物体的特征并将它们传给后代的。科学家们像贝多芬一样痴迷于他们的追求,但不是写交响乐。他们不允许出现没有物理学和生物学规律支持的解释。
DNA科学家中最一丝不苟的当属罗莎琳·富兰克林。她是X射线晶体学的大师,X射线晶体学是一种识别定义分子的原子的方法。在帮助确定了DNA的双螺旋形状后,富兰克林分析了病毒。在《小说的艺术》中,亨利·詹姆斯建议作家们“努力成为那种不会忽视任何事物的人之一”。这就是富兰克林。在1975年的传记《罗莎琳·富兰克林和DNA》(Rosalind Franklin and DNA)中,安妮·赛尔引用了富兰克林的同事之一阿龙·克卢格的话。“她注意到了一切,”克卢格说,“她制作了最好的标本……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因为简单的机械技能。这是一门艺术,做这件事关乎她遭受了多少痛苦,关乎她投入了多少耐心,关乎她对事情的记录,关乎她的重点。科学发现就是这样产生的。”
斯诺提到的鸿沟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感觉。历史已经传递了这样的感觉,即科学的冷酷理性和艺术的混乱激情并不相称。柏拉图告诉我们,苏格拉底想把诗人和讲故事的人赶出城市,因为他们胆敢吹嘘邪恶的人可以获得幸福,这并不是塑造严肃共和国的道德美德的方法。邪恶的激情必须被埋葬,古希腊哲学家的法令成为福音,二元对立就这样诞生了。
在17世纪,笛卡尔告诉世界“我思故我在”,知识的堡垒因人类多变的感情而摇摇欲坠。但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凿开了二元对立的基石。到了20世纪,像安东尼奥·达马西奥这样的神经科学家,通过生物实验表明笛卡尔是错误的。知识和理性不能与我们的感觉分开,大脑活动不可避免地将知识和理性与来自我们感官的输入进行混合和匹配,并始终以我们的记忆为底色。顺便说一句,笛卡尔先生,这并不意味着知识不那么扎实。“感情激发知识和理性的事实,并没有使知识和理性的真实性或有效性降低,”达马西奥说,“感情只是对行动的一种召唤。”

[美]沃尔特·艾萨克森 著 汪冰 译
中信出版社 2018-7
在讨论斯诺的文章时,有时会被忽略的是,科学家和艺术家们早就听从了同样的召唤。沃尔特·艾萨克森在他2017年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传》中写道,这位文艺复兴巨匠的科学研究,他对工程、解剖学、地质学和植物学的探索,与他的艺术、绘画和雕塑并不是独立的。“这些内容共同服务于他的激情——了解关于世界的一切,包括我们如何融入其中,”艾萨克森写道。
关于浪漫主义诗人,也可以这么说,尽管很少有人这么说。英国作家理查德·霍姆斯是柯勒律治的传记作者,此外还写作了关于浪漫主义时代科学的《好奇年代》和关于热气球历史和科学的《上穷碧落》。霍姆斯告诉我,他写这两本书的原因之一就是要回溯历史,纠正“现代的两种文化概念,即艺术和人文不能与科学对话,反之亦然”的说法。
霍姆斯解释说,浪漫主义诗人和作家,包括济慈、拜伦和雪莱夫妇——珀西·比希和玛丽——都曾深入研究科学,将天文学、进化论和物理学的最新理论囊括进他们的诗歌和小说。同样,19世纪的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化学家汉弗里·戴维和迈克尔-法拉第(他在电磁学方面的发现彻底改变了物理学和现代社会)都了解当时的诗人和音乐家,“并被他们深深吸引和启发,”霍姆斯说。

戴维是最早分离出钠和钾的人,也是电化学的先驱,他从他的朋友柯勒律治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柯勒律治是浪漫主义的黑暗核心,也是《古舟子咏》的作者。“他们就疼痛的概念进行了非常有趣的交流,”霍姆斯说,“疼痛的功能是什么,尤其是对于动物来说,疼痛有什么用?为什么会有疼痛?他们会把这个概念框定在上帝为什么要给这个体系带来痛苦上。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讨论,但它与戴维的实验息息相关。”正是戴维发现了一氧化二氮可以止痛,他写了一篇论文,建议将其作为麻醉剂使用,可悲的是,这个建议40年来都没有被采用。这是科学家与艺术家的对话,而艺术家则对他说,“从更宏大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然后把你的科学引向这个方向。”
沃尔特·默奇是现代的文艺复兴者,这位电影剪辑,《教父》三部曲、《现代启示录》和《英国病人》的音效设计师对科学史有着深入的研究。他提到了20世纪匈牙利物理学家卡罗伊·西蒙尼的一个理论:“艺术上的突破打破了土壤的板结,给它施肥,在混合物中加入堆肥,然后科学的果实就可以找到根,”默奇说,“20世纪之交带来了电影的发展,电影基本上就是动作的量化,把动作分解成动作帧。大约10年后,马克斯·普朗克出现了,给我们带来了量子理论。大约在同一时间,电影开始被剪辑和拼凑在一起,用并非按顺序拍摄的部分来讲述一个连贯的故事。所以,这两件事——量子力学和电影的发展——是共同作用的。”

西蒙尼的理论是否准确?艺术中的文化运动是否为科学突破提供了肥料?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关联,但或许仅此而已。这个理论强调了一点,是一种文化——而不是两种——同时激发了科学家和艺术家。
在采访中,科学家们无一例外地表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艺术尤其是电影都会激励他们。哥伦比亚大学天体生物学中心主任凯莱布·沙尔夫说,从批判性思维中解放出来是很重要的,他最近的著作是《信息崛起》(The Ascent of Information)。“作为一个科学家,你可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忘记你的人性,忘记作为人类的要素,这与分析能力或发明能力无关。人性中有一种要素是不受控制的,却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创造力。我喜欢体会这种创造力。”
沙夫在很小的时候就体会到了这种滋味,他在英国乡村长大,父母都是艺术史学家。“他们向我灌输了这样的概念: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来探索你周围的宇宙,研究人类与艺术的互动,”沙夫说,“但他们也告诉我,科学是探索宇宙的一种方式,我对科学的迷恋很大程度上来自人文学科的父母。”
做人就是会有偏见,沙夫说,意识到这一点是克服偏见的第一步。“如果科学家不保留人性的感觉,不保留与人类的联系,这对他们的工作是有害的。我们都是盲目的,文化和个性中的许多东西都会不可避免地给我们带来偏见,即使是最坚定、最善于分析的科学家也不能幸免。这将使他们看待自然的方式发生偏差,使他们探索问题的方式发生错位。我在科学方面的原则是保持开放的心态,总是质疑,永远不要拒绝任何可能性。”
这对艺术家来说也是很好的建议。当艺术家在科学的道路上冒险时,会发现可能从未想象过的联系——人与环境、生物体、基本粒子之间的联系。科学与艺术之和谐的最后一点,可能也是最明显的一点:没有人性的科学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广岛。当科学家与人文科学在一个共同的文化中互动时,对我们所有人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翻译:李思璟)
来源:鹦鹉螺杂志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