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常有人拿《水浒传》与英国的侠盗罗宾汉的故事相提并论,或是说《水浒传》是中国的罗宾汉,或是说罗宾汉是英国的《水浒传》。文学评论家孙述宇不这样认为。
在他看来,《水浒传》并非当代批评家燕卜荪(W. Empson)所说的“田牧文学”(pastoral)。所谓田牧文学,其特点在于以田夫牧人为题材的作品,既不是田夫牧人创作的,也不是供给田夫牧人欣赏的。人们过去认为《水浒传》是一部“田牧式”的强盗文学,是类似罗宾汉的侠盗故事,事实也是如此吗?

孙述宇在《<水浒传>的诞生:怎样的强盗书》一书开篇即分析道,《水浒传》的特色之一是好汉要钱,而侠盗故事中的好汉照理来说是不要钱的,即便要钱也是劫富济贫,不会像梁山好汉那样劫财为己用,在劫掠过程中还大量杀生甚至残暴虐杀——作者一般不会想要把丑行加诸英雄身上,但此处却如此不讳言杀掠,只因这位作者不将之视作丑行,孙述宇得出结论,作者也只可能是行为类似的强徒。
《水浒传》的另一特色便是对女性的态度,“《水浒传》的语调对女性可说是毫无敬意,但所鄙的只是她们的德行,不是她们的才智……作者非常不信任女性,他说她们很危险,很不可靠,读者老是听见男人吃了女人亏的故事……”为什么水浒传对于女性的态度如此厌恶,且反复彰显这一厌恶与排斥?为什么忠义堂上的英雄一个个都远离女性、恶待女性,如此不自然却一次次呈现同性质的事件和情景?在《<水浒传>的诞生》一书中,孙述宇专辟一章《红颜祸水》,为我们揭开了这部名著背后针对亡命观念的强人宣传艺术。
祸水
《水浒传》对女性的观感,过去并无很好的解释,因为大家都不小心察看事实与仔细分析,只笼统称之为歧视与偏见,继而便做出颇不审慎的社会学与文学的解释。社会学的解释认为这种偏见的成因,是由于中国往日的社会以男性为主,对女性并不敬重;文学的解释则以为中国文学有鄙视和憎厌妇女的传统。这两种解释实在都没有什么道理。首先,我们没有什么理由要去相信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必会自然而然地像《水浒传》那样诟骂妇女。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也一定希望自己的妇女不要捣乱破坏,希望大家同心合力使社会能维持下去,因此必定会设法导诱她们遵守秩序,所以过去中国与欧洲的社会都给予妇女相当的地位(大致上是与丈夫的社会地位相应的),并且大力褒扬她们贞节服从之德,而从来没有听见像《水浒传》这样对她们横加污蔑的。

至于中国文学,我们遍查史籍发现远溯《诗经》《楚辞》,在这广阔的源流中,除了水浒文学这小小的一支,都没有敌视妇女。我们的诗人有各种以女性喻言男子的习惯,而“逐臣”之情抒呀抒的,就变成对“弃妇”的欣赏了。把美女捧到半天高的《红楼梦》,倒是继承文学传统的,因为那种把女子美化了来赞叹的态度,在《西厢》《还魂》等名剧中都已见得到;《水浒传》敌视妇女,继承什么传统?《水浒传》以前有哪些文学作品是敌视妇女的?

还有些人半认真地把这种态度归诿于作者的个人际遇,猜想他也许吃过女人的亏(那女人想必是姓潘的了?),也许是性无能,有不正常的心理。这样去猜想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在水浒文学中,除了《水浒传》,现存的几本元代水浒杂剧,对女性也很不信任:六本剧中,有四本演淫妇勾结奸夫构陷本夫,在其余的两本里,男人也因女人而吃苦头。我们总不便说这四位或六位作者都有变态心理。依我们看,像水浒文学所表现的对于女性的猜疑,用法外强徒的亡命心态来解释最妥当。厌弃女色的倾向,在为了一己生命而焦虑的人当中是很常见的,渴望永生的僧侣修士如此,与死亡为邻的草泽萑苻亦如此。过去的强盗有“阴人不吉”的迷信,又有“劫财不劫色”的道德戒条,并不是没来由的。(当然,盗匪与士兵都会强暴妇女,但那种事情总是发生在他们的安全得到保障之后。)我们相信水浒故事是法外强徒所作,他们创作的目的,既为娱乐,也为教育。任何战斗队伍都希望成员远离妇女,因为妇女会销蚀他们的作战意志,延误行动,增加泄露机密的危险;反之,不接近妇女的队伍,作战效率高,与地方民众的关系也容易好。因此,《水浒传》对于女性不仅流露出厌恶之情,而且着意攻击。听故事的人会觉得女人危险得很,避之则吉。从前中国的社会鄙视女性,认为妇人既无见识,又无能力,又无胆量;《水浒传》倒并不这样鄙视她们,小说中的女人在心计与行事的胆量方面全是男子汉的匹敌,甚至梁山上的大英雄,只要稍不留神,就栽在她们手里。
《水浒传》中女人的故事,差不多必定讲到男人吃亏。宋江名满天下,江湖拜服,但除了吃阎婆母女的亏,又曾被刘高老婆恩将仇报而陷身缧绁。第二好汉卢俊义,差些儿让妻子贾氏害死。史进与安道全被娼妓出卖;雷横被歌女白秀英害苦。潘金莲鸩了武大,武松若德行与武功稍差,就会毁在她手里;同样,若不是石秀机警,潘巧云送杨雄一顶绿帽,还会害了他命。孙二娘是梁山的人马,但手上也不知沾了多少英雄好汉的血:武松没有吃亏,只是由于他天生神勇,而且谨慎得出奇;鲁智深捡回一条命,是因为张青及时回到家里。甚至林冲,一身本事,娶到的妻子又贤良,却也因她而弄得流离失所,三番几次差点儿送了命。作者很努力制造“女人祸水”的印象,防闲女性的动机清楚得很。

新的英雄
郑振铎曾说:“中国英雄是妇女憎厌者。”这句话说得不够小心了,我们分析过,在中国文学广阔的领域内,除了以《水浒传》为首那些由强人创作传讲的少数作品,并没有憎恶妇女的突出表现。在水浒故事出现之前,中国也不闻有英雄不好色之说。换言之,强人宣传家并没有继承一个憎恨妇女的传统,而是在努力创造出一种防闲女性的态度来。
照理这工作会遇上不少困难。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当一些身强力壮的青年汉子不再冻馁之时,只要危险不在眼前,叫他们禁制性欲恐怕不容易。“英雄”不同“圣贤”,要做“圣贤”,当然得要打算有所不为;反之,“英雄”之所以引人艳羡,正在于他可以满足各种恣纵的欲望,可以满足他的自我,倘若要禁戒女色,那就少了很多满足了。历来美色都是大丈夫的一项重要报酬,皇帝有三宫六院,达官贵人有姬妾,历史上的名人有名女人为伴,汉高祖有他的戚夫人,项羽有他的虞姬,孙策有大乔,周瑜有小乔。就在这些三十六人故事开始流传之际,韩世忠截击金人于黄天荡,在战船上把鼓敲得咚咚响的便是他的夫人梁红玉,她原是京口的名妓。这时说英雄不要美人,大家就肯相信?
可是宣传家接受了任务,就一往无前地编造故事,描绘出一个新的英雄世界来。在这个新世界里,做英雄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不好色”。不能作战取胜,或者不讲义气固然不是英雄;若是“贪女色”,也“不是好汉的勾当”(宋江评王英之语,在第三十二回,第504页)。忠义堂上的好汉十九都够得上这个条件。为首的天王晁盖,除了“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又“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第200页)。这样理想的亡命汉子,难怪弟兄们都尊他为老大哥。晁盖下面的宋江,依照小说的解释,也是个不好女色的人。再下来,卢俊义虽有妻子,但那个贾氏出墙,正因为卢先锋只爱枪棒,于女色上头并不着紧。公孙胜是个干干净净的道士,持戒谨严,否则法力不会那么好;吴用心计最多,不过只用在亡命行动上,从不向情色那边动念头。再下来是那一大群狮虎貔貅,个个都有一身坟起的筋肉和水牛大小的力气,然而他们要纵欲,也只限于大吃大喝而已。武松初到哥哥家中,嫂子潘金莲一见便动了情,心想“大虫也吃他打了,必然好气力”:这愚昧的女人不知道大英雄的气力是只用来打老虎和杀人的。武松和李逵这些莽汉似乎对男女之事特别厌恶,不仅自己不屑为之,甚至在山间野外路见苟且之行,也会疾恶如仇,把“狗男女”拿来开刀。李逵那回跟随戴宗去取公孙胜来破高廉,得罪了罗真人,戴宗为他求情,对罗真人说,这个铁牛虽卤,但也有好处,其一便是“并无淫欲邪心”。的确如此,这个黑旋风虽然凶猛异常,但在性生理方面却像个尚未发育的小孩。别的好汉也差不多。
宣传家还收拾了不少前人的“后遗”。宋江三十六人的故事一开头在各处传讲,内中有些并不那么洁净,现在宣传家想要加一种清教徒精神于其上,便须把那些不洁故事处理一下。比方那位“风月丛中第一名”的浪子燕青,从前一定有比较香艳的故事吧?宣传家大刀阔斧把它们删去了,现在在书中只见他品行端方,连倾国倾城的李师师也勾引不来。宋江与妇人姘居之事,于他的英雄首领形象有损,本应删掉才是,但大概阎婆惜的故事传得太广了,谁来讲宋江都不能不提这一笔,宣传家于是修改故事的细节来替宋江洗脱。我们今天读《水浒传》,看见宋江原来并不好色,他与婆惜发生关系,皆因他乐善好施,看见婆惜父亲阎公客死他乡,怜而舍给一具棺材,而那寡妇阎婆一方面是感激,一方面又冀望得到赡养,便硬把女儿给了他。这故事在《宣和遗事》里不是这样的。《遗事》并无阎家受宋江厚恩之说,只谓阎婆惜是个娼妓,宋江当然就是个嫖客,后来婆惜“与吴伟(相当于《水浒传》中的张文远)打暖”,原因恐亦不外是“鸨儿爱钞”或“姐儿爱俏”。而宋江吃醋得很厉害,“一条岔气,怒发冲冠,将起一柄刀”,把两人一起杀了(《遗事》元集末尾)。再如今本《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是没有破色戒的,他的“花和尚”绰号中的“花”字据说是来自身上的花绣,而非因为他“采花”;但宋时龚开在《宋江三十六赞》中说他“酒色财气,更要杀人”,表示他没有守这条戒。

爱美是人的天性,人会自自然然地把美的东西视为好的东西。在儿童故事里,善良的仙子长得美,邪恶的巫婆长得丑。水浒故事所要灌输的“红颜祸水”和“英雄不好色”,都是不自然的观念。我们的宣传家对此一定很了解,很知道事不易为,于是他们加倍用力。他们拿出很有效的宣传方法,一而再、再而三讲述同性质的事件。他们的语气始终是据事直陈而且斩钉截铁的,从不说些求谅解的话,从不容许怀疑故事的真实性。事实上,他们不让人家用比较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强迫人家用他们的标准。小说讲道,英雄就是这样的,李逵没有欲心,鲁智深不近妇女,武松不怕色诱。“英雄不好色”的命题不但出现在叙事的层次,而且成为理由与前提,是创作故事的材料。林冲之上梁山,起自他不爱与女人作伴,他自己跑去欣赏鲁智深耍禅杖,欣赏得高兴时便与那花和尚在菜园里结拜起来,一直丢下妻子不顾,由她独自在庙里进香,所以高衙内才有机会去调戏。杨雄与卢俊义上山,都是被不贞妻子迫成,而妻子出墙,却又正是由于这两条好汉只爱武艺而不爱女色。宋江姘居之事也关联着不好色来叙述:宋江杀惜是由于婆惜别恋而威胁他,婆惜别恋则又是宋江不近妇女的结果。这些故事前后相接,滔滔不绝,把任何抗议的声音都淹没掉。讲者在“丐词”吗?当然是的,那正是宣传的要诀。据说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有一句名言“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那真是一语道破《水浒传》宣传的三昧。
听众怎样接受这些故事呢?一般来说,非常地好。我们看见名学者郑振铎真以为“中国英雄是妇女憎厌者”,可知宣传成功了。几百年来,没有什么人疑心《水浒传》与亡命汉的教育工作有关。这里头有个原因:从前人听英雄故事,比我们今天要老实得多。他们用一种虔敬之心去听,不会随便啰唆打岔。我们今天动不动就嫌故事不真实,而所谓“不真实”有时是指违反科学定律,有时却只是说不常见或者不正常,换言之,是不合我们常人的尺度。从前的人不会这样来反对的,他们会觉得英雄当然超逾我们常人的尺度,否则还算什么英雄呢?英雄故事里的事,不必是听众见过的。谁曾见过山中杀虎与长堤斩蛟?谁见过倒拔垂杨柳?但几百年来水浒听众都像鲁智深身旁那群泼皮一样,敬佩得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花和尚把一株大杨树——树大得上头的乌鸦巢须用梯子才能除去——连根拔起。现在水浒宣传家要求听众再去相信英雄有逾常的精神力量,能守常人难守的道德,听众当然也可以相信。如果武松在景阳冈酒店中喝下数倍常人之量的烈酒“透瓶香”可信,如果他在冈上赤手捶死一只吊睛白额虎可信,难道他抵挡住潘金莲和孙二娘的诱惑就不可信?水浒听众不会觉得这种要求过分的。他们听这些新英雄故事时,还得到道德感的额外满足。

为亡命行动服务的艺术
不好色的大英雄与貌寝的贤良妇女都是勉强创造出来的观念,亡命宣传家只是不得已而为之。自然的观念,我们说过了,是以为英雄应当与美人匹配,并以为美貌妇人比丑陋妇人贤良。北宋时大文豪苏轼在赤壁怀古,“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这种感觉倒是非常自然:周瑜的雄风英气由美人小乔——在“初嫁了”的时候——衬托出来。但是这位顾曲周郎不是听水浒故事那种亡命汉子。他是个贵族,有学问与见识,能够组织与指挥,还有家财和社会关系可动用,换言之,有做事业的各种条件。他是个领导人,稍微纵欲还可以。项羽与虞姬的情形亦差不多:虞姬是项羽做了一番事业后得到的报酬,是他英雄形象的采饰,不是帮助他挣扎做事的伴侣。水浒故事中的新英雄,是宣传家给未曾成功的亡命徒众做榜样的。这些徒众也许是南宋初年那些称为“忠义人”的华北民军,但更可能是这些人蜕变了的后继者,他们也许对赵宋皇朝的感情已经渐渐淡忘,只是受不了金人或元人的压迫而啸聚山林,在很艰难的情况下奋斗求存。他们没有智识与经验,两手空空,除掉一身气力和一股决心,可说是一无所有,他们须把一切都投进斗争之中,才有成功之望。宣传家对这些人说,最好是不要娶亲,否则也要娶个“虎狼妻”,娶个粗粗丑丑、能干活、敢犯法、肯杀人的女同志。
现代的革命家常常说“一切为了革命”,水浒宣传家的格言是“一切为了亡命行动”。男子汉为了亡命行动,彻底地便牺牲家庭;即使不那么彻底,也须准备抛弃男女之乐,不求女性温柔体贴的慰藉。妇女为了亡命行动,或是要牺牲名誉,背负淫荡寡德种种恶名;或是牺牲性别,像顾大嫂那条母大虫那样,变成与男子无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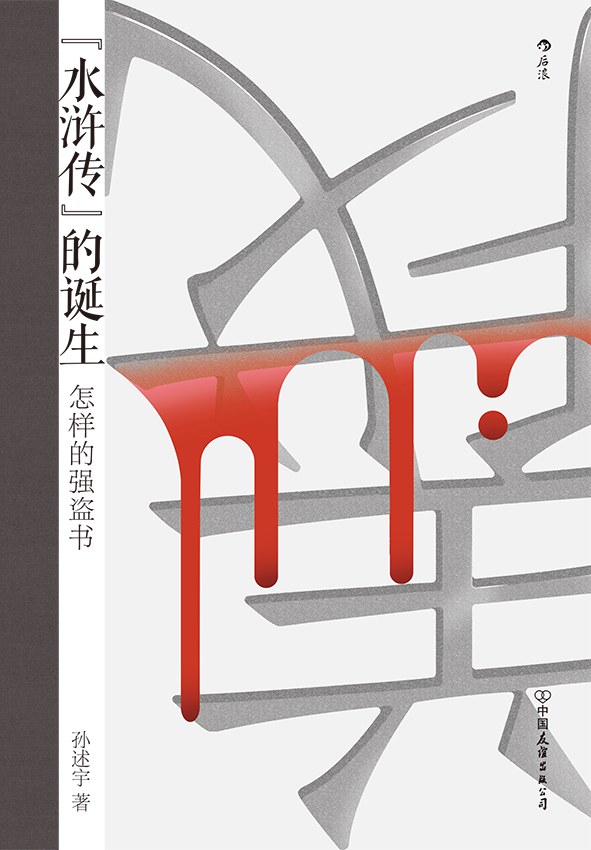
孙述宇 著
后浪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21-11
编造故事的宣传家自己也牺牲,牺牲的是他们的艺术。也许比较少人注意到这一点,因为大家以为通俗小说的水准不外如是,《水浒传》已经比别的作品高了;但依我们分析,水浒故事的作者中有很有才能的,而且还是在有意识地运用艺术手段,这些故事没有能够写得更好些,实在可惜得很。在现在的小说里,好汉们被刻画得很肤浅,他们有气力和武艺,很勇敢,很够朋友,但此外便没有多少人性内容了。他们结义结得很急,讲究同志之爱,于是抛掉了家庭伦理;他们很少反省,从不后悔,连恐惧与顾虑都几乎不会——所以出一个会恐惧会顾虑的林冲,便显得很不正常,很奇怪似的。林冲常常心存疑惧,那是由于他的故事着重写迫害。(他若是武松那样的铁汉便无从受迫害。)梁山上一群彪形大汉,个个力大如牛,然而在性生理与性心理上却是未曾发育过的。小说中的妇女也令人惋惜,她们的人性与女性从没有比较完整的描写。我们在本文一开头就分析过,作者原是很会写女性的。清初的金圣叹曾叫读者注意潘金莲怎样一声一声叫着“叔叔”,那的确是很动人心魄的呼唤,潘金莲会这样呼唤,表示作者深知男子汉心里有怎样的寂寞,这种寂寞又是如何地除却经过两性关系便难以消除。但是作者只写到此,不再写下去。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孙述宇《<水浒传>的诞生:怎样的强盗书》一书,较原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自拟,注释从略,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