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煽情、甜味剂、多愁善感,这是一组可以互相转喻的意象,它们的相似之处在于人们通常容易沉溺其中又羞于承认,可是为什么如此呢?美国作家莱斯莉·贾米森(Leslie Jamison)在一篇散文中回应了这个问题。莱斯莉·贾米森一位美国作家,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并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非虚构写作班。她的非虚构作品《十一种心碎》(The Empathy Exams)于2014年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在《为糖精辩护》这篇文章中,她将煽情(Saccharine)与糖精(Saccharin)并置,阐释我们为何警惕糖精式的多愁善感,将这种感受像甜蜜而令人上瘾的小蛋糕一般藏在壁橱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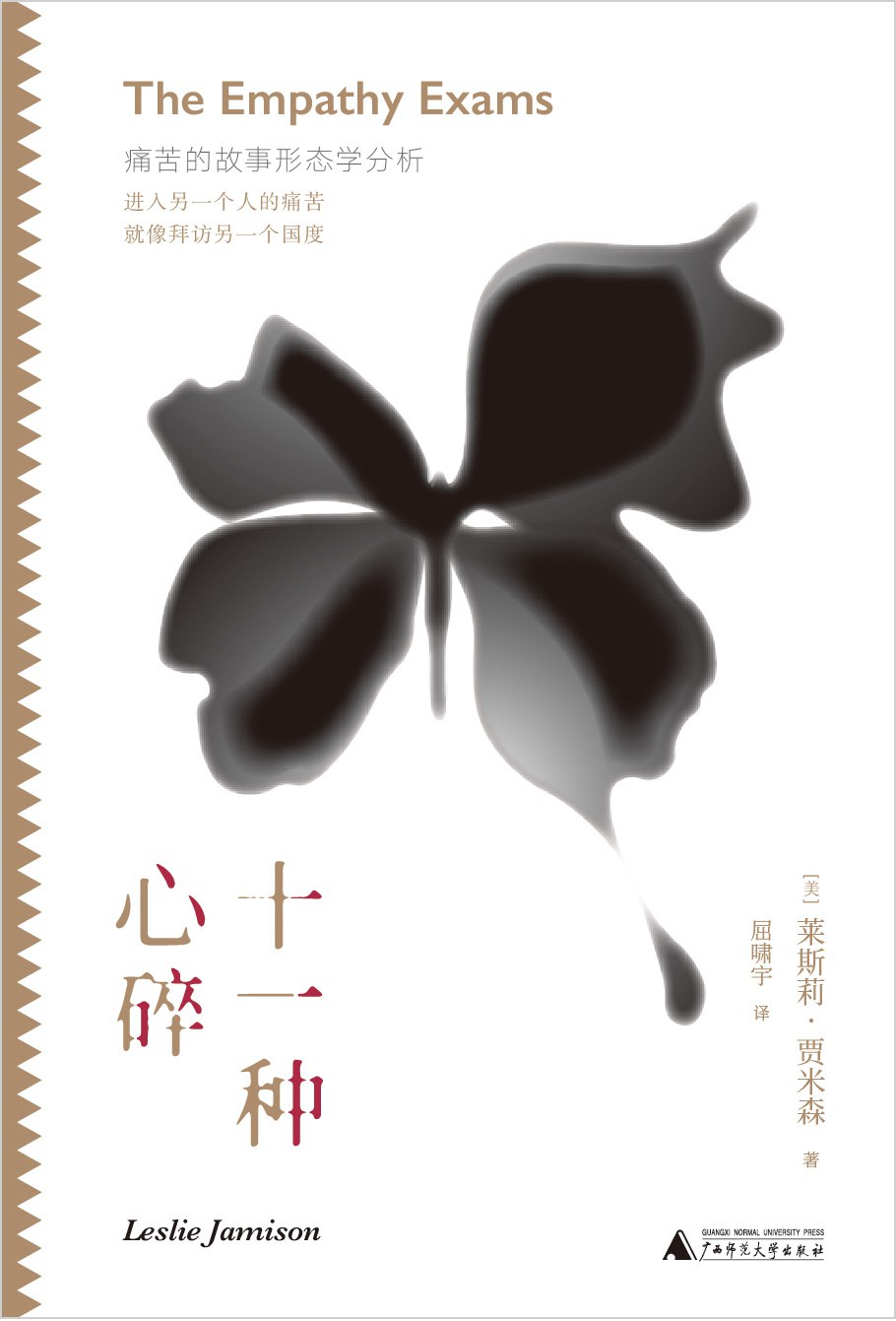
[美]莱斯莉·贾米森 著 屈啸宇 译
广西师范大学·上海贝贝特 2021年6月
多愁善感在文学史上的名声显然不佳。《包法利夫人》就是一部以多愁善感反甜腻纵欲的小说,贾米森说,她从十六岁起就痛恨这部小说,而现在却爱上了它,因为她乐于分析书中的痴妄欲求,并将艾玛的情感世界从人物身上剥离,投射到自己身上,就像艾玛对爱情小说所做的那样。作家王尔德曾点出沉溺的实质,称“一个多愁善感者只是想在情感上来一场不需要买单的奢侈享受”。不需要买单的享受令贾米森联想到人造甜味剂,这种替代物比蔗糖还甜,然而食用者却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仿佛一场作弊。
美学家认为煽情会误导情感体验,使我们对肤浅而夸张的内容投入过多情感,这也被华莱士·史蒂文斯称为“情感的失败”。而道德批判者认为煽情会导致情感过激,偏离明确合理的道德准则,情绪化的人会有用情绪替换责任的危险,书中举出的例子是纳粹军官也会被集中营囚犯上演的歌剧而感动流泪——这并不是一种讽刺,而是逃避情绪压力的方式。但问题是,多愁善感真的一无可取吗?反对多愁善感是否又会导致另一种自我膨胀?本文选自广西师范大学·贝贝特引进的莱斯莉·贾米森《十一种心碎》,经出版社授权刊载,小标题为自拟,选文有删节。
甜味剂就像煽情作品
替代性正是我们鄙视甜味剂的原因之一,实际上,我们食用这种物质时并没有付出代价,却满足了自己的味觉。我们身上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特别热衷于设立一系列规矩来进行自我约束,比方说,应该给自己每天的懒惰或勤勉程度打分,而对我们的身体,这些条条框框的规定尤其严苛。但在人造甜味剂面前,这种自我约束受到了严重威胁。我们从此可以靠甜味剂来作弊,一边放纵身体,一边却可以混个好分数。这就如煽情风格的作品一样,它一方面能让我们无须纠结于思考,一方面允许我们尽情地宣泄情感,就像王尔德说的,“情感上来一场不需要买单的奢侈享受”。相比之下,我们的审美自有其经济逻辑,应该推崇霍雷肖·阿尔杰的以白手起家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你需要努力从艺术作品中掘取感人之处,仅仅通过煽情风格的作品来获得廉价感动是不可取的。

但到底怎么去掘取所谓的“感动”才是正确的呢?我们要先解析作品中的具体意象,细读出文学隐喻中的修辞内涵,分辨角色之间的细微差别,将相关概念置于文学史、社会史、制度史、世界史乃至所有我们能想到的历史体系中加以理解。我们需要按照特定的流程去感受作品。我们想让蛋糕抗拒被我们轻易地吃掉,但还是会把它吃下肚去。
我们总是鄙视那些唾手可得的东西,哪怕自己在实质上是如此贪婪。对有些女人而言,若真有所谓天堂,那它应该是一个所有食物都不含卡路里的世界。弗兰克·比达尔的诗作《艾莲·韦斯特》以一段厌食症女子的自白开篇:“天堂,我会死在整床香草冰淇淋上。”这个女人将获得自由,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自由,不会因此变胖,不会变丑,因为她就要死了。现在,我们活着就能进入这样的天堂:因为甜味剂,它从口腹之恶中解救了我们。

比喻常常将我们引向煽情,我们总能从那些万变不离其宗的说辞中寻找到泪点(“像蜜糖一样的嗓音”“白瓷一样的皮肤”“泪如泉涌”),但是,它也可以让我们逃离某种获得情感的程序。比喻就像一个个小小的救世主、埃兹拉·庞德的小小信徒,动动小手指就可以从多愁善感中把我们解救出来,只要说“来点新鲜的!来点新鲜的!”就行了。假如语言具有恰到好处的新鲜感,那么情感自然不会觉得贫乏,而如果语言在晦涩的程度上也那么恰到好处,你自然不会觉得浮夸。通过隐喻,我们能够把情绪直接转换为一系列充满惊喜、令人赞叹的语言表达,同时隐喻也会帮助我们转换与扩散神圣的启示。史蒂文斯描述过这种遮遮掩掩的感觉:“隐喻的力量将一切缩水,无论是重要时分的沉重,还是关于活着的大白话。”
当我们把自己隐藏在隐喻之中,我们在逃离什么?在正午的阳光下,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如此害怕?昆德拉认为:“媚俗会让我们因为自己而哭泣,因为我们的思想和感觉中的陈词滥调的东西哭泣。”我觉得我们之所以会把情感的复杂之处与隐喻修辞联系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我们想隐藏自己的庸常,那种包裹着我们的生活和语言的庸常。我们怀疑如果选择把一切直接讲出来,如果把自己多愁善感的那一面表达得过于直白露骨,那么到最后,我们会发现自己除了平庸之外,身无长物。
20世纪80年代阿斯巴甜刚上市的时候,西尔列制药公司就意识到需要为这种产品设计一个图标,让它看起来既新潮又不失亲和力。他们认为这个图标应由基础的形状、表面化的内涵、舒服的颜色构成。这么一来,他们想要的形象就与史蒂文斯所主张的隐喻观念完全相反。西尔列公司想让这图标既能够体现产品作为“重大发现”的一面,又可以回避其中暧昧不清的部分。
西尔列雇了两个自称10年没吃过蔗糖的人,这两个人的工作就是要谨慎地找到一个合适的形象,它不能非常甜腻,不能是从关于蔗糖的陈词滥调中拼凑出来的。《纽约客》引用了其中一个人的访谈,看得出他有多么为难:
我们要和广告公司的一些人见面讨论产品的形象,其中有人会说:“要不然用心形怎么样?心形看起来又友好又甜蜜……” 但他们谈来谈去,说的东西实际上也就是一切煽情的陈词滥调。
哪怕在这种场合,哪怕是在创造它的人那里,糖精也需要否认自己所承载的意义,需要防止自己看起来太像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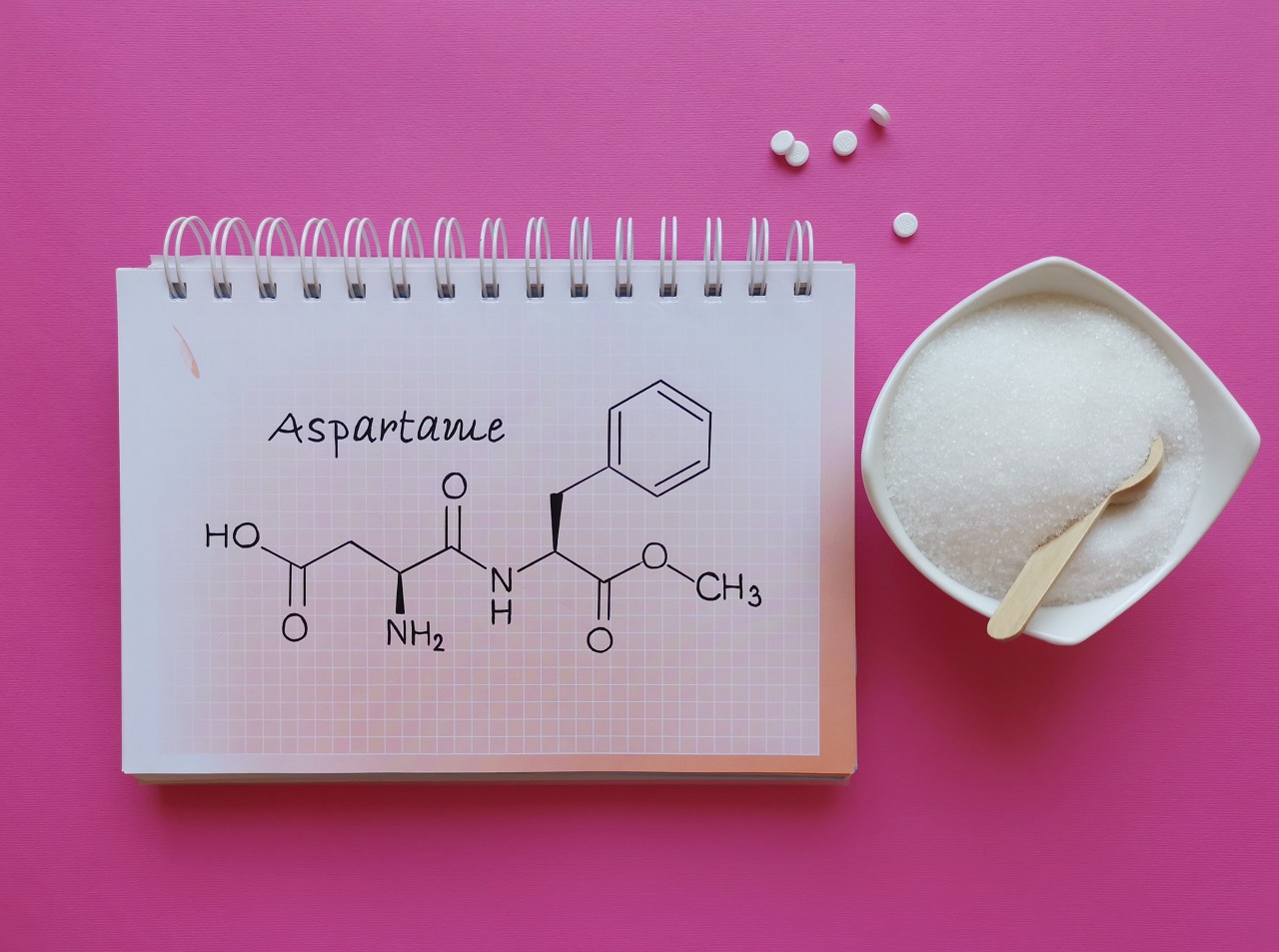
反多愁善感难道不是另一个方向上的自我膨胀吗?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应该避免陷入多愁善感之中的?可连世界末日都是以一段煽情文字作为开篇的。看看《启示录》吧,圣约翰写下它是为了警示人们世界末日的到来。在《启示录》里,圣约翰被告知:“你将口中灌蜜。”他被告知:“你将腹中苦涩。”
我害怕过度感性,但进而又害怕自己会陷入对过度感性的恐惧。恐惧和对恐惧的恐惧要求我先建立好一个可憎的预设。在某种程度上,我曾经成功地把煽情上的失败和拒斥煽情的失败这两者编织进了同一个故事里,这就形成了一条夸张的悲剧链,这样,我的每一位读者感受到的只有麻木。
那么,什么是真实的痛苦,什么又是煽情催泪呢?这两者的界限何在已经成了一个可以去机械化理解的问题:如果隐喻理解起来过于简单,叙事过于模式化,煽情倾向就会一路高扬,直到超过抒情表达的可控极限,而语言风格本身也会因情感过于外露而令人腻烦,不再有创新,情感表达也会因此变得廉价。多愁善感这个词说明在某一个时刻,人们的感性自我会完全被单纯的情绪充满、支配。“媚俗能够按部就班地迅速导致两次哭泣,”米兰·昆德拉写道,“第一道眼泪说:看着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这多么美好啊!第二道眼泪则说:当我看着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我就和全人类一起被感动了,这多么美好啊!”
这种荒谬的结论就像小孩过家家一样自然而且真实。这种印象如此强烈,引诱我们从此沉醉于自我欣赏。我们的眼泪就这样成了一种自我标榜,标榜着自己能够拥有如此热烈的情感。

但是,所谓的反多愁善感难道不是另一个方向上的自我膨胀吗?我们抵抗着自己的多愁善感,把自己塑造成真正的“洞察者”,塑造成能够准确判断何为无谓纠结、何为真实情感的仲裁者。这种反煽情的姿态实际上只是另一种自我标榜的模式而已,只是用批判代替眼泪、拼命论证自己看穿了一切而已,其实我们只不过放弃了对他人的同情,转而武断地证明自己拥有洞察力。这只是一种通过否定得来的自我褒扬,一种双重否定之下的自我安慰。
昆德拉说,这种预先设定的双重眼泪,在美学上完全无可救药, 即使如此,在其他方面它真就毫无价值吗?如何解释人们从恶俗的爱情故事和悲情电影里获得的愉悦?肆意的情感宣泄真就一无是处吗?如果它真的带来了愉悦,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尊重它?如果不尊重, 那么我们岂不是在一边为虚伪的自我辩护,一边指责他人的虚伪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好的作品应该呈现更优良的情感,应该更加广阔、更加丰富,而且更具道德感,这真的是我们一直坚持的观点吗?
即使是哗众取宠之作,也一样能让一些人跨越自己和他人生活之间的那道鸿沟。一档有关成瘾症患者的恶俗电视节目,也能让某个人感受到成瘾症患者的痛苦,哪怕成瘾症本身远没有那些节目渲染的那么耸人听闻,哪怕这样的节目里充满了各种脸谱化的典型桥段,哪怕它所讲述的情节既老套又扭曲事实,哪怕被这种情节操控情绪是一件如此可耻的事情。恶俗电影、恶俗文章、脱口而出的陈词滥调同样能让我们感受到别人的世界。尽管这些东西总会让我内心中的一部分感到恶心,但同时,另一部分在为它们的存在庆幸、欢呼。
是的,我也抗拒煽情之中的某些东西,我同样害怕其中的轻浮,害怕它的言之无物,但我更害怕拒绝煽情之后,我们会变成的样子:没精打采、冷嘲热讽、冰冷无情。我对这两极的塞壬的召唤都没有免疫力。
我希望我们都能感受煽情带来的自我膨胀,为它所伤,被它的平庸背叛,被它的局限伤害。这其实是一条能够抵达史蒂文斯所谓“重要时分”的道路。我们一头扎进情感的奇观之中 —放纵自己投身于 这种“简单化”之中,而这会让我们感受到沉重与麻木,最终冲破这 一切,等来雨过天晴。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十一种心碎》,经出版社授权刊载,小标题为自拟,选文有删节。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