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斯布福德出生于1964年,是一位天赋异禀、富有冒险精神、风格多变的作家。他从非虚构作品写起,包括2012年的作品《不道歉》(Unapologetic)。2016年《金山》(Golden Hill)出版,背景是18世纪的纽约,这是一部出色的小说处女作,赢得了科斯塔小说处女作奖。他的第二部小说《光之永恒》(Light Perpetual)入围了布克奖长名单,这是一部大胆的小说,想象了德国V2火箭弹落在伦敦南部时,如果那些死去的人没有死,他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
《光之永恒》的出发点是怎么样的?
弗朗西斯·斯布福德:在过去的14年里,我每周三都会步行到金史密斯学院(他在这里教授写作),新十字路拐角处的“冰岛”超市有一个小小的圆形纪念牌。我从来没有理由去看它,它只不过是伦敦南部景观的一部分。纪念牌上写着,1944年11月的一个中午,有168人在这里遇难。当时有一枚V2炸弹炸毁了伍尔沃斯。一开始我对这个故事十分着迷,后来开始思考城市曾经拥有、之后失去的非凡事物。我想找到一种方式来纪念这一事件,这种纪念是忠实的,但不是文学的,所以我得编造出伦敦的一个区,并在其中投掷我自己的V2,而不是践踏任何人的真正悲痛。
作为小说家,你在多大程度上扮演上帝?
弗朗西斯·斯布福德:小说家无所不能的想法是完全不实际的——哪怕是最自大的小说家,他们能想出的最好办法也无非是现实的廉价替代品。我想提出一个足够脱离人类正常生活的观点,让我们以一种通常不会考虑的方式及时审视我们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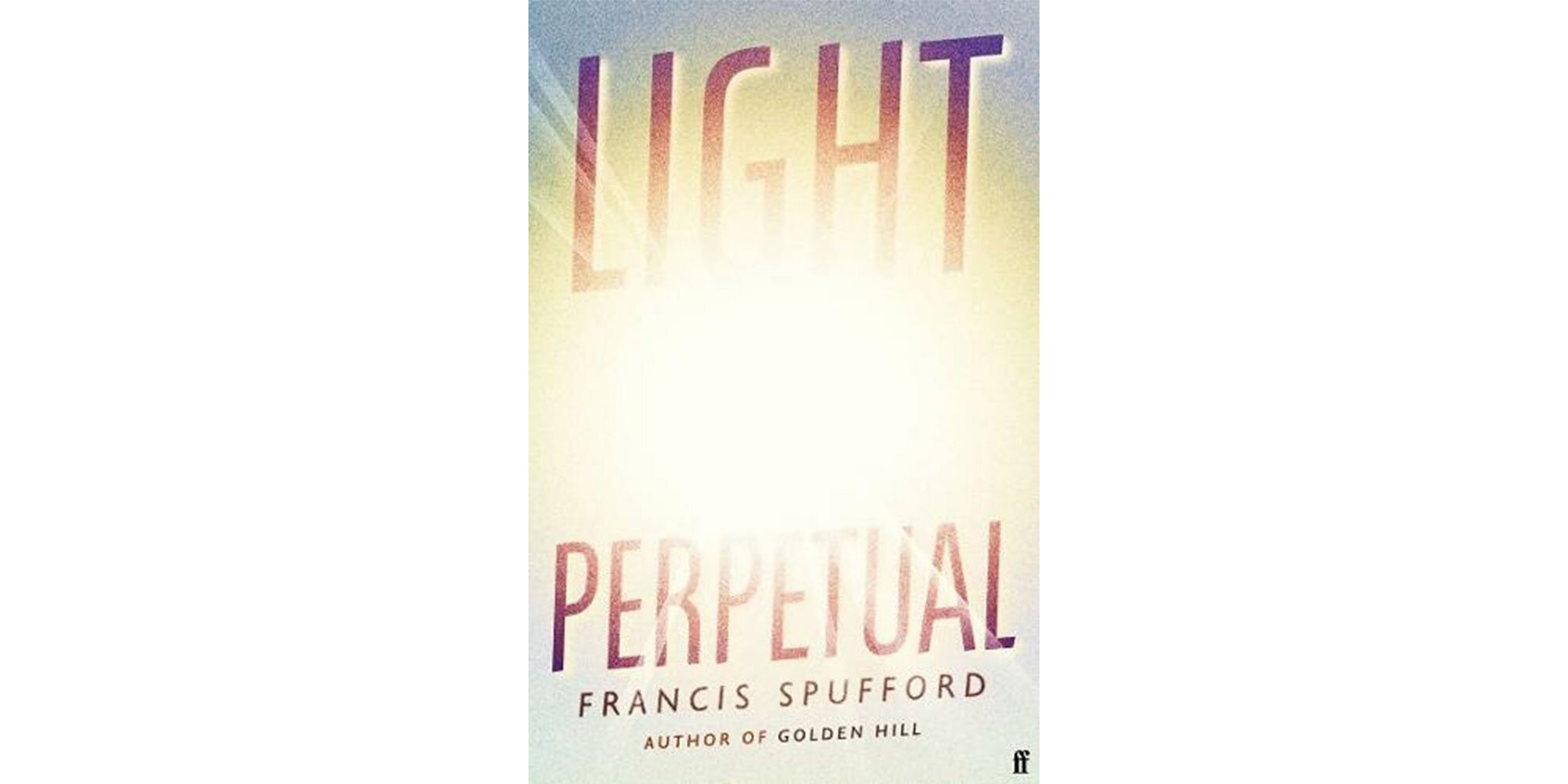
你的阅读量如此惊人,你小时候是什么样的?

弗朗西斯·斯布福德:我小时候很孤独,留着蘑菇头,穿着高领polo衫。我与成年人相处更容易——他们喜欢我的早熟以及我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词汇量——而不喜欢与同龄孩子相处。我的早熟不是情感上的,而是语言上的,因为我会用复杂的方式来表达简单的事情。我几乎总是在担心我妹妹的重病,她会在20岁出头的时候死于这种病,这让我对眼前的事情不敢有太多太直接的感受。我在书中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肯定有一些是为了逃避。我的确对阅读有强迫症,但这并没有让我想成为一个作家。我阅读是为了逃避,而不想做任何提供逃避的艰苦工作。我长大后想做一名校对,实际上我在查托和温都斯出版社担任过校对(1987-1990),这对我来说很有教育意义。
什么样的教育意义?
弗朗西斯·斯布福德:卡门·卡里尔(查托和温都斯出版社的主编)是著名的女权主义者,但奇怪的是,查托出版社也是最后一家典型的英国出版社。它坐落于一栋乔治亚风格的房子里,到处是破旧的大家具。他们让我在阁楼上用一台巨大的手动打字机阅读和写报告。这现在说起来感觉很老式,但我当时感觉非常现代。
你在1989年开始写作,那一年你妹妹去世了。
弗朗西斯·斯布福德: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旧的悲伤达到尽头,变成了悲痛,这与更自由地开始写作之间一定有一些联系。但准备开始写作也有它自己的独立时间表,写作是要变得不再被完美主义麻痹。我花了很长时间决定我想成为一名作家。之后,我觉得自称为作家或者小说家,都是一种自夸。但当我看到我的作品后,我逐渐接受了这个身份。
你的妻子杰西卡·马丁以前是剑桥大学的学者,现在是伊利大教堂的法政牧师。你现在还是教区的非专业代表吗?
弗朗西斯·斯布福德:我不再是总主教代表了,因为我真的很不擅长这个。我是一个善于说话的作家,并不代表我胜任教会政治家的角色。
不过,在读《不道歉》时,我一直在想。“天啊,弗朗西斯,你必须登上讲道坛。”
弗朗西斯·斯布福德:不!我有作为普通人的自由,我不需要为某个机构说话。我曾应邀讲过零星的布道,发现这让我非常紧张。做一些虔诚的奉献不是我擅长的事,而我的妻子在这方面非常非常擅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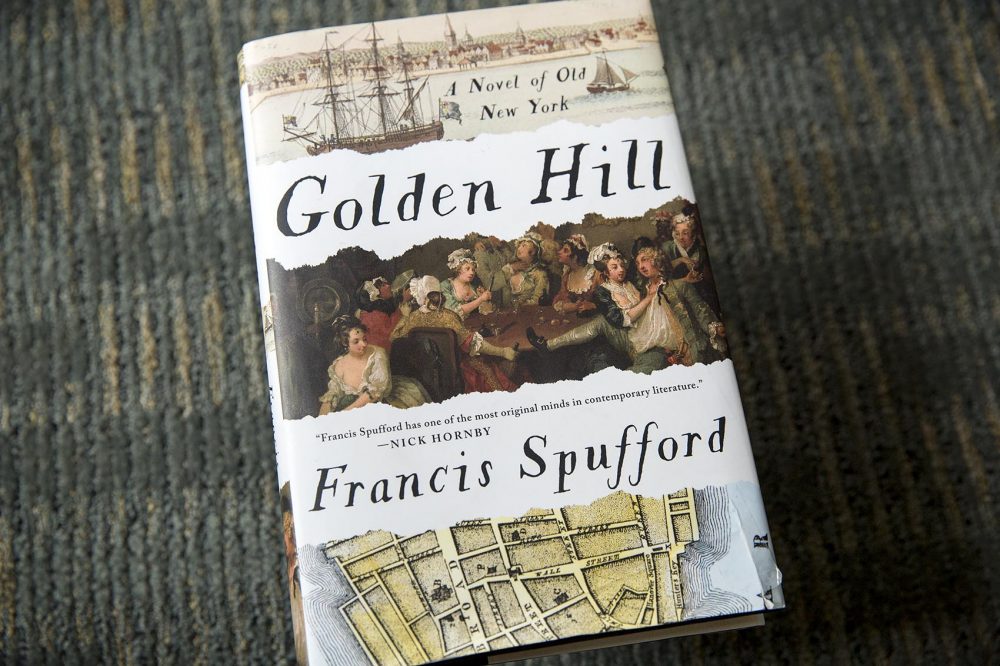
你在实践《光之永恒》所宣扬的“在生活中考虑到死亡”方面,算得上成功吗?
弗朗西斯·斯布福德:当死亡离你很远的时候,死亡更容易被接受。我在半夜时偶尔会感觉死亡扼住我的喉咙,而当早晨来临时,我会深深地感到高兴。我不是不害怕死亡,也并非不接受活着的一切是多么短暂。
在《不道歉》中,我对你说的“内疚是一种必要的情感”的说法很感兴趣。
弗朗西斯·斯布福德:文化要求我们消除负罪感,但这对自己并不友善,因为这迫使我们在不可能完美的自我形象和黑暗、绝望的自我形象之间陷入不稳定的动荡中。这就好像我们不断地被自己的新缺陷吓一跳,而我们却应该接受,我们是无可救药地容易犯错的人,接受我们的意图并不总是好的。我没有那么好,而且我可以更容易地接受这一点。
你有一个16岁的女儿。你对这个星球的未来有多担心?
弗朗西斯·斯布福德:非常担心。我很晚才成为父亲,之前做继父的时间更长。在成为父亲后不久,读了科马克·麦卡锡的《长路》——一个带有恐怖色彩的对父母情感的寓言:担心把你的孩子留在不安全的地方。这就是21世纪地球的状况。
你的床头柜上有什么书?
弗朗西斯·斯布福德:我会算上那些放在地板上的书……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第一部小说《远航》,阅读这本书是很奇怪的经历,因为我不知道达洛维夫人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我正在重读托马斯·品钦的《性本恶》,还有其他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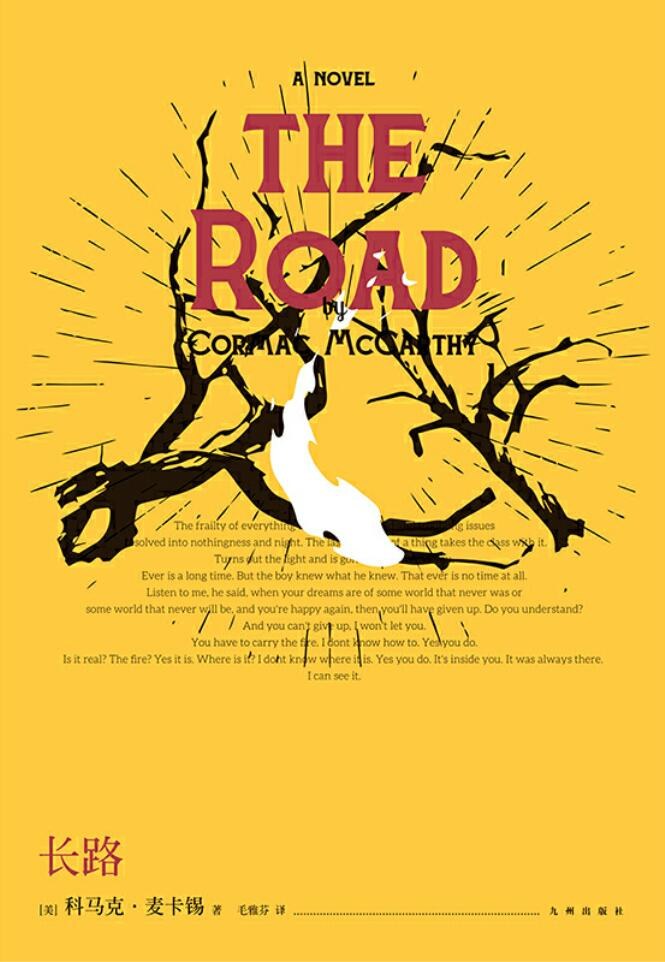
[美]科马克·麦卡锡 著 毛雅芬 译
九州出版社|理想国 2018-11
你最近读的一本好书是什么?
弗朗西斯·斯布福德:莎拉·霍尔(Sarah Hall)的《波恩寇特》(Burntcoat)是一本关于疫情时代的惊世之作。这是一本关于病毒(不是新冠)的小说,篇幅并不长,讲述了和一个不太了解的男人躲在一起的艺术家。
你对没有读过哪本经典小说感到最羞愧?
弗朗西斯·斯布福德:我只为读过托马斯·哈代的小说《还乡》感到羞愧……我知道他的作品相当不错。
人们在你的书架上看到什么书可能会感到惊讶?
弗朗西斯·斯布福德:丹尼尔·亚伯拉罕的《四季城邦》——四部奇幻小说,《光之永恒》从中借鉴了部分时间结构。
你总是回想起哪位作家?
弗朗西斯·斯布福德: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
你正在创作新的小说吗?
弗朗西斯·斯布福德:我正在写一部奇怪的黑色犯罪小说,背景设定在1922年,讲述美国历史的另一个版本:密西西比有个主要是美国原住民的城。我目前已经写了2/3。关键词有流血、耶稣会和爵士乐。这本书(可能)会叫《卡霍基亚爵士乐》(Cahokia Jazz),(可能)会在2023年出版。
(翻译:李思璟)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