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指本文作者Alex Clark)通过Zoom与诺维尔莉特·布拉瓦约(NoViolet Bulawayo)连线的当天,她正依靠一台发电机来维持自己的网络连接。忽然她喉咙发痒,推说要去打水喝,过了一会儿又大笑归来,说自己忘了今天是没水的,所幸姐姐之前帮她留了一瓶水。在前往美国处理第二部小说《荣耀》(Glory)的出版事宜前,她就住在家乡布拉瓦约(津巴布韦第二大城市),正是她笔名的后半部分。而另一半“诺维尔莉特”则由恩德贝勒语表示关系的介词(等效于英语的with)与母亲的名字合成,她在女儿仅18个月时就去世了。布拉瓦约说,幼年丧母的经历意味着她的写作总是会有一种强烈的、关注个人生活如何与更大的历史与政治力量相互交织的意识。“我们背负的一些东西与我们的主观意愿关系并不大。但我们就在这里,任何事情都可能降临到我们身上,这就是我故事的一部分。但它也无法定义我,决定不了我之所是以及我将要去往何方。”
1981年,也就是南罗得西亚并入津巴布韦以及罗伯特·穆加贝首次担任总理后的那一年,伊丽莎白·赞迪尔·策勒(Elizabeth Zandile Tshele,布拉瓦约的原名)在布拉瓦约在出生。她运用自己的作品来探索命名作为一种自我占有行为(self-possenssion)的重要意义,她的处女作就以《我们需要新名字》(We Need New Names)为题。她曾经在台上说,自己小时候有过很多名字,直到上学第一天才知道自己的称呼是伊丽莎白。
《我们需要新名字》于2013年出版,曾经入围布克奖短名单,也使布拉瓦约成为了首个名列最终6人名单的非裔黑人女性与津巴布韦人。早些时候,该书的开篇章节还以《前往布达佩斯》(Hitting Budapest)为题获得了非洲文学凯恩奖,“布达佩斯”是一群饥饿的孩子为某个富裕地区取的绰号,他们从名叫“天堂”的棚户区出发,去那里偷一些番石榴。小说的焦点从津巴布韦逐渐转移到了主角位于美国中西部的新家,这也反映出作者本人所经历的地理与文化之旅——布拉瓦约先后在密歇根州以及得克萨斯州学习,后于康奈尔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并获得杜鲁门·卡波特奖学金,二者皆属于创意写作领域。布拉瓦约18岁离开津巴布韦去投奔姨妈,由于学业需要与国内的不稳定因素,过了整整13年才得以重返故乡。在之前的访谈里,她谈到自己刚开始在美国生活时曾度过了一段沉默的时光,而她原本是个吵闹的、喜欢和别人打成一片的小孩。

后来布拉瓦约去了斯坦福以及其它一些地方教书,但2017年她却有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迫在眉睫的返乡理由:穆加贝的前任副手埃默森·姆南加古瓦发动“政变”,终结了他的统治并执掌了政权。“这件事意义非凡,我当即就感到可以为此写一个故事,”她回忆道。她起初考虑的是非虚构题材,后来在整理素材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一切值得一说的都会被说出来。”目睹了2018年时充满暴力与动荡的选举,她明白自己需要采纳一种不同的方法。“我花了些时间做实地调研,观察了人们的希望与梦想、恐惧与乐观,也目睹了选举结果导致的一系列撕裂。这一切都让我意识到,这本书甚至与穆加贝毫无关系,它需要关注普通人,以平凡的人以及他们的故事为着眼点。”
即便有了这些经历,最初的写作计划也还将面临一次更彻底的转变。布拉瓦约在大清早醒来,打开新闻频道,发现现实的发展速度已经超出了自己的预期,每一个新的发展都让已有的故事线或角色变得更趋复杂或过时。她回忆说,当时津巴布韦人经常会引用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来讨论政治局势,加之她的记忆里有不少祖母讲的以动物为主的故事,她最终决定完全抛弃人类世界。
结果就是,在小说开头处,一群虚构的吉达达国公民聚在一起庆祝独立日,观礼的老马(Old Horse)与其妻奇妙驴(Marvellous the Donkey)的安保工作则由天选者随从(Chosen Ones)与凶猛的“捍卫者”(Defenders)狗群来负责。老马已经稳居权力巅峰,他幻想着其它动物将会永远忠诚,但讨价还价时却对它们的强烈不满毫不在意:

“但国父也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对我们而言事实上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上次选举之后他其实已经作弊了,上上次也和其他人一样存在舞弊行为,靠的都是偷窃——是的,在他和他的政权挫败了所有适当的以及可能的、以和平与合乎宪法的方式敦促他下台的努力后,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变成那些动物来庆贺他的覆灭,不论他以什么方式覆灭。”
布拉瓦约在津巴布韦与南非分别呆了一年,返美六个月后,她又一次回到了家乡,继续体验津巴布韦人的日常生活现实:加个油或者去银行取钱要等好几个小时,基础设施频繁停摆,医保覆盖范围亦相当有限。穆加贝倒台后的那一波希望感过了,以后又要作何感受?她形容这是多年停滞之后的一大转折点,那么希望感的消退又有多快?“我想那显然是非常非常快的,”她一面回答,一面谈到2018年选举结束后有些人跃跃欲试,希望为新政府大展宏图开辟一些空间,但马上就“意识到我们仍要应付许多麻烦,变革并没有发生”。

我问她当时以及现在分别对国际社会的反应有何感受。“我想说,在某些时候,假如你来自诸如津巴布韦这样的地方,你过的生活又是我们当中的某些人所经历过的,那你便会意识到,你只能自力更生。世界并不会——我不打算说别人并不真正在乎我们——但他们看起来不太明白应该如何改善我们的处境。非要说什么的话,那就是我并非对国际社会失望,只不过感到这样的话我们就又回到原点了,而且没有什么跳出死循环的办法。”
但这种孤立感也不一定会让人狭隘。《荣耀》里也不乏非凡的、激动人心的时刻,如一群动物在等待被讽刺性地冠以“自由、公正与可信”之名的选举结果时,远方忽然传来新闻,它们便围在一部手机旁观看了别国执法人员施暴杀人的视频:“我们看到他们在交谈,被杀的黑人尸体就在他们脚边,看起来就像收割好的庄稼,像一大捆黑乎乎的、一文不值的东西。”这一页的内容可归纳为这句话的重复:“我没法呼吸了。”
乔治·弗洛伊德被害案以及随后的全球性抗议活动,令布拉瓦约开始反思各个国家与社会的滥用权力现象与自己身为作家的责任之间的关联:
“在工作中碰到这一点以后,我不得不暂时停下来,思考自己要如何面对世界,以及当下究竟发生了什么。想办法让我的创作能多做一点事,多一些介入性,并且继续与世界各地为争取一切形式的自由而斗争的人们站在一起。”
她对社交媒体在帮助参与斗争者与他人建立联系、使新闻与报道变得更加民主化、提供多元化的视角与声音等方面起到的作用表示赞赏。但她也提到了一个人下线以后持续参与和介入,“(以及牢记)一些参与运动的人并不总是有上网的机会,这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地点。我们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很容易把上网想象成稀松平常的事,以为这就是真实的世界。但现实情况是,有相当一部分战斗乃是在社交媒体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打响的,也有一些重要的名字永远不可能成为热点,有许多代自由斗士都是在没有互联网、也没有聚光灯的条件下推进其事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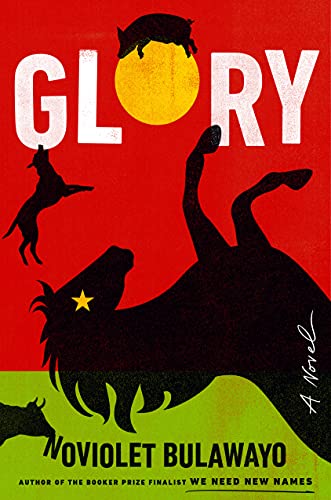
我们讨论了这些方面与女性主义相关议题的联系,以及分享经验与偏好的平台之激增如何可以挑战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话语,即那种认为该区域以外的女性都是需要救赎的压迫受害者的观点。“西方女性也有自己要做的事,”她评论道,“关键是要建立团结。我认为一场真正具有互联性与交叉性的运动可以带来诸多教益,将来自不同国家与时代的女性团结在一起,跨越一切人为设置的藩篱。”
令我好奇的是,对于在美国生活了这么长时间的布拉瓦约而言,那些人为设置的分界线是如何与她自己的经验相契合的。她说,最近几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令她有些沮丧,因为它们使她留意到“在世界上某一地点发生过的事,很容易就会波及到另一些自认为拥有民主制度从而能够幸免于难的地区”。但她仍坚持要保留自己的双重身份认同。“我热爱这两个国家。我花了一段时间才真正做到了以美国为家,要达到这一状态并非易事。我只是个移民,不是土生土长的人。这个国家屡屡让你感知到自己的他者性(otherness)以及外来性(foreignness),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尤其如此,以前的确也有这种情况,但如今显然有所加强。这无疑会让你在如何看待自身之归属的问题上陷入某种紧张。但现实情况是,我在两个国家生活的时长几乎是相同的。我在这两个国家都有生活要过,以后的生活也将在这两个国家继续下去。鉴于此,无论两国有多么疯狂,和其中任何一国彻底撇清关系都不再是可行的选项了。”
《荣耀》号称是献给“身处各地的全体吉达达人”的,而它无疑也像是一曲颂歌,既写给公民团结的伟大力量,也写给久居暴政之下猛然发现自己已经忍无可忍的人们。在我们对谈之际,在眼下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战这一时刻,这种情绪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然而,如果读者对穆加贝下台后津巴布韦面临的诸多挑战缺乏敏锐性,那他们就无法读懂这本书,毕竟这也是一部充满了痛苦与失落的小说。以现在为起点来看,布拉瓦约对未来有何展望?她思忖良久。“作为一个作家以及津巴布韦人,在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这一点上,绝望感是难免的,”她说道,“我明白这种眼光可能失之于笼统,但现实就是未来令人很泄气。而这也情有可原,因为那些管理国家的人效率低下,他们无能而腐败,也不关心津巴布韦普罗大众的生活。此外,考虑到上次选举中的种种乱象,短期之内要纠正这一状况看来是相当有难度的。绝望的来源就在这里。话虽如此,心怀希望并保持乐观总是十分重要的。新一代人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这让我备受鼓舞,我也认为这对于我们找出前行的正道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毕竟你首先得想要变好才有望走得更远。”
那她今后又打算做些什么呢?她笑了笑。“下一步我打算彻底放松一下自己。2017年以来我就一直在写作。这本书快把我的精力耗光了。我觉得这是我做过的最为困难的事情之一。”考虑到耗不起的不仅是她本人,还包括她的发电机,我们便就此别过。
本文作者Alex Clark是《卫报》《观察者报》记者。
(翻译:林达)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