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要展示即使是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也能够产生丰富的行为方式,独自处于宇宙中的人仍然能够创造他自己的价值。我认为这就是,这个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问题。”阿贝尔·加缪在二战后提出的这个问题,仍然摆在我们这个时代面前。
1913年的今天,加缪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从小就在贫民区里尝尽了生活的艰辛。年少时,加缪曾患肺结核,痛苦不堪。病痛的萦绕以及二战、冷战的影响,让加缪对死亡和生存有着更为独特的思考和把握,在《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话》等作品中,他的思考聚集在这些主题上:自杀、苦难、荒谬......
阳光和苦难一直是加缪书写的两大主题,它们包括了“生存”和“死亡”在内的各种命题。在散文集《反与正》中,年轻的加缪写下了各种人物生而在世的孤独,以及对死亡的恐惧。无论是宁愿成为他人的负担也不愿离去的老妇人、还是没人倾听自己叨唠的老头,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都只想着逃避,以博取更多的生活的光与热。如果说《反与正》的底色是沉重阴郁的“黑”,那《婚礼集》则充满着温馨愉悦的“白”。神灵的居住地“提帕萨”那灿烂的阳光与湛蓝的海洋、阿尔及尔夏天的幸福光景,都暗示着那时以“阳光与海涛之子”自居的加缪内心的宁静与和谐。
1938年,加缪开始酝酿“荒谬”系列作品。无论是这系列的第一部《卡里古拉》、还是成名作《局外人》,以及《西西弗的神话》,加缪都在其中阐述了他的“荒诞”哲学思想。认识到人们麻木不仁的生活,从而决心做“荒谬”真理的传播者的卡里古拉表面上是个暴君,实际上,他想用暴行让人们摆脱虚无,在真实中生活;默尔索看来极其冷漠,没有血性,但他却有着十分简单而真诚的灵魂。
那么,什么是“荒谬”?它是对于人类被抛到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和命运的清醒洞察。就像被罚永远一遍又一遍地推着巨石上山的西西弗一样,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时,诸种背景崩溃了。起床,乘电车,在办公室或工厂工作四小时,午饭,又乘电车,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很容易沿循这条道路。一旦某一天,‘为什么’的问题被提出来,一切就从这带点惊奇味道的厌倦开始了......在某一段时间内,这也就足以概括认识荒谬的起源。一切都起源于这平淡的‘烦’。”
这样一个“荒谬”的世界是可怕的,我们该如何面对?西西弗——加缪式的英雄——没有选择在肉体上消灭自己,也没有在精神上逃避现实,他努力抗争,“藐视神明,仇恨死亡,对生活充满激情”,“他完全清楚自己所处的悲惨境地:在他下山时,他想到的正是这悲惨的境地。造成西西弗痛苦的清醒意识同时也就造成了他的胜利。不存在不通过蔑视而自我超越的命运”,“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是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

因为反抗,这个被永久性流放的人,徒劳而无休止地重复着这毫无意义的苦役,但却是幸福的——正如同临刑前的默里索所感受到的,这个结论令人震撼。

荒谬不仅不会导致虚无主义,相反,能够承认荒谬的人,在道德上会更加诚实。在他的后期著作《鼠疫》中,加缪从荒诞的绝境之上发展出一种诚实的、富有同情心的人道主义,他借医生之口说,“我决定拒绝接受促人死亡的,或认为杀人有理的一切,不论它是直接的或间接的,不论它有理无理。 无疑,从塔鲁与鼠疫抗争的事实看来,鼠疫无疑就是毫无理由促人死亡的东西。”加缪自己也在生活中践行了这一点。
“我在上高中时第一次读到加缪。在我遍游欧洲之时,我把他放在我的行囊里。我带着他开始(并结束)每一段恋爱,我也带着他进入(并走出)人生中的困难时期。”在关于加谬的最新传记《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中,作者罗伯特•泽拉塔斯基说出了他与加谬的第一次“接触”。从这之后的三十年里,罗伯特一直更新着他对加谬的认识,并在这本书的写作之际,坦言自己现在对他的看法与三十年前很少有相似之处。这背后的原因更为复杂、也更有批判性。
与按时间顺序讲述人物生平的方式不同,罗伯特选择了加缪生前的4个大事件来追溯他的思想与经历,聚焦作为一位作家、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以及作为一个人的加缪的印迹。罗伯特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也不是从“为加缪写本更好的传记”出发,而是为了提醒人们重新认识加缪的意义,并思考加缪何以能代表一个时代的声音,又何以对今天的我们仍然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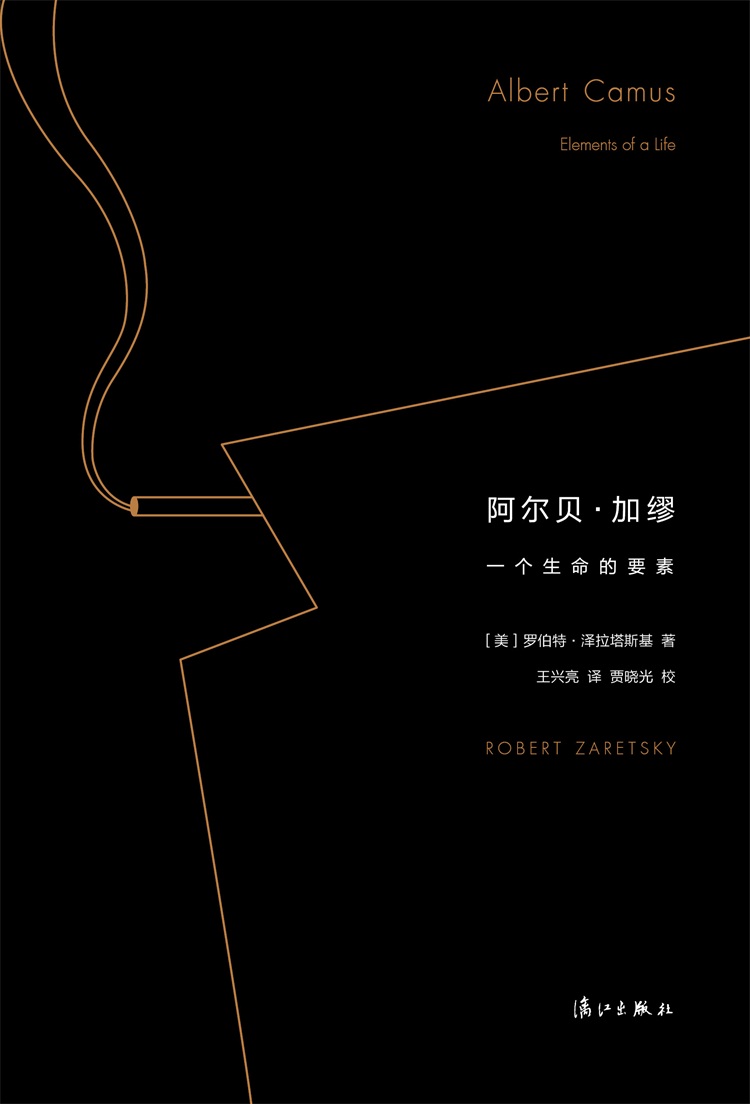
加缪的沉默
(摘选自罗伯特•泽拉塔斯基《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
“人是怀着几个熟悉的观念活着的。两到三个,”加缪曾经写道,“我们根据社会和碰巧遇到的人,来修正并改造它们。一个人通常要花十年才会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一种我们能够谈论的思想。”
根据同样的理由,很久以来,这个世界对于《局外人》《西西弗神话》《鼠疫》和《反叛者》的作者也怀有几个熟悉的观念。有一种观念认为,加缪是探究了有关自由和正义概念的人,他反思了这两种概念变为绝对诉求的危险性,努力调和它们相互冲突的特性。另有一种观念认为,加缪书写了被祖国——对于他是法属阿尔及利亚——和被一个失去了上帝的世界所放逐的本质。还有一种观念认为,加缪表达了沉默的全部谱系:孩童天真无邪的沉默,政治犯或者被剥夺公民权的本国人的沉默,悲剧冲突的沉默,以及一个宇宙的沉默——它对于我们对意义的需要漠不关心。
当我们关注他人时,我们倾向于聆听,而不是对话。因此,“关注”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就是“沉默”。加缪的艺术造诣和道德,部分地由这种“沉默”表达出来。有些沉默,如同阿尔及利亚单调的景色中海市蜃楼闪耀的微光,还有他笔下众多人物在直面世界时,沉浸其中的那种沉默。另有一种沉默,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法属阿尔及利亚突陷战火时,加缪陷入的沉默。加缪在阿尔及利亚出生,接受的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价值观。在敌对且终究难以调和的法帝国主义与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诉求之间,加缪忍受着分裂之苦。最后,在1957年,他宣布他将永远不在公开场合谈论这场战争——除了两次例外,他遵守着这个誓言直到三年后去世。
自那以后,诸般喧扰就不可避免地旋绕着这种沉默。对于在加缪最后的几年间,萦绕着他的一种不同寻常的沉默,情况同样如此。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加缪感到窒息和空虚;他担心自己已陷入沉默,因为作为一名艺术家,他已无话可说。 加缪的哲学论文集《反叛者》(The Rebel)在他和萨特之间引发了激烈的公开争论,最终不仅终结了两人之间的友谊,也加剧了加缪本人对自己作品的疑惑。正如他对一位朋友所说:“我感到自己就像被一团纸吸干了的墨水。”他后来出版的小说《堕落》(The Fall)减轻了这种疑惑,但仅仅是暂时的。
当加缪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一些评论家认为,对于这项奖项来说,他有些太年轻了(他刚年满44岁)。然而对于另一些人,加缪又太老了,而且事业也已经到头了。他们总结说,诺贝尔奖证明,加缪只是一个文学遗产,他已经无话可说。加缪本人也有这些疑惑:在短篇小说《乔那斯或工作中的艺术家》(Jonas,or the Artist at Work)中,加缪描写了一位艺术家,他的生命渐渐流失了创造力,最后沦落到只能眼睁睁地盯着一张空白的画布。尽管这篇小说几年前就已经完成,却直到1957年才在他的短篇小说集《放逐和王国》(Exile and the Kingdom)中发表,它清晰地说明了加缪所处的困境。
加缪在其艺术作品和政治生活中对沉默的强调,反映了他决意替那些出于不同原因而被迫沉默的人代言。他在诺贝尔获奖演说中宣称,艺术的崇高之处根植于“对于我们明知之事决不说谎,以及对压迫进行抵抗”。加缪描述了法属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困境,谴责大多数法国公民对此置若罔闻。战后不久,他同样猛烈地攻击法国对阿尔及利亚实施的折磨。让他震惊的是,不久前尚处于德国人压迫下的法国人,如今竟已变成阿拉伯人的压迫者。接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几个月,他又固执地同法国政府的审查官进行了斗争,坚持不懈地批判那种“认为一个民族要振奋精神,必须以失去自由为代价的诡辩论点”。这种论调,以及加缪对法兰西共和国在宣战后取缔共产党的谴责——“法律关乎所有人”,决不能区别对待——不但适用于加缪时代的危机,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在当今时代所面临的危机。加缪的呼吁所具有的紧迫性仍然要求我们对此关注,而他的洞察力仍是我们的榜样。
一些评论家正确地观察到,加缪固执的人道主义在今天显得尤为突出。然而,如果我们不够仔细,我们就可能忽略,他的立场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如此非同寻常。这并非说加缪是一位圣人——相反,他的同僚、朋友和家人都证明他身上有很多缺点。回顾他和萨特的争论,萨特在《现代》(Les Temps Modernes)杂志上对这位曾经的友人的攻击令我们感到害怕,而加缪那些被萨特正确指出的智识与个性上的缺陷则令我们感到不安,这两种情绪撕扯着我们。矛盾的是,加缪的一些德行也模糊了他的重要性。他与极权主义的斗争在当时是大胆之举,自此之后却成为了正统。他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即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LN)的厌恶,被后来的历史证明不无道理——阿尔及利亚成了一党专制的国家。他欲为道德奠定一个基础的努力,曾经被他的一些同代人视为异类,但从那之后,许多思想家也加入了进来。现如今,有谁会对加缪为直接、真诚的对话之必要性作出的辩护提出质疑?某种程度上,这个世界——或者说,至少那些倾其一生分析这个世界的人——已经赶上了加缪的脚步。
然而问题在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这种地位颇感满足:我们的道德准则和我们的人道主义似乎都是很容易习得的,而非通过努力争得的。如果加缪仍然在世,当他面对那些声称是受他启发的新自由主义者,或者新保守主义者时,他是否会感到坦然?我对此是有疑问的。相反,他仍会是一个流亡者,一个局外人——一位道德主义者,如同托尼·朱特评论说,是一位天生就与自己、与自己的世界合不来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这来源于加缪对生命基本性质的洞察。他的作品涉及神秘——不管是好是坏,他称之为“荒谬”——人类处境的神秘,以及这种神秘对意义的抵抗。导致这种荒谬的,是人类与世界的对抗,而非世界本身固有的某种东西。“荒谬,”加缪在《西西弗神话》(The Myth of Sisyphus)中写道,“既取决于人,也取决于世界。”在这种时刻,我们涉入了自认为很熟悉的一片海洋,却突然被一种形而上学的激流所击倒。
加缪强调说,荒谬不会导致一种虚无主义的人生。相反,要获得承认荒谬的能力,需要在道德上作出努力。“我所能做的一切,”他在“二战”之后不久说,“就是要展示即使是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也能够产生丰富的行为方式,独自处于宇宙中的人仍然能够创造他自己的价值。我认为这就是,这个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问题。”
如今这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之一。加缪的作品已成为受困扰者的指引——那是一种让加缪感到不安的身份。“我并不为任何人说话,”他强调说,“我替自己说话就已经够难了。我不知道,或者只是朦胧地知道我前进的方向。”这里虽然有过分自谦的因素,但其中仍有一份深切的真诚。加缪成为人生节奏极快的一代人的发声者:1942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局外人》(The Stranger)。战争时期,他又以抵抗运动和存在主义的代言人身份出现。大约十年后,195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后,1960年1月4日,他死于一场车祸,当时他驾驶的汽车在法国南部偏离了道路,撞在了一棵树上。
*********
加缪遇难时,在他随身携带的一个文件夹中,装着一份近150页的手稿。那就是《第一个人》的文稿,是他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不久倾力创作的一部小说。在这部未完成小说的开端,主人公雅克·高麦利,和加缪一样,一个中年法属阿尔及利亚人——造访了圣布里厄布来顿镇的一片军人公墓。在守墓人的指引下,高麦利找到了他此行的原因:一块刻着“亨利·高麦利,1885—1914”字样的普通墓碑。当他的父亲死于马恩河战役时,雅克·高麦利才一岁大。当他凝视着墓碑时,高麦利“不由自主地计算了一下:二十九岁。一个念头击中了他,撼动了他的存在本身。他今年四十岁。这块墓板下埋葬的父亲比他现在还要年轻”。
这一刻,高麦利和加缪都开始寻找他们的过去。尽管《第一个人》是加缪最为个人化的作品,但在这一点上它却不是独一无二的。纵观他作为一名作家的短暂一生,加缪的自我和他的艺术密不可分:在他尖锐而入木三分的言辞背后,悸动着强有力的记忆、经验、关注和激情。他的密友之一让发现,加缪在其第一本散文集《若有若无之间》中太过频繁地用到第一人称代词“我”——加缪接受了这一温和的批评:他承认,作家“必须处于幕后”。1958年,在他为这本文集的新版所写的序言里,加缪强调了这些文章的个人特质:“这本小书作为证言拥有巨大的价值。”就此而言,他最后的作品《第一个人》也同样如此。就像其他人写回忆录那样,加缪通过写这本书,将他的过去浇铸成了有意义的形状。
加缪曾经承认他“从来没有”从他艰辛而困厄的童年中“恢复过来”。加缪一家住在阿尔及尔的贝尔库社区的一间公寓楼里,有三个小房间和一个厨房。没有管道系统,没有电,楼内只有一个三户人家共用的卫生间。他同祖母、母亲、哥哥和舅爷一起住在这里,度过了从婴儿到高中的整个时期。至于父亲吕西安·加缪,他和亨利·高麦利一样,死于1914年的马恩河之役。他的遗孀唯一保留下来的只有一张照片,以及一块夺去他生命的弹片。加缪和哥哥吕西安挤在一张床上,这张床和母亲的床塞在同一间屋子里。屋子唯一的窗户朝着内院。祖母有自己的一间屋,而她的兄弟、加缪的舅爷艾蒂安睡的房间同时也用作餐厅。在悬吊式油灯昏沉的黄光下,是一张孤零零的桌子。全家人在上面吃饭,孩子们在上面写作业,艾蒂安则在上面擦拭他的猎枪,并替他的狗“钻石”捉跳蚤。这一切都处在祖母恶狠狠的注视之下。

大海赐予加缪及其友人的,正如哈德逊河赐予纽约年轻人的一样:使他们得以躲避城市夏日灼人的热浪。战后访问纽约期间,心臆难平的加缪看着滨河大道上的车辆,又想起那片大海:“川流不息的车辆发出沉闷而渺远的声响,和波涛的声音一模一样。”如果某部作品中没有渗透加缪对地中海恒久的爱,那倒是非常罕见的。他创造的文学人物,从《局外人》中的默尔索到《鼠疫》中的里厄,把大海当作远离社会喧哗与骚动的暂避之地。当然,加缪也是如此:只有当他在水中畅游,坐在地中海的沙滩上时,才会与这个世界融为一体。在太阳底下,他“不用戴面具”。 地中海既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地区,也是一块哲学领地。加缪把地中海升格为一种象征,它代表着人类价值与思想的远古世界,世俗,且与大地不可分割;加缪树立起这个世界,是为了反抗那些不断扩张、了无生气的意识形态,它们让他想起欧洲灰色的都市景观。
事实上,加缪发现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物质贫困的世界,依附于贝尔库那稀缺而破败的家产之上;另一个是精神富足的世界,存在于远处激荡的波浪里和掠过他头顶的那布满群星的天空中。他感到他的工作和生活充满了张力:匮乏与完满、社会与自然的疆域之间的张力。他清楚地认识到,他横跨着这两个领域。夜晚,年轻的加缪会从朝向大街的公寓窗口向外凝视:尽管萦绕着他的,是身后“发臭的走廊”难闻的气味,以及对身下开裂的座椅的触觉,但在同时,“他抬起眼,沉醉在这纯净的夜晚中”。




评论